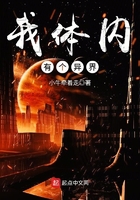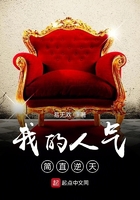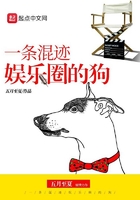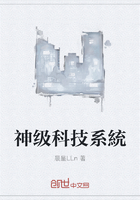给姥姥发完丧后,静轩便直接从西沟(陈山和展庄中间一条早年发洪水时冲刷形成的大沟)里过去,大约十来分钟,便到老爹家了。
小时候静轩没少走过,记得那时,大沟的北头长年还有水,现在北头却渐渐被淤泥填高,被村民种上了庄稼。而那口早年没少淹死人的井也不见了。
但是在陈山到展庄走的小路旁,有两口井,是陈山人以前喝水的主要来源。可这次,当静轩走过的时候,却看到西边的那口井,井口长满了酸枣树和野草,看来是好久没人打过水了。而东面的那口井,井口却很干净,长年的磨损,使得井口铺的石头光滑如镜。静轩一进还纳闷儿。
回到家听老爹说:那口井好几年不用了,没人再去打那里面的水吃了,因为那井里淹死了人。一个老光棍儿。
话说一天,老光棍去打水,井口铺的石头光滑如镜,他脚底下一滑,再也没上来。因为没有家人,只有一个哥哥,平日里却也不联系,所以没有人关心老光棍的行踪。由于村里的人自从有了机井供水,很少有人去井里打水,所以四五天后,有人去井里打水,才发现老棍漂在水面上。报了警,等打捞上来,才知道是老光棍。人们这才想起已有好几天没见过他了,原来死在了这里,可怜的一条生命就这样结束了,没有亲人的关心,成了井里的一个孤魂。
听到这后,静轩有些害怕,但是隔一天,当静轩再次走过那口井时,静轩却没有害怕,看着井口却多了一份慰祭的眼神。
以前拉水经过的那个大陡坡,也在长年的雨水冲刷下,不再那么陡峭。可是年近三十多的静轩爬上这段坡时,却有种缺氧的感觉,喘不上气来。真是在城里生活时间长了,一种常见的亚健康。
回到家,老爹正在喂娘吃饭,娘披着棉袄,背靠着一个板凳,两边有被子裹着,只有这样她才能坐的住。娘看到静轩回来了,眼里透出笑容。缓慢的抬起下巴,张着嘴,想说什么,却知不出声。娘前几天犯病后,就这样了。加重的病情,使得她更加的虚弱,好像抬头,她都很费劲。静轩看到这,眼泪又不争气的往下流:“我知道了,你别说了,好好吃饭啊!”说着静轩走出了里屋的门,她想让娘好好吃饭,多吃一点,不让她分心。
可是没过一会儿,就听见老爹说:“不吃了呀?”
静轩进门,只见娘慢慢的摇着头,嘴张着,还在慢慢的咀嚼着,却一脸痛苦的表情。长时间的卧床,加上病情的折磨,使娘的咀嚼功能和其他器管,都已不听使唤,吃饭对娘来说,也许就成了一种痛苦。
生命在这个时候似乎成了受罪,但是为了亲情与责任,娘的坚持,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老爹尽心尽力的照顾,成就了子女们的安心与放心。有时想想真是一种无耐。
但日子却要一分钟一分钟的这样过,现时能做的,只有让娘舒服一点是一点。
静轩在吃过饭后,拾掇完,看天还不晚,她便给老爹说她要去找元家,也就是小时候给静轩吃过奶的元的媳妇。一开始,她想找后面的婶子,老爹不愿意,她想也是,婶子本来就是个不着调的人;她又想找前面的大娘,老爹也是不愿意,可能是年长些不好说话吧。老爹说前几天,娘差点不行时,元家提过,问老爹给娘备好寿衣了嘛?老爹说还没。所以老爹想让静轩去找元家商量,一些事情她也懂。
寿衣,娘的寿衣。静轩当了近三十多年的闰女,事至今日,也就是姥姥去世时,静轩才想起娘的寿衣!这让她自责了好几天,她觉得自己太不孝了,虽然这种事不是好事,可人家也有一种说法,早准备也是好的。姥姥的寿衣,静轩的妈妈在十年前就给姥姥做好了,而姥姥的寿鞋,一双小脚的绣花鞋,娘也是在二十多年前早做好了。
所以静轩一回到家,便急切的想把这个事办了。来到元家,人家刚吃完饭,听静轩说明来意,她说:“是呀,我早就给大爷爷(静轩老爹在村里的辈分大)提过,大爷爷又是不爱说话的人,我说你有什么事你就给我说声,你看静姑和两个叔又不在身边。”
“是呀,俺爹就这样,我就没往这事儿上边想,唉,你说,弄的我好几天过不来劲儿。”静轩说到这一边摸眼泪一边说。
元家一边按抚着静轩一边说:“没事儿,现在也不晚,主要是敢上急,能拿过来就用,也不用到时着急瞎抓是吧?老人也说,说不定咱买了,冲冲也许大奶奶就好多了是吧?现在也不兴做了,都是买现成的,我给他们办过好几次了,这种事儿我懂。你就放心吧啊。”
“行,反正我也不懂,两个哥哥又不在身边,就麻烦你了。”静轩说到。
“没事儿,正好现在也不晚,咱们现在就去,我骑车带着你。”元家说。
就这样,静轩和元家一块来到乡里的专买寿衣花圈的点,和元家很是熟络,在元家的建义下,静轩给娘买了店里最好的一套。这时静轩心里才稍稍心安。
元家说:“咱装到袋子里,别让你婶子和其他人看见,省的惹闲话,到时用时,谁也说不出闲话是吧?”
静轩一边应到一边心里想:最好别让婶子看到,省的竟在娘眼前瞎说,惹的娘生闲气。
第二天,静轩把娘用的床罩和枕巾都换洗下来,天气也好,就把老爹和娘盖的被子晒了晒,中午暖和时,静轩又给老娘洗了手和脚。也许这样,也能让娘轻快些。看着静轩忙里忙活,娘一直张着嘴想说什么,眼里透着笑意。静轩看到这便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个老太太,别操心了啊,你只要好好吃饭,比什么都强啊!”
听着静轩的“呵斥”,娘笑开了花,静轩含着泪也笑开了花。
晚上把娘安顿好后,静轩和老爹,便拉起了家常。
静轩一会儿问起大娘家的人,一会儿问起那谁还活着嘛?老爹都一一给静轩说着。娘也听着爷俩的对话,脸上洋溢着幸福。
静轩问:前面俺大娘家的那个哥,还在家嘛?
老爹说:早就不在了,又倒插门到别村了,娶了一个带着儿子的妇女。妇女她老公死了。
静轩好奇的问:那,那个哥第一个媳妇是不是东北的来?
那呀,是郭山的呀,早就死了。不是生了一个姑娘嘛?那个姑娘现在不是跟着你大娘,现在在乡里上学呢。老爹说。
怎么死的呀?静轩问到。
老爹语重心长的说到:和你大娘打架,上吊死了。一开始都以为是离家出走了,找了好几天没找着人,到后来,第四天,她亲爹不死心,信着去南边山上看看,谁知还真就在南边山上的柏树林里找着了,可人已经死了好几天了!
听到这,静轩心里一惊!赶紧问到:那人家娘家愿意我大娘嘛?唉!
不愿意呀,书记说事儿,让你大娘赔礼道歉,不愿意也没办法呀!老爹无耐的说到。
唉!静轩应声到。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断送在了婆媳争吵下,是大娘太恶还是媳妇心太小,没人再喋喋不休的争论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小山村里的人们也许都已忘记被大娘逼死的媳妇长什么样了。也许只有她的女儿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才会在心里说一句:你是否知道,你的亲娘,是被你奶奶给逼死的嘛?
说完这,静轩一时想起南柴,也是位老光棍儿。昨天听大娘家前面住的兵他娘说谁,静轩以为是说的南柴来。所以向老爹问起。
老爹说:南柴早就死了,烧死的。
烧死的?!他不是和兵家一块住嘛?咋这回事儿?静轩迫不及待问。
他原来是和他们一块吃饭,晚上他一个人在上面老宅子里睡,他晚上抽烟,睡着了,烟头没灭,把被子给点着了。等他醒来,火着的很大了,他本来腿脚就不利索,硬撑着爬门口,却硬是没开开门。老爹说到。
由于南柴住的房子在村里的中心,周围没有别的住家了,人们都把新房子建在了村北或村西边,村子中心几乎是空的。大冬天的,农村人晚上睡得又早,所以等人们第二天一大早起来时,才看到南柴的房子冒着烟,等人们赶到一看,一切已经晚了,南柴已经被烧焦了!老爹说他死时的姿势很可怕:一只胳膊向前抬着,一条腿扯在后面,是多么的渴望有人来帮他一把,却又是是多么的绝望!如果他有家人,也许悲剧不会发生。
静轩现在还记得,有时回家碰见南柴,他都是扛着一把锄头,腿一颤一颤的走着,笑着问静轩:静儿,回来了?静轩也笑着答:嗯!
小山村的贫穷,闭塞,造就了人们世代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六七十年代的贫苦家庭的劳力娶不上媳妇,八九十年轻的劳力都倒插门到外村,才有了很多的光棍儿,也有了很多死去和活着的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