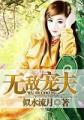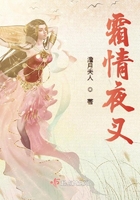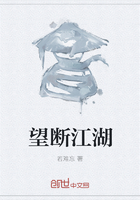在一部叙述孔家人的田野志当中,我们可以采取共时性分析法,利用结构功能主义与法国结构主义学派常常使用的策略,将某一社会视为“时间之外的存在”,从而不去考虑历史情境。如果使用这种方法分析,在一段时期内收集到的田野材料需要被人类学家假定为代表某种长期大致不变的社会生活格局。
但针对大川的材料,我们需要采用惯时性研究,将大川视为“时间之内的存在”,放在历史情境内加以研究。这做的首因是孔家人本身总是通过历史透镜考察自己的生活以及孔庙的意涵。孔家人不但一直努力地去理解庙宇或社区意味着什么,而且不断主动地记录历史。这一努力包括将口述历史代代相传、编写大量族谱、刻写大量庙宇对联、撰写醒目的纪念性匾额、精心制作祖先灵牌、举办大型有历史意义的祭奠仪式。引用桑格瑞的话说,这些活动有助于“历史意识的生产”,“重要性等同于史学”,即中国士大夫所言的“治史”。
桑格瑞所说的历史意识生产主要基于人们对记忆的建构。在大川,历史的概念不可避免地与国家政治、地方冲突、道德理性、社区苦难、宗教信仰以及仪式行为交织在一起,同时又受到影响。在最后的这一章里,我将把笔墨集中于记忆的政治与宗教层面,扼要重述本研究的两个主题——集体创伤与乡土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