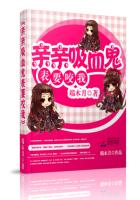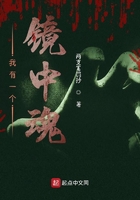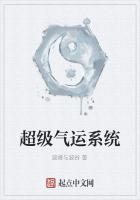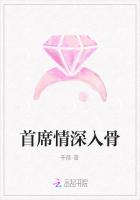新上台的干部们为什么对孔庙如此感兴趣?我们已经讨论了几个原因,但在新干部和老庙管之间还有其他的紧密关系,要从之前的政治运动谈起。
解放初期,如今管理大川孔庙的那些人大多刚刚成年。他们中有九个毕业于大川旧孔庙的小学。其中一人到兰州一所著名的中学继续读书,另外有两人去了兰州的一所师范学校。这些读书人不仅目睹了解放前庙里的仪式,而且他们学习的一部分就是要接受当“礼生”训练。他们中间的三人后来担任孔庙小学教师。村中老一代的读书人教给他们庙中仪式的原则与程序,希望他们能够继承向孔子献祭的传统。1949年,在庙中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典礼,整个孔氏家族的代表都参加了。这些人中有四个充当了仪式的助手。在1984年前,这是最后一次全族范围的祭孔典礼。
35年过去了,新庙的庙管成为大川最后一代受过古典教育的孔家人。他们和孔家的其他精英一样,遭受了政治打击。在访谈中,其中一位老者告诉我,他在土改中被划为贫农,这是令人羡慕的一种出身。但在1954年,由于他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的外围组织三青团,他又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当时他是小学教师,结果被开除,他只好回到大川。六十年代初,他负责大川的一个特殊劳动单位,这个单位由四类人组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最后这一类是个大杂烩,包括从宗教人物到偷集体东西的人。这些人被称为“四类分子”后,与妻子甚至子女在“劳改组”劳动。他们所干的那些活,出身好的人如果认为没有可观的报酬一般都不会干。这些活包括扫大街、运猪粪、放电影时摆凳子、为干部跑腿,或挑着大水桶去浇远处的耕地。其中农田里的杂活报酬很低,其他的活则被当成思想改造的补充。
“全是四类分子为大川种下了社会主义果实”,一个当年经历过劳改的老人挖苦地对我说。据大川老人们的估计,曾经有二百多人在不同时期在村中的“劳改组”干过活。其中干得最长的村民是地主或富农,一共包括十四个家庭。劳改组的另外一批劳力是解放前曾在村公所干过事的人,或曾当过低级官员和军官的人。还有一些人是在不恰当的场合说了不该说的话或干了不该做的事,因而被罚到劳改队干活。这些人的子女也很倒霉;由于父母或祖父母的不幸遭遇,他们的婚姻、工分、教育受到严重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