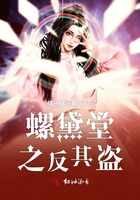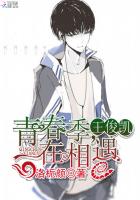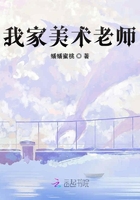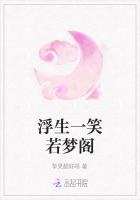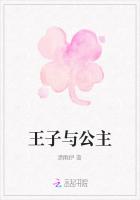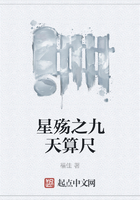中西合璧的奇装异服
1921年7月,在《小说月报》当编辑的茅盾(沈雁冰)第一次见到胡适,当时大学者胡适身着奇装异服,给茅盾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
那时候胡适才30岁,却已是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商务印书馆向他抛出橄榄枝,他也有意跳槽,便趁着暑假到商务来作一番考察,再决定是否跳槽。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国内第一,规模庞大,分国文、英文、词典、理化、东文等部,职员有160人,藏龙卧虎,人才辈出。胡适一去,就占据了商务馆编译所的一间会客室,对编译所的高级编辑及各杂志主编来了个轮流“召见”。他要全面彻底地了解商务馆的家底、状况,然后决定来不来商务馆。
茅盾是众多被“召见”者中的一个,虽说他没有见过胡适,但胡适的大名他早就有所耳闻。陈独秀到上海发行《新青年》时,他也从陈独秀处获得了一些有关胡适的故事,对胡适可谓了如指掌。当时茅盾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思想比较激进。胡适在他心目中,并不像当时的一般文学青年那样,被视为高不可攀的偶像。在内心里,他甚至对胡适有一些排斥,虽然这次被胡适“召见”,但茅盾感觉很平常、很平淡,并无荣幸之感。
轮到茅盾时,他平静地进入房间,在胡适的对面坐下,很冷漠地看着胡适,完全没有一个文学编辑见到众人仰望的大作家时的那份激动与喜悦。在他眼里,胡适的打扮特别奇怪,有点与大学者的身份不相符。多年以后茅盾回忆说:“我只觉得这位大教授的服装有点奇特,他穿的是绸长衫、西式裤、黑丝袜、黄皮鞋。当时我确实没有见过这样中西合璧的打扮。我想,这倒象征了胡适之为人。”这样的打扮出现在胡适这样的大学者身上,确实让人惊讶:绸长衫,那应该配布鞋,如何能配一条西式裤?脚上怎么能穿黄皮鞋?无论颜色还是式样,都不搭调。可是胡适就是这样穿到上海,还出席如此重要的一个活动,这应该是他的刻意而为,他要通过这身服装向世人宣告:他胡适之是一个中西合璧的文化人,既有传统的根基,又有开放的眼光;或者说他暗示商务馆的人,如果他胡适之接手商务馆,一定要将这所国内最大的印书馆办成发扬民族文化、接受外来文明的开放包容的********。服装,有时候就是一种生活态度——这是胡适后来的文友张爱玲说的。
胡适跷着腿坐在茅盾对面,无视后者异样的目光,有点心不在焉地东打听西打听,问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茅盾觉得“很琐屑”,他本来就提不起兴趣,现在见大学者尽问这些没意义的琐事,更觉得没劲,应付了一阵,就走出了会客室。
非常时期的非常之语
胡适见茅盾是在1921年7月18日,在当天的日记里他是这样记载的:“今天我专访了编译所中的熟人,先看傅纬平先生,他是我家兄弟的老朋友,十二年不曾见着了。见李石岑、郑振铎、沈雁冰(茅盾)、叶圣陶。”这一天胡适在商务馆马不停蹄地见了许多人,主要是作礼节性的访问,并没有对商务馆运作情况作深入了解,所以茅盾认为胡适的问话“很琐屑”就不足为怪。通过这次与编译所职员作一般性交流,胡适对他们大致有了一个直观的印象,为他第二次深入交流打下了基础。
三天后的7月22日,茅盾与胡适有了第二次会谈,这一次谈得比较深入,并涉及到文学创作。当时郑振铎和茅盾负责《小说月报》的编辑工作,在这份有广泛影响的杂志上,茅盾多次撰文鼓吹“新浪漫主义”,他在《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主义文学么》一文中这样写道:
“写实主义的缺点,使人心灰,使人失望,而且太刺激人的感情,精神上太无调剂。我们提倡表象,便是想得到调剂的缘故,况且新浪漫派的声势日盛,他们的确有可以指人到正路,使人不失望的能力。”在那一段时间里,茅盾发表了多篇谈“新浪漫主义”的文章。在和茅盾第二次交流时,胡适特地翻了翻《小说月报》。在《小说月报》当年第七期上,一组文章引起了胡适的注意。在与郑振铎、茅盾交流时,胡适还特意提到这个问题,他说:“昨夜我读《小说月报》第七期论创作诸文,颇有点意见。”茅盾不爱说话,听他如何往下说。胡适说:对于创作,你们要慎重,不可滥收,创作不是空泛的滥作,须有经验的底子。
雁冰你不可滥唱什么‘新浪漫主义’,现在的西洋新浪漫主义的文学所以能立脚,全靠经过一番写实主义的洗礼。有写实主义作手段,故不致堕落到空虚的坏处。“茅盾表面上不动声色,事实上他一字不拉将胡适的一番话全记在心里。从1921年《小说月报》第八期开始,”新浪漫主义的呼声消失了,胡适所提倡的自然主义、写实主义占了上风,正是这种创作理念,指导茅盾创作了代表作《子夜》。
十年后,上海滩许多阔少开始流行胡适当年来商务印书馆时穿的那身奇怪服装,茅盾这才发现,胡适不但在文化上,就是在着装上也领风气之先。那时候,他其实在创作上已铭记胡适的教诲许多年。后来在批判胡适时,他说:在1935年我应开明书店的邀约,编一本所谓《红楼梦》洁本,我在前面写了所谓的‘导言’,就完全抄引了胡适的谬论。
我不讳言,那时候,我做了胡适思想的俘虏,我尤其不敢大言不惭地说,今天,我的思想中就完全没有胡适思想的残余了。——非常时期的非常之语,不能说是发自内心,只能说是言不由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