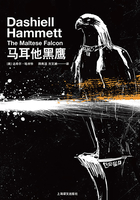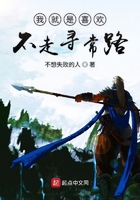我忽然很贱地发现,我似乎连到了这种时候,都难以对他狠下心来。
我把剩下的半块仙贝塞进嘴里,靠着枕头望向天花板。
其实想想,这段时间我都用时间和热情换了什么,除了疼就是疼。
我的手不由自主握住了那条一直戴在脖子上的水滴项链,轻轻摩挲着。
恍惚间我好像又回到了一睁眼就看见病床边坐着季东南的那天,那天也是一样的满室消毒水气味,也是窗帘大开铺着满室的阳光,只是那时的我还没有像现在一样满目疮痍,那时的我还对未来有着满心的憧憬。可现在呢,我早已与梦想中的未来失之交臂,自己依旧固执坚守着的只是一座颓败不堪的废弃城堡。
现在回想起来我依旧不甘,上帝为什么如此狠心,既然终究是要错过,又为何要用如斯梦魇,乱了我原本平静安好的岁月。
“还是别见了吧。”我不知道是说给郭茜听,还是说给自己听,“既然两个人都痛苦,那长痛不如短痛,该断的就尽早断了吧。你替我告诉他,我很好,他的婚礼我可能不能参加了。”
郭茜认真点了点头。
我轻叹口气,把脖子上这段时间无论如何都没下得了手去解的项链取了下来,放进郭茜手里,“还有,转告他,我会过的很好的。”
许鸿恩和方尧很快回来了。
将饮料分给我们之后两个人在沙发上坐下,也加入了我和郭茜的聊天。
聊了一会郭茜和方尧说下午还有事,就不打扰我休息了,又嘱咐了我几句要好好休养。
临走时郭茜过来抱了抱我,轻声在我耳边说,“放心,话我会带到的。”
我拍了拍她的背。
他们走后,许鸿恩看我的眼神一直很奇怪,刻意掩饰着什么。
我被他这样看久了,也挺烦。
下午吃过饭,他摆弄着郭茜带来的花,又用那种眼神瞄了我一眼,我终于忍不住了。
“你饶了这些花吧,它们还是孩子啊。被你折腾的叶子都快掉光了。”
“嗯”他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手上继续捻着花。
我咬了口苹果,一边嚼一边口齿不清地对他说,“我没见他。”
“我没想知道啊。”他还继续摆弄着花,不看我,我知道他是心虚。
“你没想知道你笑得跟嘴部肌肉抽风似的?”我白他一眼。
“啊?我有吗?”许鸿恩一边口是心非一边继续摆弄手上的花。
“是是是,你没有,你的嘴角才没有和太阳穴亲密接触呢。”
我抱着苹果缩着脖子笑他,他伸手就来戳我额头。
一下午就在斗嘴打闹中结束了。
有时候我觉得,这样的日子,也真好。
人生如果没有那么多烦恼没有那么多叨扰该多好,就平平静静简简单单的,和不讨厌的人在一起,每天只考虑些柴米油盐的小事,不卷入大风波也不想着彩票高中头奖,这样的日子,真是连想想都觉得幸福。
后来莫瑶她们也陆陆续续来看过我。
那天莫瑶刚走到我床前,我就迫不及待地把包着纱布的右半边脸凑了上去哭诉,“嘤嘤嘤,人家引以为豪的泪痣都被刮没了。”
莫瑶十分女王气地瞪了我一眼,丝毫不为我的可怜语气所动,“没了最好,我看它不爽很久了。”
我气愤地重重哼了一声,背过去不理她。
莫瑶不客气地从后面推了一把我的头,“我妈给你煲的骨头汤,不喝我全喝了。”
“喝喝!!喝!!”我反身抢过碗,又转身继续甩给她一个愤恨的背影。
你上个月才指着那颗痣说我脸上长得最正的就那一点了什么的,我才不记得呢,一点都不记得了。
后来莫瑶给我带话,说呆毛最近工作忙得脱不开身,让她给我带了束花,说等忙完一定三跪九叩给我老人家请罪。
我说最近又没有两会召开国内也没什么重大新闻,她们报社怎么突然忙起来了。
莫瑶说她也不清楚,好像是本市市内出了点什么事。
我对此表示不感兴趣,挥了挥手大度地免了呆毛的罪。
莫瑶又是一个毫不掩饰的鄙夷眼神丢过来。
一个月后我已经拆了石膏,可以撑着拐杖下床走动了,许鸿恩就常陪我去医院楼下摧残花花草草。
过了几天脸上的纱布也全拆了,这时候倒是不痒了,新肉已经全部长好了,只是右边脸上错落着一块一块与肤色不同的淡粉色皮肤。
我那天照完镜子之后朝许鸿恩潇洒地甩了一下头发,“其实也不难看嘛~”
说着又把镜子拿远了点,“远看都不太看得出来了,以后稍微擦点粉底,肯定看不出来。”
许鸿恩还是笑得一副魅惑样子,“不用化妆,我们小狸也最好看。”
我奖励给他一个大微笑,装作没有看见他藏在背后蜷成青白色的手。
听说我快出院了,护士姐姐们这几天来查房来得比平常都勤,特别是在许鸿恩陪着我的时候。
我耐着性子伸手给她,笑着问,“护士姐姐,我今天还要再测几次心率啊?我是不是得心脏病啦?”
护士姐姐笑得花枝乱颤,“怎么会呢,我们就是例行检查,你别乱想。”说着和蔼地拍了下我的头。
我收回手,拉好衣袖,“那就好,你们医院真负责任啊,每天要例行检查六次。”
护士姐姐拍我头的手僵了僵,“咳,是啊,那、那你好好休息啊,我去隔壁查房了。”
我目送护士姐姐低头快步走出,转眼恶狠狠去瞄一旁憋笑憋得很辛苦的男人。
“都是你!长着一副妖孽皮囊,要是古代早把你绑柴火堆里烧了。”
许鸿恩笑眯眯地拍拍我的脸,“你舍得啊?”
“红颜祸水,朕休了你!”
许鸿恩看我还演来劲了,好笑地走去给我倒水,“好好好,大不了我陪你一起把脸给磨破了。”
说完两个人都是一愣。
他倒水的身影很久没有转回来。
我装作气愤地朝他大吼,“臭妖孽,咱俩这梁子没有一盒马卡龙是解决不了了!”
“买,买,你这辈子的马卡龙我都包了,够不?”
我小人得志,接过水呡了一口,“算你识相。”
喝完水,许鸿恩就被我推着兑现诺言去了。
我早就馋那个小小的软软的玩意很久了,只是每每看到装修精致的柜台里,价格牌上那个豪放的数字,我又却步了。这次终于有机会敲竹杠,当然是早吃到嘴早好。
许鸿恩走后,我又开始摧残这个病房里唯一的娱乐工具:电视。
自从住院以来,这台电视机就光荣地担下了受我蹂躏的重担,谁让我下不了床出不了门,谁让许鸿恩就是不肯让我用电脑,谁让这些破电视台放的都是些雷死人的雷剧呢。
好吧,其实实质上惨遭蹂躏的不是电视机,而是他相好的——遥控器。
上一个遥控器已经在我的咬砸捏掐捶啃摔中悲愤罢工了,现在我手上拿的是许鸿恩偷偷去电器行配的新的。
他当时其实是把旧遥控器偷偷拿去修的,可那师傅检查完之后只是摇了摇头,说,“不行,修不了。”
于是许鸿恩只好破费买了个一样的。
许鸿恩回来之后努力绷着脸把那位师傅在他临走时嘱咐的一句话转达给我,我听完嘴里的牛奶全喷被子上了。
那师傅说,“不在家的时候狗要栓好啊,乱咬东西要管,管不住的时候别心疼,该打还是要打的。”
手机忽然铃声大作,我一看名字,呆毛姑娘终于百忙之中抽到空给我致电了。
“喂。”
“小狸啊,你没事吧?”呆毛的声音显得小心翼翼。
“我挺好啊,都过这么久了。”
电话那边似乎松了口气,继续说,“那就好,你爸爸这事我也刚知道,你想开点。刚刚上面下指示了,你爸这篇稿子不会见刊,所以你也别担心,我觉得既然有人施压,媒体这方面压下来了,事情就肯定还有转还的余地。”
“什么……?”我听得云里雾里的,“我爸什么?”
“你、你别告诉我你还不知道……”
“我应该知道什么?”突然的,我心里有种十分不祥的预感,呆毛接下来的话,也许会颠覆我这段时间以来所有的想法。
“你爸爸好像……被抓了……小狸你别急啊,我刚刚不是说了么,这事还没钉死,哎哟都是我这八婆嘴,没事找你瞎说什么……”
她后面说什么我已经听不见了,我只记得我懵懵地求她把那篇被毙了的稿子发给我看,之后就挂了。
我拖来许鸿恩藏在一边休息室里的笔记本,登录了邮箱。
等邮件的时间简直度日如年,每一秒我脑子里都像有一口大钟在敲,嗡嗡地疼。
终于邮件进来,我打开扫了一遍,看到了几个关键词。
挪用公款,半个月后开庭,社会贤达联名写信保释,政坛名流陈少华声援。
陈少华……陈少华……
名字有几分眼熟,总觉得在哪里见过。
印象实在太浅薄,我便百度了一下。
扫了眼资料,脑子里瞬间出现了什么,闭着眼睛想了半天,终于抓住了那缕一闪而逝的回忆。
他不就是曾经在扒付烟家世的那个帖子里出现的“在N市政坛混得风生水起”的小舅舅吗?
付烟的亲人,这让我不禁联想到了什么。
当所有线索都成功串联起来后,我只感觉脑子一瞬间就空白了。
难道……季东南和付烟那场疑点重重的订婚,竟然是为了我爸?!
人生就像心绞痛,每当你觉得自己已经疼到麻木的时候,总能有的一波疼痛清晰地告诉你,一切都还没有结束呢。
门被推开,许鸿恩拿着一个精致的小盒子站在门口,正准备开口责备我怎么又偷他电脑来玩时,看到我的表情时又突然收了口。
“许鸿恩,我爸爸他……他好像出事了……”
他没有接我的话,只是迅速低下头去,眉头紧皱。
我看着他的表情恍然大悟,一下倒回枕头上,盯着天花板半晌,突然笑了出来,“原来你早就知道了啊……”
什么时候起,我已经被这些事磨得连放声大哭都做不到了。
我靠在床头,嘴角依旧挂着笑,鼻子却止不住地酸,脸上凉凉的,怎么擦也擦不干净。
许鸿恩把小盒子放在我的床头,转身走了。
关门的那一刻他似乎有几分挣扎,最后还是一句话也没有说,轻轻掩上了门。
我躺在床上,愣愣地想,走到最后,这条路还是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出院那天,碧空如洗,日丽风清,是一个月来难得一见的好天气。
来接我的只有我妈和莫瑶,我想对她们笑,可是嘴角像是挂了千斤坠,怎么都扯不起来。
老头开庭就在一周后了,这段时间我没有去找过季东南,临近开庭,他肯定有很多要忙,虽然跟他的帐还没算清,但我还可以再等一等,等一切尘埃落定也不迟。况且,我也还有很多事情没有想清楚。
许鸿恩在那次之后就很少出现了,也似乎也在忙着什么。
其实他每次疲惫着脸出现在我面前,又迅速消失的时候,我很想叫住他,告诉他我原谅他了,只是几次都没开得了口,心想这些事都先放一放吧,等老头的事结束了,一切从长计议。
我妈也是早知道这件事的,看莫瑶的反应,她也是知道的比我早的。
算来算去,到最后被瞒在鼓里的,居然只有我一个人。
这是我的人生啊,凭什么你们一个一个的都争先恐后地替我做决定呢,承担或者逃避都是我该做的选择,这样连选择的机会都不给我,你们真的是在帮我吗。
你们一个个打着保护的幌子对我施以极刑,不过都仗着我爱你们罢了。
爱这东西,真说不清楚。
回家之后我有次问我妈,老头开庭你去吗?
她答,不去了,早不关我的事了。
我又问,你还恨他吗。
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她答,恨,我会恨一辈子。
她说话时候的那种表情,好像随时都做好了准备要说这句话一样。
无论是爱还是恨,一辈子都是沉重无比的词,可她竟然就这么轻描淡写地就把一辈子加诸在了一个人身上。
妈,真的只有恨吗?
我自己呢,真的只觉得恨他替我做了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