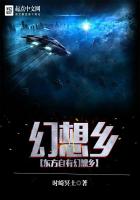“年深日久若无情,笑面多言皆可恨”
-
临近用药,夜间又焦躁难眠起来。没睡几个时辰,东方初亮就醒了。一大早,刚用完朝饭,上官柳儿就登门。待几人在正堂落座后,上官柳儿便急切地问我道:“青州来的那三个挝鼓之人,在刑部大牢被杀了,先生可有耳闻?”
“昨日珠玑姑娘回来,已经与我说了此事。听说一同被杀的还有‘武生堂’的掌柜崔武生,不知此事可是公主所为?”我反问道。
我本想上官柳儿会承认,却不想他却矢口否认道:“并非我等所为,公主也是昨日事发后才知晓。”
“哦?听说一同被关的‘长生堂’掌柜段瑰却没有丝毫损伤,难道是段瑰安排人做的?”我故作不知,再问道。
饶阳公主听完,又否认道:“不会!段瑰手底下,没有这样的人。我想此事可能是刑部和那个老阉人做的,目的就是要嫁祸给‘长生堂’。”
“‘长生堂’本就犯下了滔天大罪,刑部为何还要这样做?”我心中想笑,但还是表露出不可置信,对上官柳儿问道。
上官柳儿急忙对我解释道:“先生,这还不清楚吗?一定是刑部撬不开段瑰和崔武生的嘴,想以此为要挟,让段瑰开口指认背后主使之人。”
若真是想知道背后主使之人,刑部更应该留下崔武生而杀掉段瑰才是。哼,上官柳儿还真是说谎都不先试试咸淡就端上桌,真把我当没有味觉的傻子一般糊弄。既然他要糊弄我,我也糊弄他好了。于是,我接过话道:“所以,姑娘今日前来,是让尚某想想办法,阻止刑部,对吗?”
“先生灵犀之人,公主让奴家过来,正是此意。想着先生虚室生白,定会有神谋妙策,一解此困。”上官柳儿谄媚模样,对我柔声娇语地回道。
若非知道他真实模样,还真会被他迷惑。不过一想到他的真容,再看他此时的媚态,就不由自主地在心中作呕。为了让自己不会真的呕出来,遂赶紧堆着假笑,回他道:“姑娘过誉了,尚某才疏智浅,自当悉心竭力。此事其实不难解,就看公主舍不舍得了。”
“先生是已经胸有成竹了吗?不妨说来,奴家洗耳恭听。”上官柳儿露出悦色,急不可耐地想知道。
我便笑着对他说出心中所想:“既然刑部可以杀了崔武生,那饶阳公主也可以杀了段瑰。这样,刑部就算想查,也查不到了。不过要牺牲一颗摇钱树,就不知公主舍不舍得了。”
“倒是没什么舍不得,只是此刻,刑部已经加强了戒备,很难再有所动作了。不知先生可有其它法子?”上官柳儿听完我说的,便皱起了眉头,又问道。
“姑娘说得有理,是在下思虑不周。且容我再想想······”我对上官柳儿道歉说,接着故作思虑状,假装盘算着,片刻之后自言自语道:“若是公主此时能说动陛下就好了······”
“先生说什么?”上官柳儿假装没听清,问我道。
我明明说地那么大声,他居然装作没听清,于是我在心里笑他虚伪。看着上官柳儿,我笑着答道:“哦,没什么。心中想着一些事,不由自主地说了出来。到底是不够成熟的计谋,不敢在姑娘面前胡言。”
“先生是想到些什么吗?不妨说出来,或可行也不一定。哪怕不可行也不打紧,奴家断不会求全责备。”上官柳儿颇为恳切地说道。
我故意叹口气,说道:“哎,好吧。既然姑娘都这样说了,尚某便仗着一点挈瓶之智,说与姑娘参详。在下回想那日公主的态度,似是有意保全崔铉,因此断不能将崔铉再推出去顶罪了。可此事若真被鱼弘志和刑部一查到底,必然会查到崔铉头上。若是想让他们罢手,只得陛下开口才行。就是不知,公主和陛下的关系可还算亲近?”
“陛下乃是公主的皇兄,自然亲近。”上官柳儿毫不犹豫地答道。
听完,我装作松了口气,笑着继续说:“哦,那便好。如此可让公主去陛下面前诉诉苦,设法让陛下同情公主。从而使陛下肯去授意鱼弘志点到即止,不要继续查下去,尽快了结此事。倘若陛下不为所动,那便将实情告知陛下。我想,陛下为了公主,为了皇家的颜面,也一定会这样做的。”
“先生有所不知,此事如今已天下皆知,只怕陛下也不得不给朝堂和青州的百姓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才行,因此未必肯从了公主意愿。”上官柳儿忧虑地对我说道。
我笑道:“人们只知‘长生堂’和‘武生堂’兜售假药,却不知这两个铺子是崔铉管着的,更不知是公主的产业,如此岂能算天下皆知呢?只要公主肯舍弃‘长生堂’和‘武生堂’,将这两个铺子推出来接受刑部的惩治,并且做好善后事宜,这件事也算对天下人有个交代了。若卫国公对此还有微词,那就问问他,青州一案的源头是什么。此事的起因说起来,还是青州刺史和寿光县令因为渎职而酿成的洪灾,若没有洪灾也就没有‘假药’一事。卫国公身为宰辅,怎可只追究‘假药’一事,却放任官员渎职而不顾。至于鱼弘志的嘴,就要交给陛下去堵了。”
“先生如此说,倒也在理。可鱼弘志向来跋扈,只怕陛下,未必能堵得住鱼弘志的嘴。”上官柳儿若有所思地说道。
我端起案几上的茶,喝了一口。轻轻放下杯盏,接过话道:“前段时间不是闹着要立太子么,若是陛下连鱼弘志的嘴都堵不上,还怎么放心让杞王接过自己的位子。”
“先生的意思是?”上官柳儿不解地看向我,问道。
真是笨地出奇,非得说直白些。没办法,那就说吧。我遂同上官柳儿解释道:“一方面可以用此话来说服陛下,倘若鱼弘志真的不把陛下放在眼里,那鱼弘志留下便是祸害。另一方面提点一下鱼弘志,若此刻对陛下不敬,将来陛下定会因为忌惮他,而放弃杞王。如此,我想陛下一定会借这个机会试探鱼弘志一下,而鱼弘志也会‘知趣’的退让三分。”
“先生所说确实能达到目的,只是奴家怕此事过后,陛下真的选了杞王做太子。”上官柳儿愁眉不展地跟我说道。
我心里笑他眼界太小,却又不得不劝服,便急忙回道:“姑娘,此刻顾不得那些了,还需先解了眼前困局才是。至于立太子之事,既然陛下有意推迟,便不急于一时,今后还有回旋的余地。可段瑰眼下就在刑部大牢关着呢,此事迫在眉睫,说不定什么时候段瑰扛不住就松了口。到那时,再多筹谋,也是枉然了呀!”
“先生说的是,是奴家一夕千念,乱了思绪。此事若如先生所谋,奴家定要跟公主多讨要些赏赐,好好犒劳先生。就是不知,先生想要什么赏赐呢?”上官柳儿又娇媚起来,扭捏地问道。
我听完,装作受宠若惊的样子,站起身,作揖行礼道:“尚某一介布衣,误打误撞,投入姑娘檐下。既然姑娘是为公主做事,那尚某为公主谋,便与为姑娘谋无异。这本是尚某分内之事,岂敢讨要赏赐,更不敢劳烦姑娘为在下开启尊口。”
“先生不必惶恐,这也是公主的意思。那日与先生相见以后,公主便属意奴家,不可怠慢了先生。先生若是拒了,不知是要与公主撇清干系,还是想与奴家和而不同呢?”上官柳儿用凌厉的言语胁迫般说道,眼神中露出蚀骨的寒意,而嘴角却还保留着笑容。
我无奈,却不得不做出诚恳的样子,可心里又确实不知道他能给我什么。转眼看到站在他身后的珠玑,便对他说道:“尚某绝无此意,若公主施恩,在下断不敢不受。只是在下想要的,怕是姑娘不肯给。”
“哈哈,先生且说来便是,若是奴家有的,必定毫无犹疑的奉上。若公主的物件,我也定会为先生诚心讨要。”上官柳儿肆意地笑起来,大方地说道。
我听完,便盯着珠玑,露出淫色之态。假装顾不上看上官柳儿,对他回道:“不知姑娘可否将珠玑赏赐给尚某?”
“呵呵······”上官柳儿看着我如此之态,轻松地笑了起来。接着看了看身后的珠玑,对我答道:“他不是已经给先生了吗?”
“珠玑只是在尚某身边服侍,到底还是姑娘的人,在下岂敢逾矩。今日所求,是想姑娘能将珠玑的贱籍划与我,如此我便可名正言顺的将他留在身边了。就是不知,姑娘可舍得?”我痴痴地望着珠玑,继续问上官柳儿道。此刻珠玑一脸难堪,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低着头,像个任人摆布的木偶。
上官柳儿倒是依旧轻松地对我说道:“既然先生开了口,奴家自当照办。不过他可没有贱籍,还是良人。只不过当初签了典身契,等此事了了,奴家便将他典身契给先生送来。”
“那尚某便提前谢过姑娘的恩赐了!”我又作揖行礼道。
上官柳儿魅惑地笑着对我说道:“先生无需多礼,这是先生应得的。且先坐下叙话,奴家还有一事要请教先生呢!”
“姑娘还有何事,尽可直说。尚某定殚精毕思,庶竭驽钝。”我边跪坐下,边喜悦地对上官柳儿回道。
上官柳儿倒是不着急,对我轻柔地说道:“其实此事,事发突然,奴家也不知如何跟先生说。”
我心中想着:既然不知道怎么说,你倒是别说呀!惺惺作态······
“可此事要紧的很,若不说,奴家又没个主意,所以还请先生听我聒噪几句。”
我心中不耐烦地想:赶紧说吧,真是墨迹,扭扭捏捏故作媚态给谁看?!
“事情是这样,河朔三镇早先我们丽景门都派人去了。这三镇本已被我‘丽景门’牢牢控制着,可前段时日却不知为何,派去的人都被发现,让人除掉了。而昨日,兖王生辰,河朔三镇居然都送上厚礼,只怕是······”
“皇子生辰,藩镇送些寿礼过去,也是人之常情。姑娘会否多虑了?”我假意问道。
上官柳儿忙回道:“先生有所不知,这三镇往年从不将这些皇子放在眼里的,今年却给兖王送上厚礼,还是在我的人被除掉之后,只怕是有投靠兖王的意思。”
“姑娘是否会错意了?河朔此举会不会只是为自己留条后路?前些时日立太子之事一闹,只怕此刻人人都会为自己的将来筹谋一番。河朔此时对皇子露出善意,可能就是为自己留着后手,并非投靠之意吧?我猜只要是皇子,他们都会送礼,而不是刻意选择的兖王。无论杞王、益王,还是德王、昌王,若此时生辰,我想河朔都会备上大礼吧?!”我还是假装不可思议,怀疑道。
上官柳儿却坚持地说道:“正因此时,河朔三镇给兖王送礼,才更表露出投靠之意。先生想想,在议储君人选的档口,河朔三镇如此大张旗鼓地给兖王送礼,不就是告诉其他人,他们的选择吗?”
“姑娘这样说,尚某倒是也不敢不信。若真如此,姑娘希望尚某朝哪个方向为姑娘谋划呢?”我勉强地问上官柳儿道。
上官柳儿试探着问我:“不知先生可有法子,让河朔三镇回心转意,重新听从我‘丽景门’的号令呢?”
“姑娘派去的人都被他们除掉了,单凭尚某一己之力、榆枋之见,实在难有不拔之策。”我面露难色,对他回道。
上官柳儿遂又问道:“那先生可有法子,让河朔三镇断了投靠兖王的念头?”
“姑娘的意思是想让河朔三镇投靠杞王?难道当初尚某之言,姑娘和公主竟都没听进去吗?还是要送杞王坐上太子之位?”我有些不解,还有些气恼地质问上官柳儿。
上官柳儿见我恼怒,忙解释道:“先生,奴家并非此意······”
“既然不是此意,那为何要弃兖王而助杞王?”我没等上官柳儿说完,便打断他,继续质问道。
上官柳儿忙说:“先生想错了,奴家不是让先生将河朔三镇推给杞王。”
“不是?那姑娘此举是何用意?”我纳闷地看着上官柳儿,接着问道。
上官柳儿又说道:“至于此举的因由,恕奴家不便透露,还请先生见谅!”
我抬头,长叹一口气,皱着眉头回上官柳儿道:“也罢,既然姑娘不便说,在下也不再打听,我自尽心谋划便是。说起来,河朔三镇有投靠兖王之意,也怪当初我猜出兖王阻止鱼弘志出兵讨伐河朔,却没有及时阻止。”
“此事怪不得先生,那时河朔还在‘丽景门’的掌控之中,也不知会发生后来的事情。还请先生莫要为此自责!”上官柳儿此刻倒是假装安慰我道。
“呵呵···”我冷笑一声,接着说道:“姑娘当真只想将河朔拽在手中吗?殊不知,河朔三镇对公主和姑娘来说,就是个烫手的烙铁。若有把柄便是利器,若没有把柄,也是会烫伤自己的。”
上官柳儿听完我这样说,皱起眉头,好奇地问道:“先生此话何意?”
“河朔手握重兵,是鱼弘志的眼中钉、肉中刺,鱼弘志对他们欲除之而后快。若河朔能恭顺听话,那姑娘和公主自然有办法很好的保全他们。可若河朔不能俯首听命,姑娘和公主将他们强留于手中,只会被鱼弘志时刻盯着。更进一步说,倘若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鱼弘志以神策军拥立新君,首先要针对的便是公主和姑娘的‘丽景门’。到那时,远在河朔的三镇军队,即便挥师西进,只怕一时间也鞭长莫及。就算命令河朔提前行动,河朔三镇却也未必肯如此做,毕竟他们连陛下的圣谕都听不进。”我头头是道地对上官柳儿胡诌道。
上官柳儿糊里糊涂地点着头,接着问:“依先生之见,河朔可不动?”
“说到底,河朔三镇不过是军方的一个象征罢了。既然是象征,只要他们起到有利于姑娘和公主的作用就行了,无论摆在哪儿都一样,何必一定要他们俯首帖耳呢?我看兖王就不错,若河朔真有投靠兖王之意,那必然会分走鱼弘志的注意力。若是公主也能对兖王表面上支持一下,鱼弘志一定会将注意力从公主身上转移到兖王身上。更重要的是,从此兖王就有了和杞王一较高下的资本。若将来筹谋得当,兖王登基,公主便是拥立的第一功臣。退一步说,即便兖王没有成功,鱼弘志拥立的杞王上位了,公主和姑娘也有回旋的余地。只要对新君称臣,便不会有倾覆的风险。所以,依在下愚见,完全没有必要对河朔三镇属意兖王一事加以阻拦。当然若姑娘执意要横生枝节,尚某遵命便是,定会竭力筹划。只是无论如何筹划,都很难再让河朔三镇回心转意。尚某才乏兼人,还望姑娘和公主见谅!”我对上官柳儿继续糊弄道。
上官柳儿不置可否,只得回我说:“先生所言,也不无道理。且容奴家回去与公主仔细权衡,待商榷妥帖后,若有需要,再来问先生对策。今日还有琐事在身,就先回了。”
“那尚某便先独自思谋,静候姑娘差遣。”我站起身,边说着,边对上官柳儿行礼。
上官柳儿说着也起身,朝我走来。来到我跟前,扶着我作揖的手,妩媚地说道:“先生近些时日,身体可好些?柳儿百无一用,也不能替先生解了这毒。每每想到此处,柳儿便禁不住垂泪,心中万分的愧疚。”
说着说着,竟然装模作样的要哭起来。我实在受不了,忙抽出手,对上官柳儿躬身行礼道:“好在有姑娘准时赐药,尚某身体尚可。无以言谢,唯有躬身听命,不敢劳姑娘挂怀!”
“这几日虽暖和些,却到底是冬日,依旧寒冷。先生且歇息去吧,不必送奴家了。”上官柳儿对我柔声细语说道,接着转身对珠玑说:“珠玑,你可要好生侍奉先生,这往后更要‘尽忠竭力’,与先生贴心才是!”
傻子都听得出来,“尽忠竭力”几个字说地与别的字不同。上官柳儿说罢,便扬长而去了。我对着上官柳儿背影,再作揖行礼道:“姑娘慢走!”
待上官柳儿走远,我回过神来,看到站在一旁的珠玑,忙对他行礼道:“方才尚某轻薄之态,实属情势所迫,望姑娘见谅!”
“诗岚惶恐,先生何须如此?!诗岚虽愚钝,可也并非不通情理之人,怎会不知先生好意?!先生万难之中还为诗岚谋划,诗岚尚未道谢,先生岂可自责?”珠玑一边扶我,一边激动地对我说道。
我望着珠玑,却见他眼神中只有感激,心里顿时失落。不由自主地,独自在心中叹道:
庭院深深深几许,重门紧闭不知途。
斜阳浅立无人影,此处幽幽困若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