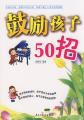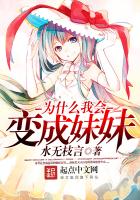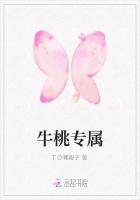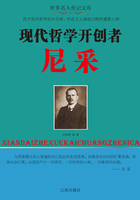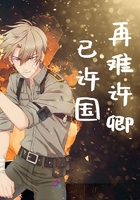互联网第一次使我们的生存环境变成了充满现成答案的世界,
几乎没有事情不能从网上获得解答的。
大多数家长没有考虑到这样的环境对孩子成长的恶劣影响,
把网络视为万能,
习惯了现成答案的孩子就丧失了独立思考、创造的动机,
更难以养成质疑的习惯。
圣诞节:我向女儿道歉
2010年圣诞节一大早,11岁的女儿像往年一样,兴冲冲地冲到圣诞树下,一包一包地打开自己的礼物。等我醒来时,她第一句话就问:“爸爸,那本《波西·杰克逊》真是你送我的?”
“噢,那当然算是我送的,不过是妈妈挑的。”
女儿继续笑嘻嘻地观赏着自己的礼物,我再一回味,心里不免一颤。圣诞节给孩子送礼,我们是入乡随俗。毕竟女儿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最喜欢过的节日就是圣诞。她早就知道圣诞老人是个虚构的童话,但一直装作不知道,不肯捅破这层窗户纸,希望父母每年还会上演这美好的戏剧。当然,随着她的长大,大家不再可能假戏真做了,但圣诞礼物这个大节目谁也不忍心取消。她生活的头几年,我们生活很困顿,不得不省吃俭用。妻子统筹管理圣诞礼物,经常在圣诞节刚过大甩卖时,以十分之一的价格购买过时的礼物,藏到来年送给女儿。虽然家贫,但因为女儿有这么个好妈妈,每年的礼物还是颇为丰盛的。当然,也正因为如此,妻子在礼物问题上一向不准我“瞎买”,全由她统一经营。这次买《波西·杰克逊》,当然也是她的主意,她和女儿经常交流小说,知道女儿最喜欢什么。我则在这方面一概不懂,难怪女儿拿到礼物一眼就看出来。
本来这是小事一桩。不过我这当父亲的未免神经过敏,马上想到一个讲寄宿学校孩子生活的电影。其中一个男孩儿生日时独自在校园里面对月色流泪,朋友跑来问他怎么了,他沉默不语,最后指指地上一包贵重的礼物,说是父母送的,和去年的一模一样,然后又仿佛是为父母辩护:“他们也许太忙了。”很明显,这种家境富裕的家庭,父母无心管孩子,将之送进贵族寄宿学校,每年送生日礼物都不过脑子,结果让孩子觉得世界上没有人关心自己……
我回味着这一幕,不禁为自己惭愧起来,赶紧走到女儿的房间,向她解释了家里的贫困历史和由妈妈统筹安排礼物的原因。女儿当然很能理解,不过我还是道歉说:“爸爸、妈妈不是在美国长大的,对圣诞节没有你那样真切的感情,没有把圣诞礼物看得那么特别。爸爸只想让你知道,你从来都是爸爸心中最重要的人。看看,前几天爸爸不是给你买了《荷马史诗》吗?爸爸只想让你早点读,等不到圣诞的时候才给你,笔记本电脑也是如此呀。不过,爸爸确实应该理解,圣诞对你特别重要,爸爸以后应该亲自给你选礼物才是。”女儿立即上来给我个拥抱。
确实,我提到的那两样礼物,都说明了我对女儿的理解。她喜欢写作,特别用功,我就给她买了个笔记本电脑。而让她最高兴的,还是那本《荷马史诗》的全英译本,是精美的真皮封面,如同一件艺术品。女儿正对希腊神话上瘾,刚拿到这件礼物时,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一步不离,这可是我的得意之作。可惜,这样的东西,在我的圣诞礼物中一件也没有。
父母送孩子礼物,其实并不是简单地送一件东西而已。礼物应该体现父母和孩子的共同经验,表达了父母对孩子的理解和关爱。这是钱买不来的东西。敏感的孩子,到了十一二岁就能够通过小小的礼物感受到这些。可惜的是,父母因为各种生活的压力,往往忘了从孩子的角度思考这些问题。真要是那样,礼物就和商店货架上的物品没有两样,只不过父母同意花钱买了而已,这种没有对孩子的理解和关爱的礼物,也自然把童年和节日都物质化了。
我在圣诞的“礼物门”后,马上到亚马逊上给女儿订了盘肖邦第一和第二钢琴协奏曲的二手光盘,连运费加起来不过五美元多,这是波兰钢琴家齐默尔曼(Zimerman)和意大利裔著名指挥家朱里尼(Giulini)20世纪70年代末录制的天作之合。我和女儿都是肖邦迷,这两部协奏曲听了无数遍,都认为Zimerman是肖邦最好的解读者,而且比较了他的几个演奏,包括最近亲自指挥而被热捧的版本,但没有一个能超越这一70年代末的经典。我对女儿开玩笑说:“只要是圣诞节那天订的,就算你的圣诞礼物了。”看着女儿会心的笑容,我不禁又回到父女俩躲在车里听完Zimerman后才肯出来的情形……
我用了八年时间回答了3岁女儿的问题
我静悄悄地走进女儿的房间:“宝宝,你有几分钟的时间吗?”
“我不能肯定,”女儿的眼睛依然盯着计算机屏幕,“我必须完成作业。”
“可是,爸爸有件事情想和你谈一下,也许只需五分钟的时间。”
“什么事情?”
“你3岁的时候问过妈妈一个问题,我们一直都没能回答你,现在已经八年过去了,很抱歉,也许我们都有点懒,没有太多地去想,不过我现在终于觉得有了点线索。也许我们能够讨论一下,一起找到答案。”
女儿把目光从计算机屏幕上移开,注视着我。11岁的她,已经是个很善解人意的孩子了。
3岁的时候,她刚刚接触芭蕾,一下子就迷上了,哪怕进了家商店,也要找块空间跳起来,嘴里哼着舞曲。不知有多少时候,路人被她稚嫩的舞姿所吸引,停下来为她叫好。一次,她坐在童车上问妈妈:“芭蕾是这么美,第一个芭蕾舞家是从哪里学来的?”
妈妈又惊又喜,骄傲地把这个问题转达给我,这个问题也成了我们家庭的骄傲。我们告诉了许多朋友,多少有些炫耀:看我们家的宝宝多聪明!女儿的芭蕾天赋也确实是出类拔萃的。如上所述,她6岁就上了波士顿芭蕾舞团的芭蕾学校,7岁被挑为小演员,参加了该团那年圣诞节《胡桃夹子》的演出。可是,对她的这个问题,我们则从来都没有回答。
我一向认为,孩子是天生的哲学家,孩子们的问题往往是最深刻的哲学问题,对孩子一定要敬畏。但是,也许是太敬畏了,我总觉得回答她的问题超出了我的能力,没有尽最大的努力去思考,怕一个平庸的回答辜负了她。现在看着她一天天地长大,已经开始读《荷马史诗》的全译本,讨论的事情也越来越复杂。当父母的,如果对这样的问题居然也不试图回答,是不是也太不负责了呢?
于是,我开始努力认真地思索答案,并不停地回顾父女之间这些年的思想交流,希望最终找到的答案既反映了我思想的努力,也能整合她的经验。出人意料的是,我居然很快找到了线索,我甚至后悔没有早一点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耽误了和她进行思想互动的机会,这也是我为什么匆匆打断她做作业的原因。
现在父女面对面地坐定,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对方,我可以开始了。
“你当初问的是第一个芭蕾舞蹈家从哪里学的芭蕾?你是否想过,第一个芭蕾舞蹈家所跳的芭蕾,和你现在看到的芭蕾(比如《胡桃夹子》中的那种芭蕾)是一样的吗?”
“噢,这个我还真没想过,”她沉吟一下,含含糊糊地说,“应该是一样的吧……噢,不对,恐怕不一样。”
“那我们怎么判断这个事情呢?有没有别的例子?比如,第一个钢琴家从哪里学的钢琴?”既然女儿学了多年钢琴,我就把问题转移到钢琴上来。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比如那些早期的钢琴家,巴赫、莫扎特……”
“他们弹的钢琴一样吗?”
“噢,我知道你问的意思是什么了。”她眼睛亮起来,“巴赫弹的是古钢琴,莫扎特弹的则是现代钢琴了……”
这一下,我们的讨论顿时热闹起来,我们都记得她一年多以前弹巴赫时的经验。巴赫还处于古钢琴时代,对刚刚出现的现代钢琴还有些排斥,他的作品也大都是为古钢琴而写的。古钢琴没有现代钢琴那种踏键,踏键的重要功能就是把琴键上弹出来的音延长,增加了钢琴的表现力。当然,现代钢琴的每个键对手指的轻重都有敏感的反应,弹重了声音就大,轻了就小,这就给演奏者更大范围的表现力度,也是古钢琴所不具备的。女儿当时在现代钢琴上弹巴赫的曲目,充分利用了现代钢琴的踏键功能和力度,曲子自然起伏跌宕。演奏完后老师鼓励一番,然后问:“巴赫自己是这么弹这个作品的吗?”“不是。”在场的许多孩子都立即回答出来。“对,他不会有这些力度,不会用踏键。但是,如果他活在今天,他是否会采取这些技术呢?”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最后老师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意见:“我相信他还是会用的,在他那个时代,这些技术都还不成熟,他只能在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下力图达到完美。如今有了这些技术,他的表现空间更大了,他为什么不用呢?”
女儿当然和老师不谋而合,所以才会那样弹。我把这个议题带回我们眼下的讨论中,女儿一下子有了新的反应:“啊,也许所谓‘第一个’的概念就不对,根本没有所谓‘第一个’。”
“从理论上说,也许应该是有‘第一个’的。”我不希望她这么快就达到结论,继续说,“但是,所谓‘第一个’,至少是我们现代人的定义,比如,巴赫弹的是古钢琴,古钢琴不是现代钢琴,所以巴赫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钢琴家。莫扎特也许是我们知道的最有名的‘第一个’吧,但是,有巴赫的作品在那里摆着,现在你也觉得那是钢琴作品,怎么能说莫扎特是‘第一个’呢。”
女儿从椅子上跳起来,找到纸和笔,马上给我上了堂图说钢琴史:古钢琴的结构是什么样的,为什么音很难拖长,为什么先进的古钢琴也有重音轻音之分,但需要不同的琴键弹出。现代钢琴是什么样的,踏键怎么工作,为什么现代钢琴每个键都能有丰富的表现力度……直到我这个音乐的门外汉听得脑子发麻,为了避免被她“灌输”,我立即“撤退”到自己的老本行中“固守”:“你看希罗多德是不是‘第一个’历史学家呢?”
众所周知,希罗多德在西方被称为“史学之父”。女儿喜欢希腊神话,自己读起《伊利亚特》来。我为了引导她对历史的兴趣,给她一本希罗多德的英文全译本,她看了十几页,但还是觉得自己正读着的那些小说更有意思,就放下了。不过她曾颇有兴趣地和我讨论:“希罗多德和现代作家很不一样,他每讲一件事情,总爱说‘听什么什么人说’、‘按照某某的说法’等等。”为此,我们曾经反复讨论了历史的叙述者和被叙述的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需要另文详细介绍。如今讨论到这个地步,希罗多德又一次派上了用场。于是,我不等她回答上面的问题,就把自己的思路又推进一步:“看看,大家称他为‘史学之父’,那分明指的是他是‘第一个’历史学家。爸爸教历史,按说爸爸的行当就是他创造的。”
“那么他确实是‘第一个’了?”女儿并不太确定。
“可是,为什么他书中总说‘听某某说’呢?”
“噢,”女儿恍然大悟,“他也是听人家讲的,就像口口相传的《荷马史诗》一样,未必是一个人写的。”
“书还是他写的,但是,在他之前就已经有了口口相传的历史,那些告诉他这些历史的人,是否比这位‘史学之父’更是‘第一个’呢?”
“是呀,那些人是更早的历史学家,我们根本无法知道谁是‘第一个’。我们只是因为自己对过去的事情知道得太少,所以为了方便,在自己开始知道的点上定义出一个‘第一’来。”
“那么谁是第一个芭蕾舞蹈家呢?她跳的是什么样的芭蕾?”
女儿笑起来。
这样,父女俩讨论来讨论去,都觉得很难有确定的答案,但至少发展出一个可以接受的假说:不管是芭蕾也好、钢琴也好,还是历史也好,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都是经过人类一代又一代的努力不断完善起来的。在起点阶段的形态,和现在的形态一定是很不一样的。比如,巴赫还在弹古钢琴,基本没有运用现在的琴童所使用的很普通的技术。希罗多德以前,“史学”还是人们口口相传的故事,是他先记载成书,形成框架,使散乱的传说有了系统。芭蕾最初是什么样,我们更不知道了,也许比现在粗糙得多,也许对现在的芭蕾舞爱好者们来说也是一种难以辨认的舞蹈形式了……
那么,女儿从这种讨论中学到了什么呢?老实说,我自己都很难判断,她在日后的生活和学习中,对这些讨论所涉及的问题也许会不停地作出自己的解释。但是,我有限的目的还是达到了:我希望她看到,她所继承的人类文明,并非某个天才一夜之间突然发明的,而是人类经过多少代的努力不断完善的,要敬畏这种文明的遗产,而不是盲目崇拜个人。同时,她也应该意识到,每代人都有责任把自己所继承的东西再完善一些,向前再推进一步。女儿一直有“要创造一种有持续影响力的东西”的志向。我则希望她明白,这种“创造”即使看起来像“横空出世”,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站在巨人的肩头”。我相信,这样的理解对她一生都有好处。
作为父母,我自己从这一经验中学到了什么呢?我觉得,对孩子要不停地激励、启发,但是,我不会找出什么“名人名言”作为她的座右铭,我不愿意对她灌输一些外加的概念和思想。家长最重要的职责是回答孩子的问题,这就像孩子饿了你给她饭吃、渴了给她水喝一样。从我回答她3岁时的问题花了八年时间的经历看,做到这一点实际上非常困难,她还有许多问题我根本没有回答,父母非竭尽全力不可。如果父母偷懒、不顾孩子是否有食欲而强行喂食,那么这种填鸭式的喂养最终会毁掉孩子的胃口。所以,我教育女儿是跟随着她内在的精神动力走,这样的过程有时也会回到某些“名人名言”所讲的道理上。但是,她以这种对话、讨论的方式理解这些道理,自然也要深刻得多。我也劝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当你们拼命给孩子灌输知识,并抱怨孩子没有尽最大努力时,不妨也问问自己:孩子自出生以来问的许多问题,你们回答了多少?回答得怎么样?你们为此作了多大的努力?
怎样教女儿学历史
年轻时,我相当迷信“家学渊源”,这大概和自己的“文化自卑”有关。父母都是没有上过大学的“革干”——“文化大革命”期间下干校,把我们兄弟三人留在北京,交给一位不识字的“大娘”照看。他们回城后多忙于工作,早出晚归,即使读过些中央文件,在孩子面前也都不谈国事。教授的家庭是个什么样子,让我感到神神秘秘。文化界的“硕学鸿儒”给孩子们打下了什么样的童子功,更超出我的想象。后来阅历渐长,见到许多“硕学鸿儒”的子弟也不过尔尔,甚至相当令人沮丧;而平民百姓家庭,却频有秀异之士。对“家学渊源”的迷信也就渐渐崩解,深信除了音乐等几个需要早期强化训练的领域,“家学”并不是构成个人事业成就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