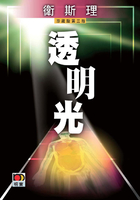夜色越来越浓了,天空中的星星也越来越密集。有一颗星,周围像是沾满了霜花,散发着逼人的寒光,冷冷地望着大地。此刻,河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了,台地上的古道渐次变得模糊起来,村子周围的环境只能凭白天的经验去判断了。风从享堂峡谷带来一阵阵淡淡的芬芳和湟水低低的歌吟。就凭这感觉,马长存缓缓地往前走着。那丝丝缕缕飘忽不定的声音,给了他些许的慰藉。
“咕——咕”,湟水发出了清晰悦耳的声音,那声音唤起了他的回忆。此时此刻,马长存又想起了刘亮。这种回忆虽然缺乏一定的逻辑性,但很自然。因为他的过去,他当书记的几十年,确切地说,他在村子里权威的逐步形成,以至越级直接去县上请示汇报工作,都跟一个人有密切的关系,这个人就是刘亮。
一九六六年,是个动乱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阴雨连绵的早晨,县上的造反司令部给大队送来一张条子,说要批斗反革命,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必须来,谁不来谁就是不支持革命。他早就听说县上有这么一个组织,都是些毛主席的红卫兵,还打着红旗去过北京,搞过串联,见过毛主席,了不得哩!
雨丝儿静静地飘着,衣服淋透了,鞋泡湿了。那时候,县城里还没有柏油路,街道泥泞不堪。马长存踏着泥水走进了县城的那条仄仄曲曲的小街。他看见造反派们涌进县委大院揪斗“走资派”、“反革命”,还一个劲地喊着打倒“某某某”、让“某某某”滚出去的口号。人群里有很多是县一中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青年农民。他意识到一场灾难又要降临了。
批斗会就设在县一中的操场里。那操场对于马长存来说太熟悉了。当年,闹学潮、打学监就是从这儿开始的;穿上二尺半,吃粮当兵是从这儿上路的;解放那年,举行开国庆典,也是在这儿。同是一块土地,发生的事情却有天地之别。马长存这样想的时候,发现几个红卫兵小将手里提着皮带、木棒、链条,气势汹汹地吓唬着一群留着“一撮毛”头发的“走资派”。
“谁叫刘亮?”翻着花名册的红卫兵头头喊叫着,“叫刘亮的滚出来。”
马长存瞅了一眼,很快在留着“一撮毛”的队伍里发现了刘亮。刘亮油头垢面,衣服褴褛,看来这样的批斗和整治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是旷日持久、没完没了的。他向周围的人一打听,才知道已经折腾了一个多月。刘亮已被这帮人整怕了,听见叫他的名字,乖乖走出队列,软塌塌地说了声:“到!”
“你个驴球日的,你真反动,过去讲话劲儿咋那么大?往前站。”刘亮向前走了一步,规规矩矩立正站着。
“再往前站,把头勾下去。你他妈的真反动。给我把头勾下去,九十度。听见了没,再不九十度,老子弄断你的腰,让你一辈子变成弓腰儿。”
“报告红卫兵!我……我不反动。”刘亮极力把腰弯成九十度,哆嗦着说,“我是一贯拥护党和毛主席的,我……四八年就入党了!”
“好,好嘛,我让你煮熟的鸭子嘴硬,就是不知道你的骨头硬不硬?来,给我来点厉害的,看他的嘴还犟不犟!”
一根木棍往刘亮的小腿肚上落下来,把没有防备的刘亮打得腾一下跪在地上,刘亮的裤子上沾满了泥水。“革命的站起来!不革命的滚!滚!滚!滚他妈的蛋!”这酷似于小学生背诵课文的口号喊过之后,一个戴红袖章的提了一根短棍过去又要打刘亮。马长存看清了那个戴红袖章的是自己的外甥娃冯子,便挤过人群去打招呼。
“冯子,一年不见长这么大了?”
“阿舅,你也来啦?咋不告诉我一声哩。快晌午了,走,到食堂吃饭去。”
“你们去吧,我替你们守着这群坏人。大放宽心去吧,已经成了全县人民的公敌,他们长了膀子也不会飞到哪里去!”说话的当儿,马长存突然蹲下身来,将鞋带猛一下解开,又慢慢地佯装系鞋带。冯子和几位红袖章拉拉扯扯地走了。马长存不慌不忙地系着鞋带儿,鬼才知道他二斤半里装的是啥药。等冯子和那群人走远了,在一处拐弯的路口消失后,他鬼鬼地贼笑了一下,往四下里看了一眼,见没有他们的人,这才站起身来。他刚站起身来,目光正好与刘亮的目光相撞。他想跟刘亮说几句话,落难时来一点感情投资是很有必要的,但又怕被红卫兵们发现,扣一顶划不清界线的帽子,才这样做的。
马长存的脸蓦地涨红了,因为他刚才的举动分明让刘亮注意到了。他暗暗地谴责自己:“你呀!驴日的,真笨。一个小动作就给人留出破绽,还能干成啥大事呀?”然而,他又很快地平静下来。
马长存看了看四周,看热闹的越来越少了,只剩下几个半大娃娃在玩儿。他正要上前去跟刘亮搭话,发现七八个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向这边走过来,不远处拿枪的兵也朝这里张望着。他便干脆装着肚子疼,蹴着双臂抱着肚子,装着缓一会儿的样子。这时候,他又开始暗暗责备自己:“马长存,你个没事找事的东西!你要贴着说话的是啥人?是‘反革命’,是‘走资派’。在这节骨眼儿上,许多人把他们当成一泡狗屎躲都躲不及,你却撵前跟后惹骚哩!”他龇着牙,咧着嘴,一副肚子疼的样子。
马长存估计此时自己脸上的表情一定很可笑。他向刘亮瞅了一眼,正好刘亮也在看着自己。他发现刘亮对自己瞬间的表情变化流露出吃惊和不安的神色。吃惊就吃惊吧,老子的肚子才不疼哩!
那七八个戴红袖章的红卫兵转了一圈,远远地站在操场边清点了一下人数,走了。大概他们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哩。
雨丝儿还是静静地飘落着,根本没有停下来的征兆,那几个被批斗的对象被雨淋得一个个像落汤鸡似的。
马长存也真有耐心。与其说他在细雨中静静地缩在那里佯装肚子疼,还不如说他像一个猎人等待着机会,跟刘亮说几句话的机会。
那个拿枪的兵,经不住雨水的淋泡,终于动摇了革命的意志,看看左右没有认识的人,脱下衣服盖在头上跑了。
马长存看周围确确实实没有了人,就赶紧窜过去:
“老刘!”
显然,他把“刘书记”叫“老刘”,并不是因一时激动的口误,他叫“老刘”完全是在有意抹去跟刘书记的上下级关系。过去,刘亮来到大队,他跟在尻子后头口口声声“书记”长“书记”短的,连自己也觉得有点低三下四。而现在刘亮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是人民的公敌,他心一狠,改叫“老刘”了,这说明他和刘亮的上下级关系抹平了,是一个牲口上的褡裢了,至少在目前这种形势下是如此。一个农民能够挣脱这种心理障碍是极不容易的,可马长存就有这种能力。在他看来,刘亮现在的处境,还不如一个种田的农民哩,在这种处境中叫一声“老刘”就已经高抬刘亮了。
“你……你……”
刘亮环视了一眼,见没有红卫兵小将们,这才露出一副惊喜的神情来。为了避免让红卫兵看见,刘亮不敢抬头正视马长存,却露出了过分的激动和惊喜。他一点都没有想到,在这样的环境和处境下,还有人竟然这样亲热地称呼自己,想到这里,眼泪禁不住与雨水同时顺着鼻洼流下来,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平时开会讲话时的那种口若悬河的好口才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
“嗨,你呀!你真是个死奴才。”
马长存是个善于周全地考虑问题的人,有时还有一点农民特有的小聪明。比如这会儿,尽管刘亮把手伸了出来,他就没有主动握手,刘亮只好又把手缩回去。但用语言表达感情,他就显得比较迟钝了,一声“算啦!再甭球哭了,不就是受了几天罪!”就表明了他全部的心情。
马长存突然又觉得要安慰一下刘亮,人在困难时期是最需要这种安慰的。他向周围瞧了瞧,看没有人注意他们,这才把那一只粗大的手用力伸过去。刘亮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就在握手的那一瞬间,他感到这一次握手和以往不一样。往日,他主动热情地跑上去跟刘亮握手的时候,不知为啥,总觉着那是一双自负、骄傲的手,尽管刘亮不论是神情还是言语,从未表现过这种自负和骄傲,但他总有那么一种感觉。因为,他每次只握到手指头还来不及往紧里握一下,刘亮的手就已经抽回去了。而现在就不同,刘亮使劲地握住他的手,使他第一次感觉到了刘亮手上的力和热。但手是不能长时间握下去的,对刘亮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安慰,而对马长存来说却多了几分危险。
马长存主动抽回了手。长久的对视之后,他发现刘亮的鞋没有后帮,前面也露出了“阿舅”,“阿舅”上还沾满了红胶泥。他把手抽回来,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蹲下身去,把自己的解放球鞋脱下来,说:“老刘,穿上吧!过去坐办公室,阴凉房子里轻闲,现在雨里泡着可不好受哩!”
他知道刘亮有关节炎,经不住雨水的淋泡。
“这,这,这咋行哩!这大雨天,你不穿鞋咋回家?”
“你穿上吧,我夏天浇水经常精脚哩!”
刘亮有点迟疑,不敢接球鞋。马长存只好硬是脱了刘亮没有后帮和露出“阿舅”的鞋。刘亮往四周慌乱地扫了一眼,那样子像做贼似的。
过去,刘亮是极有风度的,特别是那抽烟的动作,就更加潇洒,可现在真有点可怜。马长存突然觉得刘亮那可怜劲让自己扫兴,同时他又觉得这一帮子娃娃也太狠心了。
“驴日的,革命个球哩!”
“说不得,让他们听见就坏了!”刘亮哆嗦着向四周扫了一眼。
“球个说不得!你杀人了?”
“没有。”
哼,都落到这个地步了,还连个响屁都不敢放,真是软骨头。他心里暗暗地责备刘亮。
“你反革命了?”
“没有。”
“你到底干了啥了,说嘛!”
“没有的,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我不承认我是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