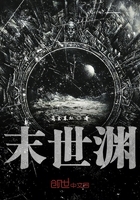在“八字方针”的指引下,农垦事业于调整中发展,发展中调整。
1964年春,农建师根据省上的指示精神决定:以东寺农场为主体,与原属邻县的西屯、柴冬、李寨三个小型国营农场“合四为一”,形成一个大约一千多名职工、1万亩耕地的县(团)级大型国营农场。四个农场原有的家底与经营状况各不相同,如以穷富划分:西屯、柴冬二场较富,东寺、李寨二场较穷。前者余粮剩米,流动资金都较充裕,后者则是“罗锅上山前(钱)紧”。
那时候实行的计划经济有个规矩:上年度的决算做出上报,经审查核准,上年度的亏损弥补拨下,新的年度计划得到批准,基建投资落实,农场的经济活动和职工生活像获得输血一样才能“活”起来。曾源调来东寺农场时,正值农场上年决算未报之际,正赶上“穷吃富,打平和”,从西屯和柴冬两处挪用了一批资金给全场职工发了一个月的工资(共欠发三个月工资),把春耕生产打发了。前两个月工资发不出,不少职工手头拮据,无钱买盐,买煤油,甚至连学生上学的课本费也无力支付,如此境遇,曾源也只能入乡随俗,他第一次感到置身亏损企业的尴尬。
曾源前来农场报到的当天上午1时左右,忽然听到高音喇儿顺风飘来一阵悲壮、激越的声音。曾源驻足静听,原来是场部播音室正在播送一篇新华社记者写的通讯稿《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这篇稿件他虽然在最近的报刊上粗粗读过,初步有点印象,今日听到在广播里播送感觉不大一样。焦裕禄同志的事迹太感人了,他呕心沥血,勤政为民,不顾病魔缠身,一往无前,带领全县人民战风沙,斗盐碱,治“三害”,在兰考大地上创造出惊世伟业,令人敬佩,令人感动。撰稿人激情满怀,播音者如泣如诉,感人肺腑!
听着听着曾源觉得这声音不亚于电台播音员的水平,惊叹东寺农场竟有如此水平的广播人才,他转而又觉得这声音怎么像一位熟人的声音,难道是他一一汪继丰?曾源与汪继丰夫妇已是多年未见过面了。1958年冬天曾源被借调到军区“征文办公室”工作,因报到时间紧张,匆匆离去,未来得及向好友辞别。次年初农场干部大调动,一大批干部被调往乐德地区“农口”安排工作,其中包括汪继丰和他的妻子艾冬梅。有人说农场某领导“吃不到口里”,就把人家“开销了”。这一别就是五年有余,由于曾源自身的工作飘移不定,又不知汪继丰夫妻俩的所在单位和确切地址,双方一直没有书信往来。想不到今日在此相逢,滚滚红尘,知音犹在,真是三生有幸。
播音告一段落,曾源到广播室找到了汪继丰。汪继丰领他到隔壁一间办公室叙谈,多年不见两人都有说不完的话。
这一对当年的英俊少年,同窗好友,各自在人生道路上历经挫折和坎坷之后步人了“而立之年”:汪继丰一直背着家境出身不好和其父在土改中被人民政府镇压的政治思想包袱;曾源在一度短暂辉煌后丢掉了党籍,使两人重逢之时颇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沧桑感,又为从今往后身边多了一位知心战友而庆幸不已。
汪继丰告诉曾源,他和小艾调来东寺农场这几年倒也清静,没有当年在红星农场时那么多的是是非非。他说我现在在农场党委办公室工作,办公室共两人,一位姓沈的河南人任党委秘书兼管组织工作,剩下的宣传教育、文教卫生、工会、共青团、户口管理全归我管,成天忙得不可开交。”
“小艾在农场小学当老师,学校里除了小艾,还有两位名副其实的老教师:一位女老师姓罗,上海移民,已有三十多年的教龄;再一位是咱们的老熟人哩”“谁?”曾源迫不及待地问。“你猜?”汪继丰故意吊他的胃口。“你快说,还卖什么关子?”“我们的老大哥章希贤你没想到吧?”
“我听说他在河西哪个县的一所中学里任教,怎么会在农场?”曾源依旧似信非信地摇着头。
“没有错,他原在乐德市中学任教,1957年‘反右’后下放到农场,高中教师教小学,他倒游刃有余。”汪继丰解释说。
“太好了,那你快领我去见他,我和他未见面差不多十二三年了。”
“你还是那个猴性子,现在快下班了,中午的时间这么短,我家和他家都在老场部那边,往返七八里路,找到人恐怕又到了下午上班时间,这样吧,”汪继丰看了看腕上的表,“中午咱俩就在这里吃。一会儿我到食堂打两份饭回来,吃完饭你留在这里看看报,我去找小艾交待一下,让她下午与老大哥联络好,晚上到我家一起聚一聚。”
事情就这样定了。
曾源说:“早上我来报到,二直没找到场领导,又没找到主管人员,现在还是个‘游民’哩,我得先报到,不然心里总是不踏实。”
汪继丰说:“这事你得等他们回来,主管人员就是与我同一个办公室的老沈,他陪新来的李书记到基层‘认门’去了,下午肯定回不来,就是个迟早问题,你就耐心等吧。呃,这李书记你也该认识呀!”
“咋回事?”
“解放初期,咱们县农业科的李科长,姓李、名士奎。”
“李科长?”曾源仍未回味过来。“他是咱们的同学叶曼玲的丈夫呀!我们参军离乡时,人家还和曲健、董敏老师一道参加了欢送我们的宴会哩,怎么?你都忘了?”汪继丰说。
“噢,是他呀!”曾源终于明白了。他转而又问:“1956年那次咱俩去兰州农校看我表弟时,李在农校当书记我们在大门口碰到他和叶曼玲,他啥时候调到农垦上了?”
“1958年他在凉城地区的石羊河农场当副场长,现在到咱们场当一把手,又升官了。至于报到的事,你还是先找沈秘书为好。”
“这样也好。”曾源点了点头。
“叶曼玲还没搬来,位子早已定了,来当东寺农场的小学校长,听说下个星期就要把家搬过来。”
“那咱们又多了一个老同学。”曾源说。
下午4时多,曾源见到了沈秘书,将一应调动手续交给了他,沈秘书说:“你的工作场领导碰过头了,安排在行政办公室任秘书。”沈秘书领曾源到一间办公室交待说:“这里就是你的办公室兼宿舍,你先住下来,工作上的事,场领导会在适当的时候找你谈谈”
曾源的工作和落脚点都有了着落,他在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起点启动了。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汪继丰来接曾源,同来的还有他的妻子艾冬梅。她手里抱了一个年约六七岁的小女孩,大大的眼睛,皮肤白白嫩嫩,活泼可爱。小艾身穿粗线呢外套,蓝布裤,浅口布鞋,梳两条小辫,比当年丰满了些,妩媚动人不减当年。
“你们就这么一个孩子?”曾源问。
“有两个呢,这个是老二,大的是个男孩,放在陕北他姥姥家了。”
三人带小孩离开办公室走在大路上,曾源问汪继丰老大哥那边说好了吗?”
小艾回答说:“他执意要做东,说是给你接风,故人团聚,长者为东,你知道他那个脾气还是说一不二,我们只好顺从他,咱们这就到他家去。”
老大哥章希贤敞门出迎。自从1951年兰州高三酱肉铺一别,屈指已是十三年有余。在曾源眼里他已早生华发,背也有点弯了,只有双目神采依旧,露着睿智与诙谐的目光,人生苦短,他巳过不惑之年了。
“曾源贤弟,别来无恙啊?”章希贤抓住曾源的双手使劲摇晃着。
“有恙无恙’友情难忘,想不到咱们今日又重逢,可真是他乡遇故知呀!”曾源露出一丝苦笑。
章希贤家住在老场部那边一处早年修建的职工宿舍。这些住房都是按“因陋就简”方针修建的土木结构房子,一面出水,又窄又小,通常一般职工每户只有一间;章希贤有三个孩子,额外照顾了半间,一间住人,半间作炊。汪继丰家只有一间,都是这种房子。
进了门,小艾吩咐女儿:“去,去找姐姐和弟弟玩去。”
章希贤有二女一男,两个女儿都比小艾的女儿大,男孩子比小艾的女儿小一岁。四个孩子都是同学,又因章希贤和小艾同在一个学校当老师,两家交往较多,彼此间显得更亲近。
章希贤的妻于年约三十二三岁,中等身材,虽然算不上俊美,却也五官周正,温柔贤惠。小艾向曾源介绍说咱们的章嫂可是个能干人,左邻右舍都夸她心灵手巧,会理家,你看到了,三个孩子都收拾得整整齐齐,家中大小事都理得顺顺当当,你看一—”她指着一架成色很旧的缝纫机说:“除了大田里干活,她还抽空儿给别人做这做那,收个小钱帮衬、补贴家里的生活,章老师抽烟的钱,大多是嫂子挣来的。”
“羞死人了,你再别说了,咱是个粗人做粗活,哪像你们当老师的有体面,让人尊敬。”章妻自谦地说。
“大嫂真是一位贤妻良母,大哥算是福分不浅哩。”曾源颇为敬重地说得章希贤夫妇有点不好意思。
汪继丰说:“老大哥,我让小艾来请你过我们那边陪曾源吃顿饭,你说今晚你要做东,要我们无论如何要成全你,不知是何缘故?”
章希贤说我之所以喧兵夺主,理由有三:第一,我是老大哥,长者为东,理所当然;第二,你大嫂的单位给各家分一点苜蓿尝鲜’我们用它捂了一坛子浆水,味道奇佳,愿与家乡的朋友共享。要吃家乡饭,首推浆水面,我这里有现成的;其三,我有个重要消息告诉你们,我原来所在的市一中要把我收回去,说法是‘下放期满,收回成命’。听说那边高三语文教师病故了,让我回去顶他的班,下个星期就要去报到。农场呆了三年多’一切都习惯了,猛地一下子要进城去,真有点舍不得哩,没办法,吃人家的饭,受人家管,只好听命。不巧的是,咱们的曾源贤弟刚来,我就要走,不能在一起共事,太遗憾了!”
曾源、汪继丰相继与章希贤握手,以示惜别之情。
那年头,迎客会友,想要饮酒动荤,有钱也难买到,要不怎么能叫“短缺经济”呢。居家过日子,浆水面是家常便饭,只不过把面擀得薄一点,切得细一点,泼辣子的油放得多一点而已。今日厚待曾源,特意从自家鸡窝里掏了两个蛋,来个韭菜炒鸡蛋,算得上是美味佳肴了。大人孩子吃得很香。
招呼孩子们吃完饭去玩耍,大人们围坐在一起,无酒尽欢,以茶代酒,叙说别情,忆念故乡,问讯故友,其乐融融。庆幸终于熬过三年困难时期,政治运动少了,一心一意搞生活、干工作,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
大家兴致很高,曾源提议:“难得今日相聚,岂能无诗,请老大哥即席赋诗一首,以助我兴!”
“请、请、请!”汪继丰和小艾鼓掌欢迎。
章希贤凝眉苦思良久,终于诗潮喷涌,一气呵成饥寒交迫夜“三年”,“中右”帽下苦熬煎。
斗换星移光明在,寒夜过后艳阳夭。
第二天上午,场党委书记李士奎单独召见曾源。故人新境,心照不宣。
李士奎:“曾源同志,观迎您到本场工作。”
曾源:“愿在场领导同志指挥下做好本职工作。”
李士奎:“我们碰过头了,决定安排你在行政办公室做秘书工作,怎么样?”
曾源:“自己能力有限,恐怕干不好。”
李士奎:“据我们了解,你在红星农场干过秘书工作,见识广,笔杆子硬,这份工作让你干,不在话下。”不难看出,分局给场里打过招呼之后,他已向有关方面做过了解并翻阅过曾源的档案材料。
曾源:“那是在红星农场初划时期,我当秘书只能算做忙乱中打杂,现在到了正规科室里干,只怕跟不上趟。”
‘李士奎笑道:“不必过分谦虚’先干起来,不过行政办的工作是比较杂乱,你得多操些心。眼下的困难是人手少,上无主任,下无帮手,你得一个人挑大梁。除了机关的日常行政事务,还要管好一个大食堂,三间招待所,做到彼此兼顾,内外满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相信你一定能够干好。”
曾源还之一笑:“那就试试看,我尽力干好,如果不行’敬请领导上另做安排。”
李士奎年过四旬,已经谢顶,额上有明鲜的抬头纹,只是由于他长得清瘦,不显老态,露出几分精干之气,这或许是他处事顺心,兴致好。与故人交谈勾起几多怀旧之情,他说:“十多年里,咱们不期而遇已经有三次了:头一次是在南安县送你们参军的宴会上;第二次是在兰州农校邂逅;如今这是第三次了,而且是走在一起来共事,咱们算得上有缘分了。”
“李书记过事不忘,好记性!”
“精力远不如前些年了,一些事情本想干好,常常力不从心,不像你们精力旺盛,正是干事情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李士奎脸上现出几分惆怅之情。
“李书记革命工作经验丰富,请多指教。”
“不能那么说,水平、经验这东西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干出来的。你的学识、才干都是不错的,放心大胆地去干吧。”李士奎关切地问,“你还有什么想法,请提出来?”
“有个个人问题一一其实也没啥。”曾源欲言又止,觉得初次见面’时机不当,不便开口。
“不要有什么顾虑,在我这里有啥想法都可以说,你究竟有什么问题?”
“党籍问题。”曾源把想说的话说出口,他又有点后悔。心想,在老单位发生的事说给新单位的领导,给人家添麻烦,原本不应该,可又说出了口,泼水难收,一时有点无所适从,心中的阴影挥之不去。
“你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详细说说,咽回去总不是个办法。”
“好吧,我说,”曾源坦述了自己被取消预备期的始末,他回避了个中的个人恩怨成分,讲了三条理由:“第一,结论与事实不符,其中有的无中生有,有的被歪曲,经不起事实的核对;第二,我当时因公出差在外,未能参加讨论本人转正问题的支部大会,失去当面澄清事实与据理申辩的机会与权利;第三是在农场干部大调动的混乱局面下‘处理遗留问题’草率了断的,有失严肃与公允。”
李士奎听完,良久无语,看得出来他是对曾源提供的信息在脑子里加工、判断,选择适当的语言,他说依我个人的看法,原单位党组织对你的党籍问题的处理不能说是毫无根据,也不能说完全错了,但显然是过严了,有失公正,负面影响也不小。这样吧,”他坦诚地提示曾源:“你这个问题可以个人申诉复议一下,不过还得与原单位党组织取得联系,时过境迁,怕不太容易,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4取消预备期’不是党纪处分,可以争取重新人党。据我们了解,你出身于劳苦大众家庭,本质好,工作一贯积极,有才干,只要你继续努力,党组织不会长期把你这样的同志关在门外。”
曾源离开李书记办公室之际,似乎觉得今天被召见无所得,甚至不如不谈,但透过迷雾又仿佛看到一线曙光……对于安家问题,鉴于曾源家已是祖孙三代五口人,住房给了一间半,指定就住章希贤原来住的房子。在李书记的亲自过问与督促下,场里派了一辆卡车,将章希贤家搬到城里,将曾源家搬来农场,一车两顾,往返不放空车。
1964年初夏季节,“四清运动”在去冬今春完成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各地分期分批由上级领导机关派出工作队(组)进驻选定的单位开展“四清运动”(此时由上而下已将“四清运动”改称“社教运动”),由于这次运动都是县以上党委直接抓点进行的,故称“点上社教”。
东寺农场所在的乐德市是全省首批开展“社教运动”的地区,省委第一书记亲自率领工作队到市郊某公社的一个大队蹲点,来势不比寻常。在这一背景下,全市城乡各大系统都选定了相应的“点”与省上的“点”同步进行并被当做“头等大事”来抓。东寺农场作为农建师的首批“点上社教”,与之相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