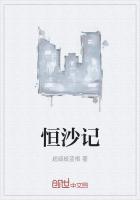曹操本来就生性喜好猜疑,一听华佗想要砍开自己的脑袋治病便勃然大怒,喝道:“当要杀孤耶!”华佗不慌不忙地回答:“大王曾闻关公中毒箭,伤其右臂,某刮骨疗毒,关公略无惧色;今大王小可之疾,何多疑焉?”曹操说道:“臂痛可刮,脑袋安可砍开?汝必与关公情熟,乘此机会,欲报仇耳!”便马上命人将华佗关进狱中,严加拷问。
贾诩上前建议:“似此良医,世罕其匹,未可废也。”
曹操斥责道:“此人欲乘机害我,正与吉平无异!”又命人抓紧拷问。华佗情知获救无望,恰巧狱中有一位姓吴的狱卒对华佗优待有加,华佗由是感激,便把他所著的《青囊书》赠予他。
生性猜忌的曹操下令处死了华佗。华佗被处死之后,曹操的儿子曹冲忽患怪病,遍请名医医治无效,曹冲因此病而丧命,曹操为此悲伤不已,加上头疾复发不治而终,曹操的猜疑终于让他自食其果。
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这样的人除了自己谁都不会相信,曹操做事虽雄才大略,做人无疑是失败的。这种猜疑的心态使曹操错杀朋友、误中周瑜的反间计、怒杀华佗而断送了儿子和自己的性命。
疑神疑鬼,杀臣如麻——朱元璋
平明百姓的猜忌尚且会产生很多的悲剧,一个帝王如果有这种心理,其影响必然扩大到他统治的每一个角落。
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也是一位猜疑心态极其强烈的人,他在建国后不久便大肆杀戮功臣,其统治时代也由此成为我国历史上较为血腥的一段时期。
国基初定之后,朱元璋生性忌猜的心理日益显露出来,他为了自己的王朝能够长治久安,借胡惟庸、蓝玉之案,大做文章,火烧庆功楼,诛杀功臣,排除异己。为了皇权的巩固,他制订了《明律》,设立了东厂、西厂的锦衣卫特务机构,明朝成为历史上专制最严重的王朝之一。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猜疑最初源于其参加农民起义军时的自卑心理。朱元璋出身贫农,生活上无恒产,17岁便出家当和尚,靠乞讨为生。在天下动乱之时,投到郭子兴部下,也只能当个亲兵。而从封建伦理标准看来,他不是豪门显贵的余绪旁支,如果没有聪明睿智的表现,就没有资格君临那些高门后裔和文人雅士。于是他在政治军事上扩展自己的势力的同时,还努力学习文化,屈尊结交大文人如宋濂、刘基等,似乎他虚心好学、礼贤下士。
但实际上,他只想借助这些文人的帮助,为他打点江山,而大明江山统一之后,这些人反而成了他的心腹之患,他虽不识多少字,但深知这些人的活动能量,倘若反对他,肯定是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从那时起,他对这些人就抱一种怀疑猜忌的心态,就怕有一天,这些人变成乱臣贼子,反对他的统治。
朱元璋的猜疑心理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他当皇帝之后爱舞文弄墨,并把文章颁行天下,其实他写文章的起初动机是炫耀帝王的文可安邦,武能定国的气度。他的猜疑表现在他大兴文字狱上面,当时因文字被杀的人不计其数。有一名叫来复的僧人为了讨好朱元璋,在谢恩寺用了“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的句子,朱元璋认为“殊”乃“朱”是骂他之意,“无德”更是讥他没有德政,那位一心取媚的和尚不明不白地送了身家性命。
最能体现朱元璋猜疑心理的是他开始怀疑一切,甚至连备受他重用的宋濂也难免遭殃。大学土宋濂告老还乡,每年都要来觐见朱元璋。有一年没有来,朱元璋就将他的儿子宋琏、宋慎杀掉,并将宋濂谪居茂州。文学家高启被荐修《明史》。成书以后,朱元璋授以户部侍郎的高位,高启坚决推辞。朱元璋认为他不肯合作,就将他腰斩于南京。当天下文人都只能以他的文章“为表式”的时候,他的心理才得到一丝平衡。
朱元璋令天下大办学校,初衷不是振兴文化,而是为了统一思想,从这个举措上,也可看出他那多疑狭隘的心态来。洪武二年,朱元璋诏令天下建立学校。他做了校训刻石于校门前,不许生员“炫奇立异”,不许生员直言。
他多疑的心态使他残酷迫害一切,他迫害比自己高明的人,特别是迫害文人,因而对于文化的影响特别大,这个举动首先是形成了轻视和践踏文化教育的恶劣风气。毁书院就是这种恶劣风气的一种表现。明代曾发生过三次毁书院的事件。朱元璋就是不想让知识参与政治,只能在小范围的情况下为他所用。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无疑会使教育滞后,导致了科学技术的落后,我国的科技水平在明朝中叶明显落后于世界的发展水平,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客观事实。
文化的衰微必引起道德的沦丧,而道德沦丧的突出表现就是官吏大肆贪污。明代权奸贪污行为之猖狂,贪污的赃物数量之巨,令世人瞠目。同时,文化衰微又导致人才十分缺乏,奸臣当道,以致连目不识丁的魏忠贤也能执掌国家大权。素质低下的人既不可能在经济文化上做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贡献,也不可能成为巩固王朝政权的“栋梁之才”,甚至不足以抵御外侮的军人或者凭借农民起义以建立稳定的新政权领袖。明军在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战争中表现得非常怯懦。
朱元璋的多疑还体现他谋杀开国元勋上,他称帝不久便迫不及待地大杀臣子甚至皇族。当时的京官去见皇上之前,都要和妻子儿女诀别,到下午平安地回到家,全家人才高兴起来,可见当时朝臣的恐怖达到了何等程度。他以种种名义杀戮群臣,其中包括曾经跟他征战南北、战功卓著的功臣。明朝建立后,这些功臣宿将不仅居功自傲、骄恣如故,而且随着权力和欲望的不断增长,他们在政治、军事上的势力也在迅速膨胀,遂与朱元璋提高皇权,专制独裁的政策发生激烈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平素多疑的朱元璋当然会怀疑这些人对自己地位的威胁。
同时,君权和相权发生了严重的冲突,随着中央集权专制的日益发展,君相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朱元璋称帝后,先后任命过四员丞相,其中以胡惟庸最为跋扈。他是一个“专恣不法,擅作威福”的人,在任丞相的时候,也“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奏,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胡惟庸曾先后铲除了异己徐达、刘基等人,满朝文武中能与其分庭抗礼者坐无几人。于是胡的权势已发展到炙手可热、不可一世的地步,这种对皇权造成的严重威胁,多疑而又狭隘的朱元璋自然不能坐视不理。而胡惟庸的“专恣不法”,正好给他抓到了把柄,朱元璋遂以“胡党谋逆”为由,于洪武十三年兴胡惟庸党案。“词连所及,坐诛者三万余人”,前后因胡党案牵连被诛的公侯大将达二十余人,成为明初的第一大狱。从此,朱元璋吸取教训,废丞相,设六部,大权独揽。
另一方面,君权与将权也发生了冲突。朱元璋自己就是一个“马上皇帝”,一生南征北战。深知依靠武将夺取天下对于他自己的将来意味着什么,十分担心武将的叛乱。早在明朝建立前,谢再兴,邵荣的叛变就给朱元璋思想上带来深刻的震动,因此他对诸将很不放心。诸将出征,以其家属留京做人质,并依靠检校侦缉将士私事。而朱元璋对公侯大将防范越是严密,矛盾越深。功臣宿将不仅手握重兵,且又和各地卫所军官有过统率关系,很容易形成和朝庭对抗的军事力量,成为颠覆明朝统治的潜在威胁。以大将军蓝玉为例,他是开平王常遇春妻弟,虽骁勇善战,但为人“性复狠愎,专恣暴横”,在朱元璋面前也举止傲慢,无人臣之礼。诸多迹象均表明,将权将要威胁到朱元璋的皇权,多疑的朱元璋当然不可能连这一点也不知道。于是,捏造蓝玉谋反的罪状。
猜疑型性格的人警惕性特别高,对周围的人都采取不信任、怀疑的态度,而且总是朝“恶处”考虑。对于地位显赫的人物来说,生性多疑的危害性也就越大。一方面处于权力地位的巅峰,他们的这种多疑心态可以理解,但从道德伦理角度看,他们的行为又是一种不可饶恕的错误。
同时,他们也为自己多疑的心态付出了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