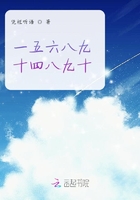绝望就是在永无止境的噩梦中无法醒来。
1993年9月11日
郑磐伸出手掌,让从窗外射进的阳光穿过指间缝隙落在脸上。渐黄的秋叶在枝头依依不舍,诉着离别的悲歌。曾是同一枝头的树叶,从嫩芽到茂盛,它们见证了春天的柔和月光和盛夏的生机勃勃。它们曾充满活力高高在上俯瞰林间众生,可分别在即,将各奔他乡也许从此再无缘聚首,在思念中葬身于寒冬的僵硬泥土里。想到这里郑磐感到了寒冷,仿佛照在脸上的不是周六的晨阳而是雪山崩塌后倾泻出的冰柱,让人感到刺骨寒凉。
“郑磐呐——让淑女等待可是犯罪!”张滢的大喊大叫不知为什么会令人感到安心。
“你哪里像淑女了?”郑磐叫着起床穿衣,微笑着想:“我不再孤独了,因为有你们在。”
出门后郑磐看见穿着短裤的张滢正抱着肩膀斜坐在自行车上,嘴里叼着不知哪里抓的狗尾草杆。“赶紧的,大米饭粒带着小梦涵先过去了。恩……让他俩在一起总觉得心里不安呐,果然这是犯罪吗?”张滢唠叨着,嘴里的半截草杆上下摇摆看得郑磐眼晕。路上张滢又发起了骑车比赛,几乎把车链子蹬红的郑磐险胜一辆自行车的距离,齐冬莲远远被甩在后面,头上点缀着碎花图案的米色布帽几次差点被风吹走,最后只得放慢速度。
五人聚齐在废弃采石场入口,曾经被夷平的工地现已重新被野草占据,门口警卫室的门窗残破不堪。山间的劲风穿过废弃的厂房,吹起阵阵尘埃,尚未加工的粗糙石料静静躺在运输槽里毫无生机。
“恩……没想象中那么恐怖嘛。”张滢显得有些不屑。
“这样能稍微让人安心些,是吧?”齐冬莲倒是松了口气。
“啊哈哈哈,小的们前进吧!”林中兴边说边趁机摸王梦涵的头,却被张滢拦住:“喂喂,大米饭粒,你这绝对是犯罪了。”
“就是这了,让我看个究竟,为什么会梦到这里,为什么有来过这的感觉。”郑磐暗想着踏入采石场坚硬的地面。
穿过空无一人的工地厂房,在空洞的走廊里听着凌乱的脚步声,即使在白昼也让人感到压抑。众人把废旧的厂区几乎走遍,除了挖掘机械和工人遗留下的铁架床并没有什么值得留意的东西。直到郑磐在一块石壁旁发现了一闪白光,虽然只有一瞬间,但郑磐清晰看到了它——银制百合花耳坠。他把耳坠捏在手里,感觉重若千斤——在梦中曾见过这耳坠。“真漂亮,被丢在这里可惜了,是吧。”齐冬莲发现了郑磐手中的耳坠。“恩,浪费就是犯罪。”张滢表示赞同。郑磐苦笑着回头:“给你就不是犯罪了吧?蝇蝇。”说着把耳坠递给张滢。张滢一时愣住,盯着递过来的耳坠结结巴巴:“那个……我,我……不太适合……吧?”脸上泛起了一阵晕红。“好像真是。”郑磐说着转头把耳坠放在齐冬莲手里,“仔细一想还是给小莲比较合适。”
“啊,谢谢……我会好好保管的,是吧。”齐冬莲傻笑着接过耳坠攥在手里。没人留意到张滢眼中轻轻掠过的失落,她把半截狗尾草杆吐到地上:“都逛遍了吧,感觉这里很无聊,是吧小不点。”大家把视线转向王梦涵时才发现她神情恍惚。“不好!”郑磐冲向王梦涵,张滢却抢先把梦涵抱起大喊:“小不点又犯病了,快去卫生所!”张滢的自行车像脱弦的箭冲在最前面,不断把灰色的峦峰抛在脑后。郑磐也拼命蹬着自行车,只是再也无法赶上张滢,她的背影越来越远,无法触及。不知为何这让郑磐心中泛起一丝落寞。
到达卫生所时,王梦涵几近昏迷呼吸微弱。拥有像石虎村这样大卫生所的村庄不多,白色的三层楼内科室齐全设备完善。石虎卫生所是联邦特别为石虎村修建的,作为惠民政策缓和了反对修采石场的村民的矛盾。王梦涵的主治医师是杨珊——一个迷人温柔的女医生。杨珊毕业于中央医科大学,才27岁的她已是负有盛名的精英医生了。
透过监护室的玻璃窗郑磐可以看到昏迷不醒的王梦涵,门外是焦急的同伴们。“杨大夫,梦涵她怎么了?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上周就昏了一次。”张滢紧张地问道。杨珊扶了扶白色窄边的眼镜框回答:“贫血,伴随着心率不齐,导致的突然昏迷。并没有生命危险,现在需要的是静养。”“可是……”张滢还想说些什么却被打断。“真要是为这孩子好你们应该回去了,她需要休息。”杨珊说着把手放在郑磐肩膀上,“相信我,她会没事的。”
当夜郑磐辗转反侧,他想不清百合花耳坠的意义,也对小不点近期的两次晕倒很在意。更让他不安的是张滢,突然感觉和她之间有道看不见的墙。今夜无光,漫天的乌云将夜空涂抹成一片漆黑。窗外稀疏的蝉鸣凄冷寂寥,不知名的飞鸟漫无目的的扑腾着双翼盘旋在阴湿的林间。未来的几天内会持续多云,天气预报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