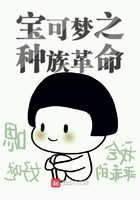谨以此纪念那些已经或正在被遗忘的关于我的民族的一切。
第一章
1980年,黔西北。
云雾山中,一块泛黄的木牌匾两旁是独特的彝族老鹰图像,中间彝语和汉语同书:归则村。
往里走,是一颗高大的皂角树,树下,一群彝家儿女正在古老的跳锅庄舞,欢声笑语。
这是阿洛父辈传说中的以前居住的彝家寨子。后来,因为灾荒,阿洛的父辈逃至这个没有丝毫彝族气息的村落,在这里阿洛和他的父辈正在遗忘着关于自己民族的一切……
1
四周环山的石丫口村。漆黑的夜里散落了几颗微弱的灯光。
一处破落的茅草房,一道昏黄的灯光从门缝里漏了出来。
砖头围砌而成的火炉上,一壶水在哧哧地冒烟。
围坐在火炉边的30岁彝族妇女阿舒严肃而无奈地说:“你不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吗,你倒是说说该怎么办啊?”
37岁彝家男子阿文只顾抽自己裹卷的旱烟,闷不作声。
简陋破乱的床上,他们刚满两岁的孩子小阿洛看上去似乎已经奄奄一息,偶尔作一两声呻吟。
一个5岁小女孩气喘嘘嘘,破门而入,她是阿洛的姐姐阿香。
阿香说:“阿妈,收废品的又来了。”
阿舒看着阿文,有些生气地说:“你还是不是男人?”
阿文还是闷不作声。
一对家传的银镯子放在床边的黑色木柜子上。
阿舒摔门而出,一会儿领着回收废品的男子来到门口。
阿舒拿着银镯子问:“大哥你给个价吧。孩子等着钱看病呢。”
男子装模作样打量了一下,说:“五块钱。”
阿舒咬着呀,犹豫着。
阿文说:“这可是银子的,父辈传下来的,五块钱,开什么玩笑?”
男子补充说:“最多十块。”
阿舒白了阿文一眼,说:“十块也不够,反正也不够,如果你诚心要,三十块钱,不然的话,就不卖了。”
男子考虑了一下,转身走了,消失在黑夜之中。
阿舒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淡出。
2
阿文家院坝里。百年樱桃树下。
阿香穿着不得体的绿色军衣(80年代民兵衣服)与同村的汉族小伙伴趴在地上玩。
凶恶的爷爷边故意吃面条吃得很响边骂道:“几个死母狗,衣服在地上都滚脏了~~~~~”
他是阿文的母亲带着阿文来到这里后才改嫁的,姓刘,名大先。
阿香白了刘大先一眼,继续玩自己的。
3
石丫口村民组组长李会学家。夜。
灯光昏暗。男人们的旱烟烟气四处弥漫。
李会学抽着烟说:“今天喊大家来,有两个事。一个,一组的黄马二家父亲去世了,农活不忙的都去坐坐,搭把手,帮帮忙什么的。还有一个是,李文学家大儿子打工回来说,现在国家在搞改革开放,鼓励大家做生意,共同变富裕。你们有什么好的路子的都说出来,大家斟酌斟酌?”
村民陈学达带着长角彝族帽子数落着手上的旱烟叶子说:“开啥饭哦?好好种地,就有饭吃,不种地****都没有。”
龅牙村民李从军说:“我准备学杀猪,就是本钱要得有点多。不晓得国家这个什么开放,有点补贴没有?”
李会学说:“改革开放是一种政策,不是什么开饭,也没有什么补贴。”
杂七杂八的声音:“那有鬼的搞头啊!”“远天远地的,就像什么坏事也到不了我们这儿一样,什么好事也到不了我们这儿。”
整个村庄在一阵狗吠声中,淡出。
4
穿村而过的马路上。两旁长满了一人多高的玉米。一辆马车拉着一车煤炭悠悠而来。
阿舒背着阿洛去找大夫,阿香也跟着去了。
他们前脚才走,后脚阿文就带着陈学达进了茅草房。
两人在火炉边坐下。阿文从床下拿出一瓶苞谷酒,又从碗柜里拿出两个白瓷碗,斟上酒。
陈学达用彝语说:“喝酒喝酒!”
阿文跟着符合:“喝喝喝!”
边喝,二人边谈论“哦索尼邹邸素博,勾邹邸邑撮”“黑羊大箐”“吴三桂剿水西”……
陈学达侃侃而谈:“酬尼勾邹酬尼那洛,十二家(支)头人(勾邹)和十二家(支)黑彝(那洛),不知道如今都沦落到何方?”
说到激动处,两人竟泪流满面。
阿文醉醺醺地问:“勾邹?那洛?”
陈学达:“以血统关系来论,‘勾邹’(上层白彝)与一、二、三等之间没有关系,但因其在彝族群体里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有‘勾邹’功名),故排名在那(黑彝)之后,属于四等群体。而以其社会地位来说与‘酬尼那洛’(十二支头黑彝)相当,只是‘那’(黑彝)在血统上是与‘祖摩’(君王)相连的。‘勾邹’有十二家(支),‘那洛’(其他的‘那’除外)也有十二家(支)。”
陈学达:“‘祖摩’(君王)及其家小一等,‘哄’(土目)为二等,‘那’(黑彝)三等,‘勾邹’(白彝头人)为四等。”
一会儿,阿舒背着孩子回来了。
看到阿文喝酒,阿舒努力压住自己的怒气,转而笑着对陈学达说:“陈大哥来了啊。”
陈学达举起碗一饮而尽说:“嗯。我们在说我们彝家的历史,你要不要也听?”
阿舒说:“不了。阿洛病了,刚去没找到大夫,我准备再带他去找王老师家媳妇看看。”
站一旁的阿香白了阿文一眼,说:“爸,你就只顾自己喝酒。弟弟病了,你也不管。”
阿文看了阿香一眼,本来想说什么,却最终还是闷不作声。
陈学达试图打破尴尬,伸手拉住阿香说:“阿香,我教你学彝话,好不好?”
阿香挣脱开说:“不学。”
阿舒拉着阿香说:“阿香,走了,一会儿王老师家没人在家了。”
随后,阿舒背着孩子拉着孩子的背影在马路上越走越远,最终消失。
5
石丫口不远处的镇上中学。
几栋红砖房围起来的空地上,百十个学生迎着烈阳正在听一位老师演讲,大概内容是,为祖国之崛起而努力读书。
这是当地镇上唯一的一所中学,历史悠久。
学校的西北面有几间瓦房,门口有一排栀子花。王老师家就住在那里。
王老师与阿文以前是同学,两人关系不错,只是后来命运悬殊太大,阿文在这一点上很自卑。
阿文总是说:“以前他学习还没我的好,我又是班长,哪次他不会不是我教他。”
阿舒拍了半天门,开门的是一个小胖子。
王老师正在洗衣服,回头说:“大嫂来了,阿洛还没好吗?”
阿舒说:“好像越来越严重了,脖子都撑不起头了,王老师。”
王老师对小胖子说:“大庆,快去郭伯伯家喊你妈妈回来。大嫂,你们来坐。”
王边说边收拾沙发上的几件衣裤和书,腾出位置来。
阿香又好奇又有点害怕地紧跟母亲后面。
小胖子到外面喊了几声:“老妈,老妈,回家给人看病!”
王老师客气地说:“大嫂,你们喝不喝茶?”
阿舒满是拘谨:“不用不用。”
傻痴痴地等了几分钟,王老师的妻子提着一袋糖果回来了。
王老师的妻子:“大嫂,来了。”
阿舒急切地说:“我家阿洛越来越严重了!”
阿香呆呆地盯着那一袋糖果,咬着手指。
王老师的妻子帮阿舒把孩子从背上放下来,放在沙发上,然后蹲着看了看他的脸色,摸了摸脉搏,说:“没多大事的,大嫂,不要太担心了。阿洛主要是脱水有点严重。回去注意营养给补充补充。”
这时,王老师从里屋里拿出了一袋米递给阿舒,说:“给孩子煮点南瓜粥喝。”
又拿了些药,阿舒掏了半天钱,王老师的妻子按住阿舒的手:“大嫂,不要翻了,都是自家人,自家人看个病,哪还要钱呢?有那个钱啊,你给孩子买点吃的。”
阿舒:“但是,每次都这样.。。”
王老师的妻子:“那就争取让阿洛赶快好起来,下次不要来了,哈哈。”
阿舒心里想:以后阿洛他们长大了,一定要告诉他们记得王老师一家人的恩情,一定要报答人家,人家不收钱,下次家里母鸡下的蛋就不要哪去集市上卖了,凑多点,给人家王老师家送去。
在回去的路上看着脖子都撑不起脑袋的孩子,阿舒满脸忧郁。
阿香嘟着个嘴只顾跟着。
6
五年之后。
镇上小学。
阿香带着七岁的阿洛去报名读书。
阿洛只顾低着头看路,遇见同村的人打招呼也不理,只顾玩自己手中的打针用过的塑料管子。
填报名表的时候,已经上三年级的阿香握着他的手在民族一栏写下歪歪扭扭的“彝”。
阿香说:“以后你要记住,你是彝族。”
阿洛呆呆地看着阿香,似懂非懂。
接待报名的女老师说:“小姑娘,你是彝族啊,你会说彝语不会呢?”
阿香撅着嘴说:“我爸会,我外公外婆也会。但是我不会。”
老师呵呵的笑了笑,喊:“没事的。回去喊你爸爸教你。下一个。”
报了名,挤出人群,准备去收费处缴报名费的时候,阿香脸色一下子变了,四下里翻自己的衣兜,还翻阿洛的。
阿洛问:“姐,怎么了?”
阿香说:“我找不到报名费了……”
阿洛哈哈地笑了起来:“那我就不用读书了,哈哈哈哈。”
阿香却哭了,不知所措。
听同村人说了之后赶到学校的阿舒,狠狠地在大庭广众之下揍了阿香阿洛,哭喊声此起彼伏。
阿舒边打边责备:“叫你不小心,叫你不小心!”
第二天,阿舒向村邻借了钱补交了学费。
阿香牵着阿洛走在翻山越岭去上学的路上,背影渐淡。
7
经历考验的彝家儿女,在灾荒之后,依然生活在美丽富饶的归则村。这是黔西北大地上众多纯彝族村寨中的一个。
那一年的灾荒,年轻人都外逃了,留守的老人们靠吃杜鹃花和树根树皮活了下来。
外婆穿着漂亮的彝族服装拄着拐杖,在村口翘首张望着。
归则村依山而建。一条清澈湛蓝的河水从村前流过。
动听的彝家妹子歌声由远及近。
“我的情哥哟,
小河大河水容易在一起,两座山难碰到一块;
我俩用歌声搭座桥,
就看搭桥的材料够不够?
就看搭桥的材料好不好?”
又一男子应和唱着:
“我的情妹哟,
两条河相遇容易,两座山相碰难,
我俩最难碰到一块。
青松树做好了楼梯,
已经搭在你的楼口,
是你从楼上下来?
是我从梯子上去?”
两人合唱:
“阿哥的材料做桥梁,
阿妹的材料做桥板,
一座美丽的彩虹出现了,
两座山相连起来,
我们两个相会了。”
盘山的毛路多荆棘。
每年四五月间,满山全是艳丽的杜鹃花。(百里杜鹃绽放镜头切入。)
沿山而下。
是阿洛的外婆家。
一看到三个身影,外婆笑了。
阿香、阿洛齐声喊:“外婆!”
外婆搂着两个外甥:“好好好!外婆给你们做了好吃的。”
阿舒:“阿妈,你和阿爸,最近身体都还好吧?”
外婆:“能吃能睡能喝酒,好着呢,不要为我们操心。”
8
归则村。略显破败沧桑的彝族民居。日。
大人们在屋内喝着自家酿造的咂酒,吃着大块的肥肉,想当年,又想未来。
外婆突然说:“前几天听乡里的干部说,好像,我们这边也准备开始修路了,到时候就方便了。”
披着彝族披风的外公说:“修了才算。”
刚刚成年的四舅吃完饭一个人跑到房背后的山坡上吹口琴,好听,但不知道是什么曲子。
外婆说:“这个小四不像话,这么大了,媳妇都不去找一个。好的人家看不上他,差一点的他又看不上,让人操心得很。”
阿舒说:“现在外面像小四这么大的人好多都还在读书,人家都二十七八才结婚的多得很。”
外婆说:“那是人家。我们彝家不那样。想当初,我十四岁就跟了你爹。这才有了你们几兄妹。”
吃完饭,外公和阿文到仓库一边聊天一边摘刚采收回来的豆子,摘下来要拿到院坝里晒两三个大太阳,才能入仓。
外公说:“有时间你还是教教阿洛他们彝语,虽然不一定用得着,但是这是祖先留下来的。丢了可惜。哦索尼邹邸素博,勾邹邸邑撮。”
阿文说:“他们不肯学,而且,连我自己也会得不多。”
外公摇了摇头说:“现在我们寨子里基本上没什么年轻人了,怕是以后会讲彝话的人越来越少咯!”
阿文随便地笑了笑,其实他根本不知道学不学彝语有什么意义,尤其是对于改变他自己的生活,在他的印象里,也许只有苗子才叮零当郎讲些别人听不懂的苗语。
第二天,是一年一度的彝族火把节。
阿舒也穿上了五彩的彝族服装,跟着大家围着篝火跳舞。
大家互相祝福着,觉撒格撒(生活吉祥)、孜莫格尼(吉祥如意)。
虽然寨子里人越来越少,当大家还是都一如既往地坚持着这些记忆中的传统。
在这些老人当中,也有一些年轻人如阿舒他们一样回来看望老人与老人们一起过节的。
虽然他们的舞步不那么熟稔,但是态度是绝对认真的。
大人们歌舞。
小孩子们则在另一边兴致勃勃地玩着“磨磨秋”(彝族传统体育运动)。
阿洛不敢玩,即便是阿香把他抱上去,他也知识趴在长木棍上哭。
转来转去,一高一低,各种笑声歌声,在这个小寨子里漫延开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