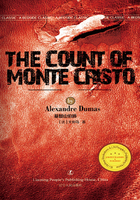天渐渐地黑了下来,荒凉的原野上吹过一丝丝晚风,饱受了一整天灼烤的这驾马车也显得有了精神,向前移动的速度加快了。
厄休拉有意识伸长了脖子让晚风自然地撩动飘在前额上的几绺头发:“好舒服,白天太烤了。”
“可是我们看不到故乡的影子了。”唐娴担心道。
“这没有关系,只要沿这条路走下去就一定能够到达。胡福先生,我说得对吗?”厄休拉问。
胡福将帽檐正了正:“我只是一个脚夫,或者叫马车夫,我只是得到信息这条路的尽头就是你们的故乡。”
“看看,我猜对了。妹妹放心吧。”厄休拉显得很自豪。
“可是不看着它我的心里总不踏实。”唐娴不无忧心地表示。
马蹄声在夜里加快了节奏,不管怎么说夜间的凉爽能够暂时抚慰旅途的焦躁。唐娴也不由地将手搭在厄休拉的腿上,厄休拉握着她的手,两个人心灵上的依靠是她们能够走在漫长希望路途中的保障,为了活跃气氛,厄休拉为唐娴唱起了古老的尼德兰民歌。
“好听,很好听。”唐娴鼓起掌来。
在冷灰色的天际飘动着一贴轻快的影子,歌声、掌声、马蹄声旋绕在空气里,如果酷热的白天躲得远一些,谁能否定这不是一次美好的旅程。
就连一向不多言语的胡福也被感动了,他居然凑热闹似地道出了他的秘密:“过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到达一个真正为我们这次旅行服务的驿站的招待。我们将换掉这架马车,东方的马车怎么说也不像礼车。对了,厄休拉,你见过十八世纪欧洲的马车吗?”
“当然见过,记得很小的时候父亲曾经赶着那样的马车送我去外婆家,印象特别深,那种马车像个花轿似的,怎么了,我们要坐那样的马车吗?”厄休拉一边回忆着一边兴奋地问。
胡福好像察觉出自己的什么问题,将声音压低下来:“或许是吧。”
唐娴没有见到过十八世纪欧洲马车的样子,只是听她们的对话自己在脑海中构想着。
不论怎么说,这段时光使她们从焦虑与煎熬中解脱出来,她们愉快地想象着。在唐娴的眼里,周围的一切好像为她编织了一个美妙的梦。她以赞许的眼光望着厄休拉,同样也望着胡福,好像幸福就要降临那样。不知不觉她也自然地从嘴里哼唱出小时母亲教唱的民间小曲《小放牛》,同样引来了厄休拉的掌声。
“很有韵律。”厄休拉夸赞道。
唱完之后,唐娴像品尝稀有的果品那样表示:“小时候的故事真是最美的。”
厄休拉点点头。她们在马车上聊着、笑着,完全忘记了胡福,对胡福的精神依恋也是她们幸福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胡福的身后,回忆幸福的童年俨然是得到了上天的保佑,至少她们不认为被抛弃了,她们正赶在回家的路上。安静中,唐娴想起她与厄休拉在路上失离的那件事。试探着问:“在我上车之前,我们是不是离开过一段时间?”
“没错,我也好奇,你好像被一团迷雾裹去了,到哪儿去了?”厄休拉问。
唐娴现在也模棱两可:“我似乎见到了我的乡亲,像是故乡的样子,但故乡在那里好像变成了一具展品。就是这样,也许是梦游。”
“要是那样我也梦游了,先是找回希望开始的金字塔所在地,就是和罔杲向往的地方。”厄休拉表示。
“看到金字塔了吗?”唐娴问。
厄休拉摊了摊手显得为难的样子:“那是多么伟岸的神殿呀!怎么像风吹跑了似的,那里的人都在手里摆弄一个个小模型,骤然间金字塔成了玩物。”
厄休拉回忆道,唐娴很愿意听她的故事,追问道:“后来呢?是不是也见到了家乡的影子和熟悉的亲人。”
“没有,倒是经历了一次非常有意思的历程,不过我感觉那也许是梦游。”厄休拉回答。
唐娴要厄休拉讲一讲梦游的内容。厄休拉摆摆手表示都是一些荒唐的事,还是不要讲了吧。
“即便是荒唐的事,讲一讲听也有意思。”唐娴表示。
“我想忘掉那个不幸,要是回忆起来,会让我发抖。开始很美妙,碰到了一位流放到一座荒岛上的白马王子。我们相爱了,共同幻想着美好的未来,齐心协力将荒岛创造成一个美丽的家园。开始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妙。我怀孕了,这就是希望。可是美好的向往才刚刚开始我就老了,时间过得也太快了,我真希望上帝在人们感到美好的时候取消时间。接踵而来的就是不幸与悲剧,那座荒岛上,我与那个流落到此的年轻王子,对不起,我这样称他为年轻王子完全是自封的,你想,岛上就我们两个人,一定就是王子与王后,共同设计着未来,天下的人都是有欲望的,不过特殊的条件使我们的欲望显得特别宏伟:通过生育使这座寂寞的孤岛变成一个热热闹闹的国家。到我老的时候,真是一转眼的事,我的子孙居然厮杀起来给我看,一开始我还想施展权威,可是没有人听我的,于是我就想早点死去,可是偏不死,又弱得四肢无力,终日里软绵绵的……”厄休拉不知不觉就陷进自己的回忆中。
“你的夫君,老皇帝也是这样吗?”唐娴细心地听着不时插话道。
厄休拉抬了一下眼皮:“一样,我们只是不停地颤抖,不光是心脏,连身体的每块肌肉都颤抖。那种日子太难熬了。”
说到这里,她用两只手紧紧抵住前额。
那也许是她生来最为恐怖的一夜,尤其是当感觉到现实还能够接受时,突然变故,制造一个预先设计好的与想象的结果相反的现实出现的时候,会使人感到迷惑和恐惧。回想一下,厄休拉与国王的最后一夜,能够猜想到底发生了什么噩耗。测量的人在他们逃到所谓的寝宫之前,大概是三个人,第二天,经历一夜的恶梦之后,她只看到一个测量员。虽然不能确定那个土地测量员是否与那三个测量员有什么联系,然而,可以肯定其中有两个测量员遇害了,被她的同胞杀掉了。就是到现在,厄休拉也是耿耿于怀,她认为如果这样的事没有真正的发生过,只作为一般的梦幻,也够她一生恼火的,何况真的经历过的故事。不管是南区还是北区,不就是一座荒岛吗?我和那个男人为了创造繁荣给了你们生命,结果,这些生命是什么,连畜生都不如,分出南北区然后相互杀戮,不把我的权威放在眼里。那一夜刻在心上了,一辈子,甚至到死也不会忘却这一无法弥补的创伤。她想,如果胡福确实能够把她带到故乡去,她就要为那一夜的悲剧立一座纪念碑。
究竟是怎样的一夜,只有厄休拉自己知道。在路上,她尽可能回避对这一事件的回忆,然而,只要闲下来,或者陷于疲倦的时候,那件事就从意识的深处渗透出来。
那两颗头骨显然是从门缝被抛进屋里的,当时断定是南区的人杀害了那两个测量员,然而,仔细地验证,两颗头骨至少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最后只能这样解释,或许岛上的时间规律不是她能够理解的。
后来,好不容易入眠,自己却被一具骨骸从床上拉起,那具骨骸分明也是从门缝外挤进来的。她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个反应就是拒绝成为他的那个世界的一员。想想,那一刻她还有人的感受吗?灵魂在那一刻很轻易地就飞走了。她像一个木偶那样被骨骸摆弄。骨骸从地上捧起那两个头骨放在案桌上,厄休拉只能一动不动地看着骨骸。案前的壁镜中央起初只是一团墨点,后来骨骸用手只轻轻摇动一下手臂,壁镜的金框就脱落下来,继而墨点迅速地扩大了,向浓浓的烟雾飞过来,烟尘的后面远远地能够听到隆隆的机械声,轰鸣声越来越近了,还夹杂着钢铁履带的碰撞声。她看清楚了,那是一台巨大的推土机,她的眼神虽然有些木讷,但这一刻,她的眼睛被带动起来,她更加惊恐了,推土机前面就是横七竖八的枯骨。随着枯骨在机械动力下向前移动,几具带血的骨骸滚落到她的脚下。面对这样突然而至的恐怖,她无所适从,她曾下意识躲开,然而,她的脚却像钉子钉在地上那样无法移动半步,骨骸的手紧紧地按住她的肩。当发动机的响声停下来,那间驾驶舱的驾驶者才看清楚,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生物,要不,就是人的变种。厄休拉见到的这个家伙,要是出现在今天的大街上,一定会吓死人。那个家伙全神贯甲,他从驾驶舱下来的时候,铮亮的光线从甲胄上划过,这对于习惯了以一种常见的认识看待人的厄休拉而言是平生以来最大的冲击,他完全是铁铸的怪物。这家伙绕开髅骨堆来到厄休拉眼前。他拍了一下腰间的按钮,裹在身上的甲胄自动打开了,他从里面脱出来。呀!看到他,会浑身上下感到不舒服,那是什么东西呢?他能够向你讲话,不能否认他是人类吧,但是,除了露出嘴唇的两颗尖锐的牙齿他的全身没有一点挺得起来的东西,也许是软体动物,他的身体肥肥硕硕,全身没有一点儿毛发,身上的皮也自上而下地垂落下来,在胯部叠成皱褶。生殖器仅仅是一个肉坠,不经意能够看到肉坠在颤动。他的脸部尤其怪诞,那是眼睛吗?眼开的形状像贴在前额上的柳叶条,斜向排列着,眼球紧紧地系在内角侧。鼻子是平的,在突出的上唇中露出两个鼻孔,两只尖牙就饰在鼻翼两端。
他来到厄休拉的眼前,咯咯地笑了一阵儿,暗红色的口腔将白色的尖牙衬托得更加犀利:“女士,你根本无须害怕,这是一种游戏,仅仅是要你见识一下还有这样的游戏。你猜,我们两个的世界谁更加真实。”驾驶员居然要自己评论一下哪个世界更真实。
慢慢地厄休拉适应了这样的景象。看到这个怪物用这样的语言刺激自己,决意捍卫自己的尊严,她告诉他,自己的世界是真实的世界,看看进化的样子,一眼就能看出美的归属。
“可是,他们是美的吗?”驾驶员顺手拎起一具骨骸用带有浓重的鼻音的口吻在讲话。这具尸骨显然还带着血,挂在骨骸上的肉丝渗出殷红的血来滴落到脚下。
厄休拉只有惊惧没有语言,她只能用不解的神情看着驾驶员。
“你知道,前面这些带血的尸骨是最近被处理的。再让你看看那些化石。”驾驶员将肥墩墩的手伸进甲胄套里,抻出一串用头颅制作的项珠,那些项珠比现实人的头颅要小得多。他戴在项上,问:“怎么样,漂亮吗?”然后美美的走上一圈。
他低着头,欣赏着那些被他称为化石的头骨,一边欣赏一边解释:“这是精心挑选的工艺品,加工过才是艺术品,对吗?”
他顿了顿,接着表示:“你以为你认为的世界才是美妙的吗。只有一个世界,看看这些化石就知道了,他们不是自称自己是你这样的人吗?几千年前这个变化就开始了,这里不过只有一块石头,想一想当初他们不是也抱着那么多的欲望被安排到这里,谁有能力主宰这块石头,我!所以,他们只能做我的装饰品。现在只有你一个人能够感受,总要留下一个有体会的人来欣赏吧。”
“那么你是否把自己现在的样子也称呼为人的形象?”厄休拉问。
驾驶员一仰头,他项下的肉太多了,只是使肉皮的纹路改变了一下:“当然,这个称谓属于我,你应该恭维我才是。”
厄休拉希望了解那些骸骨的来历:“这些原来不是活生生的生命吗?像你这样能够自豪地发笑,能够到处走动。”
驾驶员伸出手止住了她的提问:“他们与我一样?先让我更正一下,他们,也就是你们,与我不属于一类,我是蛮族最优秀的变种,是强悍与聪明的结合体,而你们只是弱小的生命在感受阳光求得活着的权利,而我们决定留下谁来感受阳光。你明白吗?”
“那,那……”厄休拉一时不知道怎样提出问题。在她还没有来得及想出问题的时候,驾驶员就又随意抓起一具尸骨悬在她的眼前,厄休拉下意识地避开了这样血淋淋恐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