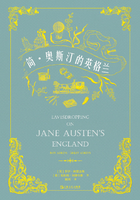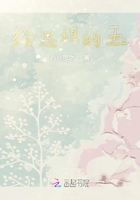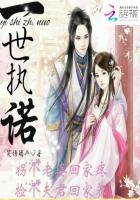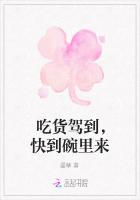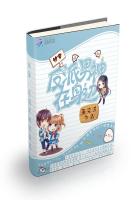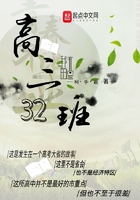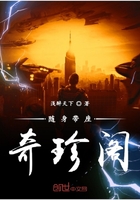子兰还不用这个幽雅、素净的笔名时,已是小有名气,在熙熙攘攘的高考大军中。言情中篇《心尘》,曾让一丝不苟、之乎者也的语文老师刮目相看,而那些自视才高情高的文科班男生一边自叹弗如一边春潮心生,钟情子兰。那时我也偶尔有一两篇短小文字在校办油印刊物《春溪》刊发,正是花一般的年纪,因为自卑,遂以莠子作名,狗尾花而已。由此结识子兰,言语相投,交好至今十五年矣。
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对于等待,简直就是受罚。子兰选修了美术专业,四月份要去金城参加专业考试,来去一周时间。这一周是十八九岁时最值得纪念的七天。在一起的时候,不觉得日子有什么特别,只一味快乐地度过。一旦分别,此地的春天仅属于莠子一人。花那么艳,树那么绿,河水依然欢快地流淌。然而心里实实在在空了许多,任是春浓如酒也难填补。
我只有独自坐在河边,常和子兰一起坐的三棵树下,头上白云悠然,脚下流水无心,真真百无聊赖。闭目瞬间,感觉有什么东西掉落我打开的书页上,竟是一朵桐花。软软的花瓣,淡淡的紫,淡淡的香,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可爱可怜。当时对桐花厚爱有加,觉得那是春天里最美的花,只缘于别离带来的善感。在树下看到的桐花团团簇簇,白色居多,不及手中花朵的粉紫,我只当远近之故。谁知过了河站在对岸遥望这三棵桐树,只见满树紫花专注而深情,我在树下看的不过是花托,颜色当然淡了许多。
总算找到新鲜的话题,我在信里告诉子兰桐花的美丽,堆砌了那么多拖沓重复的形容词,中心只有一个:希望你快快回来,不能让花儿等到凋谢。当然信是无法发出去的,只等她回来亲启。那时我们常用写信进行交流,哪怕是面对面在一张课桌上。常常连自己都觉得奇怪,两个女孩子怎么会有那么多说不完的话,还不用嘴巴,而是在笔端在一页页的纸间。
重逢被我们设计得浪漫而富有诗意,才不辜负这一周时间带点苦涩的思念。河边的三棵桐树下,许多花儿凋零于地,像飞天散落的绢花,我们把给彼此的书信铺在落花上,在若有若无的花香间解读。记得子兰信里说得最多的是金城的槐花,洁白、芬芳,又那样容易在风中飘落。结尾处还附有一首短诗.:《花落》不必寄托于风雨/凋零/是生命最凄美的部分/吻别枝头落叶/慢慢坠落/风中飘飞的残瓣/是/谁也读不懂的从容。真正少年意气,花落亦不伤悲!回想起来,那时子兰远比我成熟有主见,我在心理上也是对她依赖有加。当我们又整天待在一起,春天是那样的快乐又实在。她常常指给我看夕阳中颔首伫立的狗尾花,通身罩在落曰余晖当中,细细的草穗光芒四射,笑说那就是害羞的我,赞我以此自喻的恰当:微小但自有光彩。我便真觉得是那样,一下子自信起来,仿佛换了个人似的,从来不曾自卑。
那年的舂天除了白云似的槐花和紫雾般的桐花,令人销魂的还有芳香四溢的蔷薇。子兰家的小院里就有满满的一架,一直攀到院墙上,粉红的花朵和深红的花蕾掩映于娇嫩欲滴的绿叶之间,花繁叶茂,赏心悦目。一个雨后的星期天,我去找子兰,那时都没有电话,未曾预约,结果吃了闭门羹。隔着一堵矮墙,只见满架蔷薇被雨洗褪了颜色,红的显粉,粉的变白,低头又见遍地落英,瓣瓣带泪,越发心下怅然,郁郁离去。当晚在灯下信手涂鸦,写下几行字,题名《不遇》:长街如歌/街头有一扇久立春天的门/原想定有人在守候/守候一串敲门的音符/而当曲了一路风尘的指节/嗒然/碰上门环/那春深的小院/却拒我于门外/也许/是春风/被雨淋湿了的缘故。
好像就是那一场雨后,春天的脚步渐行渐远,火热的夏天赶我们走进黑色七月,闲情逸致统统远离。高考主宰了生活,也改变了彼此的命运。子兰考入师大美术系,一去四年,我上的中文专科,早她两年毕业回乡当了乡上的文化专干。就是那时起,我们少了书信往来,即便有,也不过断鸿零雁。毕竟没有了共同的生活环境,学校与社会一墙之隔,常使相通的文字在飞越千山万水之后有了些许隔膜,一点点的不能完全解读,逐渐拉长了彼此的距离,终于音信全无。然而在乡下,单调清寂的日子背后,更深人静的灯下夜读,稍稍走神,一缕淡淡的思念袭上心头,无数次地设想与子兰的邂逅。那时最爱唱的歌是李进的《你在他乡还好吗》,也全是因为子兰。
日子如书页飞快地一张张翻过。五年之后,我收到子兰的结婚请柬,既惊喜又意外,为赴婚宴的衣着颇费一番踌躇。然而天不作美,偏偏那天风狂雨暴,进城的山路滑坡,我只有托人送去贺礼,遥祝子兰婚姻美满幸福。未能亲见闺中腻友穿上婚纱的模样,至今忆及仍隐隐生憾。很快我也准备出嫁,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请子兰做伴娘,已经当了妈妈的子兰拋下怀中娇儿欣然前来,陪我站成婚礼上最亮丽的一道风景。
同在小城,前后结婚生子,莠子与子兰前缘再续,开始了长大后相对成熟的友谊。关爱和体贴,理解和支持滋润了这份不同寻常的情谊。
又是一年春来到,一心想调回城里工作的我事未办妥,单位又收假了,2月14日,情人节那天我把孩子寄在母亲家,告别爱人去乡下,颠簸在乡村公路上,一颗心扯了八瓣,孩子、工作、家……正愁闷着,子兰手机上发来一首七言:
诗里日月无冷暖,砚底墨迹留浅深。
抬头忽见新蔷绿,始觉人间又一春。
隔着车窗,公路两旁迎春怒放,樱花如海,的确是春天了,念友人深居小城,见新绿而知春至,觉春色而告故人,想必是愿与我一同体味这份欣喜,可我正愁肠百转,叹事不遂心。感喟罢,遂步韵和之:
道中山水沐风暖,眼底云烟变幻深。
每忆人生难如意,雪海樱花不似春。
子兰却笑叹我消沉,不该在万物皆有生机的春天。
然后用非常女人味的口吻发信:鸟儿都想在春天里换一身新的羽毛呢,你去买套漂亮衣服穿上吧,心情一定能好起来!暧暧的真诚,切切的关心,乡下的春景竟一天美似一天。
自此,两人短信往来,时有唱和,虽多为风花雪月,然求一美字,若凡常琐屑,则得一真字。于子兰或大气、或工丽、或豁达、或率真的文字间,莠子重拾自信,告别曾经的放任自流,一心要写一笔锦绣文章。子兰在此时是诤友,阅我文字,有缺点即当面告知,有佳句遂大加赞赏。正是她文字功底及博学多才的吸引、不倦好学精神的激励,使我在文字上大有进步,2004年她鼓励我参加市文联组织的散文诗歌大奖赛,获了三等奖,这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同年底,我从乡文化站调回县文化馆,有了更好的环境来写作,也有了更多的时间与子兰在一起。
仿佛春天从不远离,不见面时,我们作诗互赠,咏春、惜春、伤春、叹春……正着意“桃红柳绿正当时”,忽又叹“名花已逐春归尽”,峰回路转才发现“层碧却胜万千红”,有多少花开就有多少春天的情谊;待到面对,融融春日总给我们奇好的胃口和口味,榆钱、槐花、荠菜、地衣……任谁的妈妈做出来都是美味,餐桌上刚吃罢,立马又跑到街上,一个店一个店地找最早上市的冰激凌,各人手执一盒,旁若无人地穿过闹市,边笑边吃,倏忽又回到少年时光,青春一点都未曾走远。细雨霏霏的日子,牵手在河堤柳岸,看远山如黛,山岚岫烟皆脉脉有意,又引发几多诗情:“风流谁竟华发客,不信诗心属少年!”是子兰的洒脱和豪性。
真的像诗人一样,我们总爱在一起喝点小酒,微醺的醉意中,心与心更真的谋面。两个尘世间的女子,一壶五谷酿的浊酒。彼此把心事抖落,无非寻常琐事,说得最多的还是自己的爱人自己的家,都觉得那个曾经很优秀的男人婚后怎么有点懒散了,她说:男人心,没深浅,我的死活他不管!我劝:好妹妹,不要哭,如今流行女休夫。她即佯怒:要休你先休,榜样做前头……于是唇枪舌剑,叽哩呱啦,旋而情不自禁,哈哈大笑,常惹邻座侧目。恍恍然重回年少轻狂。陶醉了那么多休闲、快意的日子,别离已近在眼前,子兰就要去北京深造。阳光明媚的午后,送伊归来,独倚小楼,“我欲疏狂醉韶华,手持长盏待故人。”是莠子的深情和执著。
但我们从未断了书来信往,总是将自己深藏心底的温柔化作丝丝屡屡的感悟赠予彼此。突然的想念、细腻的消磨、快意的协同、默契的联合、相互的鼓励和促进……总觉得在同性当中这种近乎肝胆相照的情感应该不多,弥足珍贵。诚如子兰所说:从不谙人事的少年到七情味尽的中年,我们相携一路走来,心心相通,视彼此为良友、诤友、腻友、至友,在这世上,拥有这种大概不算是平凡的友谊,真可谓一大快事!可是有几天我忙于杂事忘回了子兰来信,直到惹她生怨,雨天发信给我:下了一天雨,想了一天你。鱼沉雁无凭,幽恨知几许?一下子,我的心像被揪了一把,自责、内疚、怜惜一齐袭来,赶忙拨通电话,一番长聊,知道彼此都很好,心中无限快慰。
年年的春天都很准时,花儿如期绽放,桐花依旧那么紫、那么唯美,我坐在开花的桐树下,四月的风中,想起子兰,心里满是花开的声音。想要在这个春天里写点真实的文字,关于莠子和子兰。趁桐花正盛,落下笔来,却是人间四月半,桐花次第开。山山横紫雾,为待伊人来。还有一直没有说出的话:子期遇伯牙,春天喜欢你,平平仄仄律知己。
200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