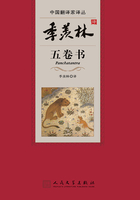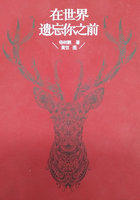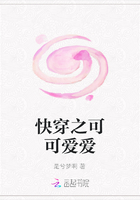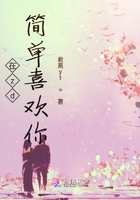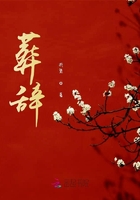父亲的二婶第一次来我家,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一双小脚,很玲珑的模样。那时候不过六十出头的样子,一点没有小脚老太颤巍巍的走姿,人也生得端庄,于是当母亲让我喊“二婆”的时候,我还有点不好意思,觉得太年轻了些,有些喊不出口的羞涩。二婆却亲亲热热拉我的手,从随身的包袱里拿一双绣花布鞋送我,黑色平绒鞋面绣着粉粉的一枝荷花,草绿色丝线点缀的浮萍,鲜艳得土气。虽然不大喜欢,我还是很高兴地收下了,毕竟是父亲的长辈啊。
二婆来是让父亲给她的孙子联系上成县师范的事情,只是成绩差1.5分,未录取。二婆很是失落,母亲留她多住些时散散心,并让我和二婆同睡。我那时候刚上中学,一味地喜欢读琼瑶,二婆每每见我伏枕夜读,一边心疼我睡得晚,一边自己也睡不着,干脆让我读书给她听。这可真是难为人,当时看的是《失火的天堂》,书中的情节不知赚了我多少眼泪,哪里又能读得出来啊。二婆看我不情愿,也便作罢。只是我心里存了点内疚,打算第二天找本故事会给二婆读读。
次日放学回家,母亲却领二婆去鸡峰山游玩了,直到太阳落山才回来。二婆一脸的疲惫没掩住心中的兴奋,草草吃了饭上床给我一本书让读给她听。是本油印的《因果报应》,里边的语句简单明了,我让二婆自己看,她这才说:我不识字啊。于是我逐字逐句给读了一遍,然后又给解释了一遍。二婆方才安心睡觉,我依然读琼瑶,大半夜了,放下书睡的时候发现二婆大睁着双眼,眼角分明有星星点点的泪光,我也不敢多问,一会便睡着了。
从那天起,二婆在我家的半个月日子过得可真是快乐。白天给我们看家,中午回来午饭已经做好了,手擀面又细又长,我们兄妹四人放学迟早不一样,二婆耐着性子给我们一碗碗煮面条,回来早的吃完了,又给回来晚的煮,总是笑眯眯的。有时候是烙饼,厚厚的馍饼看上去白的像生面似的,吃起来却香甜的有如面包。二婆真是好手艺,要知道用柴火在铁锅里烙饼,靠的就是把握火候,不疾不徐,才能熟得好还不焦。到了晚上,二婆最感兴趣的就是我教她念《因果报应》,一本小册子都让我给翻烂了,内容我闭着眼都能背下去,可是二婆整整学了十多天才勉强记下,每见她磕磕巴巴地让我听她背书,我心里就起了疑团,二婆为啥痴迷于此呢?等有机会一定要问问母亲。
那次送二婆回去,一家人依依不舍,二婆没有忘了她的小册子,我也没有忘了问母亲关于二婆的事情。母亲说二婆在鸡峰山上信了和尚的话,说我那已经去世三十多年的二爷成了神,就在鸡峰山的二字殿里,只要二婆好好信佛,天天念因果报应的口诀,百年之后就能和二爷相见。
原来如此!那么二爷是怎样早早离开二婆的呢?
父亲接过话题,叙说了当年二爷怎样替自己的地主老子去接受劳动改造,又怎样悄无声息地客死他乡,丢下可怜的二婆和唯一的儿子。孤儿寡母的日子熬不下去的时候,二婆也想过改嫁,可是大家族的规矩束缚着她,于是一年年的耗干了眼泪和青春,一颗心慢慢灰了。好在日子有大家帮衬,倒不至于忍饥挨饿。
父亲说他的祖父母健在的时候,全家共有三十多口人,吃的大锅饭,一起劳动一起分粮。二婆家虽然人口少,按股数分来的粮食和棉花却总是能余下一部分来,二婆往往将棉花纺线织布,然后托人去换钱。终于拉扯大了唯一的儿子,后来在本家兄弟的帮助下娶亲成家,至此,二婆算在他们的大家族中赢得了尊重和名望。
我从父亲对往事的叙说中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凝重,虽然大家都说二婆是熬出头了,可这一个“熬”字饱含了她多少孤灯挑尽不成眠的寂寞和辛酸?
从那以后,我对二婆的感情有了更多的怜惜,母亲也一样,每年一次回老家,总不忘给二婆买一双软软的小脚布鞋。二婆留我们小住几日,三茶六饭的招待,仿佛我们不是还乡而是做客来的。也就是从那时,二婆开始吃斋,心心念念记着和尚的话,每天诵口诀,不敢有丝毫懈怠,都只为自己半生的相思和爱恋。我是不相信来生的,可是我不忍也不能打碎老人的梦想,每见二婆念念有词,我不由别过头,将眼底的泪水退回心里去。
后来二婆又来过两次我家,主要是去鸡峰山上香,两次上去都是在山上住了一晚。记得那回从山上下来,一进家门二婆便给我父亲哭诉一番,说她昨晚在山上梦见二爷了,还是年轻时候的样子,只是不和她说话。二婆问我父亲:大侄子,你说是不是我信佛的心不诚,你二爸才不肯给我说句话?我看见父亲一下子连眼圈都红了,很尴尬地笑着,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好在母亲接过话去,安慰二婆不必这样伤感,说假如能见到的话早晚会见到的,二婆这才好一些。
等我参加工作的时候,二婆已然老迈许多,不能坐长途车来我家了。父亲还是一年回去探望一次,我没有什么好送给老人家的,只托父亲给二婆一点零花钱,让她想要点啥自己去买。后来我结婚,二婆打发她的孙子送来一大袋子自家地里的棉花,雪白絮软,母亲给我絮了两床被褥,转眼十年时间过去了,被褥柔软如新,温暧如故,仿佛二婆和母亲的怀抱。
几年没见过二婆了,想起的时候拿出早年的绣花鞋来把玩一阵,鞋子不但小,颜色也褪得很淡很淡,似乎也就穿过一次,洗过一回就成这样的了。可是多年来没有舍得丢掉,我自小没有了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对二婆的感情是最单纯的隔代亲,真挚而朴素。
终于有时间和父母再次回老家,是前年秋天。和往常一样先去看望二婆,晴朗的天气,大家坐在堆满玉米棒子的小院闲话家常,鸡们在凳子下钻来钻去,抢食散落的玉米粒。二婆手拄拐杖坐在高凳上,一张脸笑成绽放的菊花,重孙儿偎在她腿边啃苹果。我赶紧拿出相机拍下了这温馨的一幕,回来放大洗出来细看,二婆老态龙钟,一颗牙都没有了,未免惆怅了一阵。
去年中秋再回去,我把照片拿给二婆看,二婆的视力竟然也不好了,远了看不清,近也看不清。但还是非常高兴地拉我的孩子在跟前仔细端详,说她现在不行了,要是早几年还能给娃做鞋哩。其时二婆坐在靠墙的沙发上,告别的时候,老人家努力了几次才站了起来,可到门边就跨不动门槛,只好站在屋内送我们远走。出了院子我回头张望,看见二婆用袖子拭泪,母亲叹息说二婆不过一年半载的客了。
转眼到了春节,父亲念叨说元宵节后还要回趟老家,再看看二婆去。谁知正月初六父亲却因为心脏病辞世,我的世界由此黑暗了整个春天,在无望的思念和彻骨的心痛中熬过了一天又一天。我常常想起二婆来,想要在她的面前痛哭一场,可是我不能也不敢,据老家来奔丧的叔叔说,大家一直没敢告诉二婆我父亲去世的消息。直到给父亲烧尽七纸的时候,终于让二婆知道了,当时大恸9却已经没有了眼泪,很快便也病倒,一直到上个月农历十五的夜里与世长辞,终年八十九岁。
我因为母亲身体的缘故,未能回去送别二婆,心下时时不安。在二婆离去的又一个月圆之夜,写下上面的文字表达我的怀念。同时焚一炷心香,虔诚地祈祷老人家在另一个世界里见到她思念和牵挂了一生的人。但不知是否也遇见了我的父亲?
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