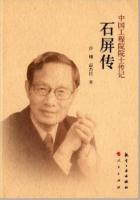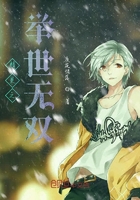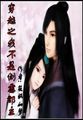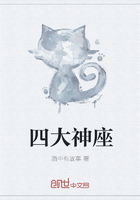梁以上的这些话是出自内心的。正因为他有了认识,提高了觉悟,所以,对以后的事处理起来就顺利多了。比如,1957年3月,******总理在京召集少数知名人士座谈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梁应邀出席并讲了话,表示赞成了意见。他说:“一让两有,一争两丑,汉族与少数民族都要以对方为重。”他的议论受到与会者的重视。周总理在总结时,特别强调说:“今天,汉族应该多多替少数民族设身处地想一想,不要让他们再受委屈,应该使他们也能得到较好的发展条件,只有汉族主动地替少数民族着想,才能够团结好少数民族。我同意梁漱溟先生在这次会议上说的一句话,要‘互以对方为重’。”后来,梁先生在回忆起这桩事时,若有所思地说:“当时,黄绍竑反对说,我们汉族是多数,为何要改?周总理给他解释,他听不进去,后来成了‘****’。”接着梁又说:“我犯错误早,问题已经过去,我又没什么‘****’的那种表现,所以‘反右’时没有我。因为我同意广西改为自治区,总理说广西人不了解情况,要我回去宣传需要改的理由。”后来梁受周总理委托与陈迩冬、陈北生、载涛同行,先后到梧州、南宁、桂林、柳州等地与各界接触,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为促进自治区成立而做出贡献。
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梁漱溟仍然过着极为平静的生活,除参加一般的政治活动外,多是在家学习马列主义、******的著作及党的政策文件,有时也写一点回忆录之类的文章。然而,到1965年后他又出事了。事情是这样的。
1965年初,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总理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总结近年政府工作的成绩与经验,全国政协委员列席听取了这一重要的报告。会议后代表与委员们均分组认真学习,讨论了这一报告。在政协分组会上,委员们纷纷发表意见,称赞总理的报告从头至尾都贯穿着一条阶级斗争的红线,因此这个报告非常好。并称,15年来成绩之取得,主要是由于抓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等。梁对大家的发言持有不同意见。在他看来,1956年9月,****八大的《决议》中已经说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当前,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根据上述决议的精神,他认为现在再来强调以阶级斗争来解决一切问题,怕是过时了。然而他又没有把握说阶级斗争不起作用了,于是他决定自己说自己的话,谈自己心得体会,各抒己见。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作了一次发言,大意是说: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论列的许多事情,在他看来,从头到尾贯穿着两个大道理,第一个是我们要认识必然以争取主动的道理。所谓必然就是指一切客观规律而言,认识它我们就能争取主动,反之则变为盲动,结果是到处碰钉子、失败,无自由可言。第二是要信赖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这样便能无往而不胜,完成任何艰巨的任务。前者重在客观事物规律的认识与掌握,后者重在人类主观的能动性的发挥与表现。前者为科学之事,后者为道德之事,两者缺一不可。但后者尤其重要,因为人是最重要的,一切都依靠人。最后,他总结说:“在革命进程中,****从建党、建军而建国,40多年间不断总结经验,掌握了种种客观规律,时时操有主动权,其势如破竹也是当然的。伟大奇迹之出现,我以为以此两大道理解释之,说明之,似乎更切题,更有说服力。个人体会是否得当,请指正。”
梁的这一发言,其见解与众不同,于是引起与会者的批评。有人就质问他说,大家都谈阶级斗争,你却只字不提,而大谈什么两个道理,用心何在?又有人揭发他说,梁漱溟一贯否定阶级斗争,以自己的那套唯心论来曲解周总理的报告,本身就是阶级斗争。梁听了大家的发言,认为是乱扣帽子,不作理睬。然而此事并没有到此停止,后来在政协闭幕会议那天,主席团在大会场内向来参加会的近千名出席者散发了一份批判梁漱溟的书面发言,指责他“否定阶级斗争,曲解周总理报告”,“否定党的阶级路线”等等。梁看了十分气愤,认为大会没有印发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不公平,而且是断章取义,实不足以服人,于是要求大会给他答辩的机会,并写了一封信,亲自交给了******。后来因为时问不够,闭幕在即,不可能在大会上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所以周总理在作大会总结时对这个问题作了特殊处理。他说:这次大会是一个团结的、民主的大会。在谈到民主时,他指示说:有一个委员要求辩论,可以在会后安排,充分发扬民主。会后不久,政协负责学习的人告诉梁说,他写给主席团的信,已经转到学习委员会了,以后可以在学习会上进行辩论,希望他做好准备。
这次学习组的辩论会,参加的人数大约有30余人,时间是从1965年5月至10月,每周两三个半天。名曰辩论会,其实是批判会。梁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批判’,而毫无‘辩论’之意。……我听了也就不想再多说,因为说多了也无益。但辩论是我主动要求的,我却不能不说话。因此,我在1965年8月3日作了一篇将近8000字的答辩言,重申我的本意和观点。自此以后,我就是履行每场必到、洗耳恭听的任务了。”所以,这场辩论或者说批判搞了近半年的时间,没有什么结果便停止了。但这不等于说梁就没事了,后来,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更猛烈的雷鸣电闪的批判会还在后头哩!”
“**********”中坚持反对“批孔”
1966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开始了“**********”,在这场十年内乱中,梁漱溟也未能幸免于难。8月24日那天,他们家突然来了许多气势汹汹的红卫兵,说是来“造反”的。梁说既是来造反的,那就请便吧,抄什么都行。几个红卫兵翻箱倒柜,搜遍每个角落,把所有书籍,除马列主义及******的著作外,统统拿到院子里,一边撕,一边烧,其中有许多是他们家几代人保存下来的文物、字画。梁当时看了很心疼,但也无可奈何。后来,看到红卫兵从屋里抱出两大本洋装书,一本是《辞源》,另一本是《辞海》,梁上前阻止说,这两部书是谁也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从外地学生那里借来的。如果烧了,我就无法还人家了,是否可以留下?红卫兵不理他,把书扔进火海,嘴里说道,有现代化的《新华字典》就够了,用不着这些老古董。梁在一旁看着,心里十分难受,暗想造我的反,造我祖宗三代的反,我都忍下来了,唯对这两部普通的工具书也不放过,使我无法物归原主,乃终生遗憾之事。这且不说,他们还揪斗了梁的妻子陈树棻,让她跪在地上吃生丝瓜。梁上前说,她那么大年纪了,不要折磨她,结果自招其祸,红卫兵喝令他也跪下。之后,梁的住宅变成了附近一个学校红卫兵的司令部,梁被赶至南屋,一问日常存放家具的小屋。他每天打扫街道、厕所,有时还会被抓去游街、批斗。待游斗完毕,又把他关进这间小屋,写交待材料。这样的生活一连被折腾了20多天。
9月7日那天夜里,他突然悟到他的问题必须上书毛主席才能得到解决,于是开始动笔,10日寄出。其内容大意是向毛主席反映被冲击的情况,要求发还他的文稿,以便写作,实现他撰写《人心与人生》一书的宿愿。信云:“近年来,我正在撰写此书尚未完成。此番抄家,一切文稿全被收去。假如在或斗或批之后,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续写,无异乎宣告我的死刑。……人的生命是与其向上心不可分离的;失去意义的生活,虽生犹死,生不如死。以故家中书籍几乎全数被收或被毁,钱财百分之百被收去;衣物等等被毁被收者百分之九十八;在我举不足惜。唯求发还我的那些书稿,准许其续写成书。”此信发出不久,书稿被退回来了,他感到很高兴。
梁虽然处此恶境,心情仍然平静。从9月21日起开始写《佛儒异同论》,每天写1000多字。在这篇2万多字的长文里,他首先将儒佛两家同与不同之处作了说明,略谓:儒家从不离开人来说话,其立脚点是人的立脚点,说来说去总归结到人身上来。佛家则反之,他站在远离于人的立场,总是超开人来说话,更不再归结到人身上——归结到成佛。这是不同之处。其相同或说相通之处者有二:一是两家为说不同,然其为对人而说话则是一样的。二是两家为说不同,然其所说内容为自己生命上一种修养的学问则是一样的。接着对其上述论点进行分析、论证,其异同之结论可归纳为:儒家是入世之学,肯定人生;佛家为出世之学,否定人生。二者不相同,可是,都是讲求实行修身养性的学问,不是西洋古代所说的“爱智”(philosophy哲学)思想,如果把它当做哲学来看,那是不懂儒、佛,都是外行。是文写成后,他又接着写《东方学术概观》等长文。梁的生活条件随着运动的发展,政策的落实,条件也有所改善,行动比较自由了,可以到各个公园散步,上街购物,一边学习,一边写写稿,生活倒也还可以。到1969年五一节,曾被邀请到天安门前观礼台上观礼,政治待遇有所改善,政协的学习逐渐恢复,从此梁的生活条件有了显著的改善。
到1973年10月,江青等人突然提出在全国范围内要“批林批孔”,其实目的是要打倒******总理,这在当初是不为一般人所得而知的。运动开始,全国政协组织学习,梁出席会议。在学习过程中,大家都表态,发言表示“支持”、“拥护”,并狠批“孔老二”,其实多是说些违心的话来敷衍。这样的学习,时间过去1个多月,而梁在会上却一言不发。这个情况自然要引起与会者的关注,于是就有人向他提出警告说:“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里面有感情问题,也有立场问题。”还有人公开指名道姓地说:“如果梁先生也向北大某教授学习,公开表态支持批孔,影响将会更大,大家都会欢迎你的转变。”梁听了直摇头,回答说:“某教授文章我拜读过,我疑他的文章是否说的是他心里的话。”此言一出,会上气氛骤然紧张,有人就严厉地指责他说:“你有什么根据怀疑别人?就凭这句话,你反对批林批孔,的态度已经暴露无遗。奉劝梁先生不要再一次做运动的对立面了。”梁听了只是一笑,没做回答。
这种情况相持了一段时间,后来不发言好像不行了。到12月14日,他才在学习会上说:“此时此地我没有好多话可说。这里是政协学习会,‘政’是政治,必须以当前政治为重;‘协’是协商、协调,必须把一些不尽相同的思想、意见求得其协调若一。因为我们都是从四面八方来的人,原不是一回事。怎样求得协和、协调呢?那就是要求同存异。毛主席多次说过,允许保留不同意见。我对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我有话要说,我准备专门写篇文章。但我的文章不能公开,怕有碍于当前的运动。”梁的话音一落,会上就有人反驳他说:“有话就摆到桌面上来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梁回答说:“我的文章太长,要在会上讲,会占各位许多宝贵时间,还是写完后交给领导参阅更好,不必公开。”这时,主持会议的人说话了,他说:“讲与不讲,由你自己定。但时间长没关系,听听你的高见,我们愿意奉陪。”梁见此情形,觉得退路没有了,于是答应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