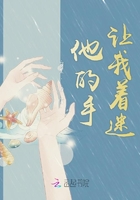谷子地不仅仅是一个人,他代表了一种价值观:牺牲、责任和奉献。在利己、自私和冷血的和平时期,这样的人,一定会处处伤心。我们认为,他会死,无疑是认为,在和平时期,这样的价值观,一定会处处碰壁。然而,我们都不忍心让他死。
他死了,就说明,他失败了。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一个失败的结局?一时的碰壁,一时的伤心,就能说明一定会失败吗?我们都觉得这样的价值观会处处碰壁,但看看我们的周围,为什么,大多数人还是相信、向往并且去身体力行这样的价值观呢?
所以,最终我们觉得,谷子地一定要活。
谷子地会活着,我们要他好好地活着。
但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他怎样才能好好地活着。所以我们给他选择的解决方式是,他的努力,终于等到了上面的认可,国家的认可。
这个结局,是个结局,但其实,不是最好的结局。
但这一点,当年,我并没有认识到。其实,一直到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后,我才忽然找到了,谷子地最好的结局。
当然,这是后话了。我对《集结号》的认识,是我的2007年一次完美的注脚。
每一个牺牲都永垂不朽。
你是否记得,《集结号》中,有一场狙击手浑身着火的戏?拍完那场浑身着火的戏,我竟然无比兴奋。
我感觉到,我像个男人了。
在东北,我总觉得,我特脏。零下二十多度的辽宁省,抱着十多公斤的枪跑来跑去,每天在冰天雪地里浴血奋战。不但衣着单薄,而且整天经受着炮火的洗礼,经常弄得满身是泥,狼狈不堪。我们总是脏兮兮的,脸上全是泥,钢盔再一戴上,看不出谁是谁了。一看镜头回放,只剩下两只大眼睛。
但我的灵魂,却无比纯净。
就像电影宣传词里写的一样,"每一个牺牲都永垂不朽"。当我拿着枪四处奔跑的时候,我真的想起了那些扛着真枪实弹打仗的前辈军人们,不同的是,他们面对的是真的炮火,真的坦克,真的流血,真的牺牲。所有人都一样,都是骨肉做的,珍贵的生命也只有一条,人在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本能的就会有求生的意识,而在战火纷飞中,在求生和为胜利求死之间,又有多少的勇士选择了后者呢!
这种顿悟让我常感觉自己生在和平年代的幸运。
我记得,拍这出戏的时候,拍戏的间隙,我们都特别会苦中作乐。
没有戏拍的时候,我们都会找一个阳光好的地方晒太阳。我们这个戏,要么就是在雪里一趴趴好久,要么就是一跑跑好久,反正无论怎么拍,真的都挺不好过的,趴着就冻死,跑步就累死。在这几个月里,晒太阳成了我们最好的享受。
每天晚上拍摄结束后,九连的兄弟们都会拎着红酒,到廖凡的房间里去打牌、喝酒、聊天--因为廖凡的房间里有张大床。我们都瞄上了那张大床--睡在那样的大床上,该多舒服啊。
廖凡实在太有意思了。他总是跟我说:"宝强,大家都是兄弟。"于是我就会跟他开玩笑,"凡哥,皮鞋不错啊,哪买的?""凡哥,皮带不错啊,哪里买的?"他都会一挥手,说拿走。
拍戏冻得不行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去捡点柴火,生火,烤火。火苗映照着我们的脸,我看着他们,觉得他们就是我的兄弟。在咚咚的炮火声中,在每天的烤火和玩笑中,就这样,我们都成了兄弟。
那一刻,我觉得,我是个男人了。
电影《甲方乙方》里,冯小刚借用葛优的角色说: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2007年年终的时候,我在新浪的博客上写了三句话:
200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2008年开始了,我要好好活,做有意义的事。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第一句,我借用了冯导的创意。第二句,我借用了康导的创意。第三句,我借用的据说是但丁的创意。但不论如何,这真是让人难忘的一年。在这一年里,生活像过山车一样,从这头翻到了那头。
写完这几句话,我记得,我在发呆,呆了好久好久。我起身,去洗手间,洗了把脸。擦脸的时候,我在镜子里,看到一个年轻人。他不再是八岁时跟在母亲身后哭哭啼啼的那个男孩,也不再是十六岁领奖时茫然无知的那个少年。这个年轻人有一张平凡的脸,不白净,不平滑,坑坑洼洼,但那双眼睛,坚定而宁静。
我望着那双眼睛,轻轻地微笑了--那条黑暗的、不知道尽头的胡同终于消退到了身后,或许,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抱着枪跃出那条长长的、阴暗的战壕时,我也跃出了那条黑暗的、不知道尽头的胡同。
"嘿,好样的!"镜子外的我,悄悄地对镜子里的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