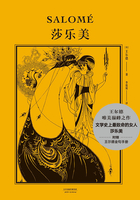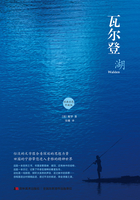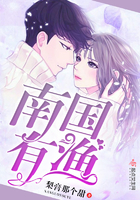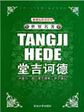从这段时期蒋介石的日记里就可以看出,1942年国内国际形势异常复杂,作为政府首脑的蒋介石也承受着巨大压力。
9月初,蒋介石到西安召集军事会议,蒋鼎文再次呈报灾情,希望河南军粮问题能够引起中央足够重视。蒋介石高度重视,但由于对事实情况了解不清,他认定所谓军粮问题,完全是由于粮政人员办事不力所致,并不是因为粮食缺乏。
蒋介石因此规定,以后县长的考绩,军粮和兵役各占35%。第一、六战区可以设立战区粮食调查处,凡是百石以上的大户人家,调查清楚之后,即转交省政府管理统制,以备不得已时就地征购,接济军食。考虑到河南遭灾的特殊情况,蒋介石同意河南的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并把西安方面的部分储粮迅速运往河南,以解燃眉之急。
1942年9月后,随着救灾工作的展开,河南省救灾委员会相继制定了《紧急救灾实施办法》、《奖励各县绅商富户自动救济灾贫办法》、《节食救灾办法》等政策法规。并设立难民收容所,较大程度上缓解了难民的无序逃亡。河南省政府卫生处抽调精干力量,组织临时防疫注射队,为鲁山等地的难民注射疫苗,减少了一些无谓伤亡。针对流向陕西的难民人数众多问题,河南省赈济会在洛阳设立了办事处,主要工作是有序运送难民。省政府并致电陕西、湖北、安徽等邻省,呼吁“各本救灾恤邻之旨,对豫民入境赐予安置”。 虽然政府做了相当安排,但临近冬季之时,灾民死亡率还是急剧上升。个别地方甚至还发生了卖妻卖儿、易子而食等耸人听闻的事情。
对于严重的灾情,河南及周围军队各部都给予灾民积极帮助。蒋鼎文接到各部队目击各地灾荒的报告,提倡第一战区全体部队参与救灾,具体办法是每月减食两餐。杨虎城的旧部第四集团军第38军在驻地汜水积极响应,办起一个规模不小的粥厂,每天固定开24锅,有时还根据情况临时增加。汜水周围的饥民经所在村开具介绍就可发票领粥,就食者每日都在千人以上。第17军驻渑池官兵配合节食救灾,先是省出了15万斤粮食,后又拨款开设粥厂11处,增加节粮力度用于施粥。第三十六集团军把节余下来的4万多斤粮食交由各级政治部,会同新安县政府、地方保甲长散发灾民以资救济。陕西关中地区的胡宗南部第三十四集团军,1943年春自发节食十日,共得面粉5 000多袋,由豫省驻陕粮秣处汇扣拨交。
河南驻军很大一部分是属于汤恩伯系统的中央军,该部也积极参与救灾。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第13、29、暂15军全军,三一分监部,独立第14、15旅等部,从1942年10月至1943年5月,共计节粮128万斤,用于救济赈灾。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又分两次放出小麦、杂粮等军粮600石,用于救济漯河大新店镇一地灾民,此地当时没有饿死一人,这在河南大灾中实属罕见。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部、第十五、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骑兵第2军及骑兵第8师,第85军等部,也从1943年1月份至5月,筹得赈灾粮125万斤。此外,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又单独捐出赈灾粮15万斤。
1942年的河南,当时是抗日最前线,并不是大后方,占据河南的既有国军,也有日军、共产党军队、豫西土匪等各种势力,占据区犬牙交错。救灾中,当时的国民政府事实上做了一定的工作。现在还留存有大量当年河南国统区赈灾文章、历史照片,政府不但在各车站、集镇、街道广泛张贴有抗灾标语横幅,还开仓赈灾。此外还有政府专门开通免费火车组织疏导灾民坐火车前往陕西、甘肃逃荒的照片。
在此次救灾中,何应钦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举措就是大量收容灾童。1943年3月,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来到中原大地,用相机拍下了沿途见到的一切,而这一切使他感到无比震惊。这位美国记者说:“我认为汤恩伯不失为一个好人,他命令所有的军官都要在营房里收留一名灾区孤儿,所有的士兵都要从每月的配给中扣下一磅粮食分拨给受饿的人们。”
1944年4月17日,日军发起了“一号作战”。大战再次在河南爆发,日军依靠庞大的机械化部队,大有横扫豫中平原之势。日军围攻许昌时遭遇国军顽强抵抗。激战至30日晚上,防守许昌城的新29师伤亡惨重,师长吕公良壮烈殉国。蒋鼎文的司令长官部被日骑兵部队包围,多亏他的一个参谋长亲率警卫部队将日军引开,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才得以脱险。蒋鼎文深知河南战局险恶,在官庄临时战斗指挥所给夫人和胞弟写了一封绝命家书,其中写道:“我早已以身许国,且为职责所在,一息尚存,当与暴敌拼,人生几十年,免不了一死,生死关头,我一定认得清楚,望勿以我为念。”
5月21日,第三十六集团军总部行至河南陕县秦家坡,遭到日军伏兵袭击,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为国捐躯。24日,日军突入洛阳城内,守军第15军及94师与敌展开最后的巷战,次日8时,洛阳失守。
豫中会战日军伤亡约4 000人,国军的损失更大,据日军统计,阵亡和被俘者超过4万人。
就在中日河南浴血惨烈大会战期间,包括第四集团军在内的许多参与过救灾的军队,都不同程度遭到当地民众袭扰。当时社会秩序陷入一片大混乱之中。据史料记载,当时有铤而走险拦路抢劫的,有与讨麦士兵发生武装冲突,以致互有伤亡的。各县都有数千民众,向县政府缴契、缴农具、请愿,甚至捣毁乡公所、区署、发起群体暴动的。此种现象,可以说是在河南境内随处可见。
当国军士兵面对日本“一号作战”撤退时,乡民们更是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还杀了一些国军,有的士兵甚至被活埋。豫中会战中发生的河南民变和1942年的大饥荒一样,同样值得今人反思。
1945:胜利来得太突然
这场险胜来得又太快了,而为了这场胜利,中国人民等了整整14年。在这漫长的14年中,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就展开过22次大型会战,1 117次中型战役,38 931次小型战斗。其中国民党261名将军战死疆场,陆军伤亡、失踪、负伤3 211 419人、空军阵亡4 321人、坠机2 468架、海军舰艇毁损殆尽……
1945年8月15日,中华民国政府主席蒋介石,在重庆向全国和世界发表胜利广播。
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经重庆电台传出,重庆市民大放爆竹,欢欣之状空前。1945年9月9日上午九点,在南京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举行受降仪式。之后的一个月中,在15个受降区,分别接受了日军投降。直到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中山堂受降仪式的完毕,才宣告中日相持了50年的两度战争到此正式结束。
直至今日,有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当日本投降时,很多中国人乃至国共抗战的最高级领导人都深感突然和意外,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不乏对抗战一直持有悲观情绪的人,甚至在胜利到来之后仍然“后怕”不已,连呼惊险,庆幸侥幸获胜。李宗仁在回忆录里毫不掩饰自己的判断:“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卢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所以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都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
这场险胜来得又太快了,而为了这场胜利,中国人民等了整整14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人就像在炼狱中一样熬过了漫长的14年。在这漫长的14年中,中华大地上历经无数次惨烈的战役,有官方数据统计,自1937年到1945年八年的正面战场中,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就展开过22次大型会战,1 117次中型战役,38 931次小型战斗。其中国民党261名将军战死疆场,陆军伤亡、失踪、负伤3 211 419人,空军阵亡4 321人,坠机2 468架,海军舰艇毁损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