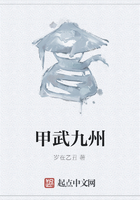“也亏得了然师傅平日里还自称将万事参透,事到如今还妄想佛祖将我等脱离苦海,带至在极乐世界么?”卞朗言语颓唐,兹因秦难相视,不得已将已是褴褛的布衫规整了规整。
“唉,某当时真该一掌击毙你——左思右想我等弟兄之中可作细作的也只有孙良兄弟了,没成想平日里于弟兄近旁竟有你这么一头养不肥的白眼狼。”了然声调低落,狠瞪卞朗,不料胯下坐骑受了大当家的秦难重重一鞭,咴鸣几声,紧跑几步就由随马变作了引路先锋。
“事到如今,我等仇敌已非不仁不义的冷山朝廷、更不是紧追不舍的乌崖谷红衫军,已是我等众人之中渐生弥散之意的人心。我等弟兄切不可再生出内讧了。眼下要紧之事是寻一处落脚之地。”秦难略略扬了扬嗓音,挥手示意众人慢些前行。
“兹是我等可往何处去?”孙良于秦难身前道。
宁怡叹了一声,“政客变起脸来比我等这些只认钱的江湖客来得还快;卞朗,不若劳你拉下面皮去至在乌崖谷,疏通关系将我等隐藏于你祖国之中,使一个险中求胜的手段来?”
卞朗垂首应宁怡,“二当家的,您是当真要将兄弟变作墙头草么?我先前已算作背叛弟兄,又叛离乌崖谷,如今还是要再背叛弟兄么?兹是,此等事端皆非紧要,要紧的是我等不比躲在一处等人来营救,却是已在逃亡之路了——指望不得吴有利携属下纵穿乌崖谷大半国土,将我等几个******裹挟出逃?如是这般可称不得营救,那可是明火执仗的赤裸裸的造乌崖谷朝廷的反了!”说到激动处,卞朗低垂的脑袋缓缓抬升,言语于宁怡已有冒犯的意味。
“天要灭我十三玉么?”原本一直无语的陈吉终于也发出了声响。
“阿四,你若是仍不做声,某家就忘却了你也跟来了,”戒灯醍醐灌顶,盯着陈吉道,“阿四,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纵然十三玉没能一把屎一把尿将你养大,但事到如今,弟兄们仅能凭借阿四你的江湖关系,才能脱身了。”
此刻陈吉面目生出了些喜色,“我早已不再挂念以往弟兄们就财富之事生出的那些争执了,再者说来,弟兄们哪个需我相帮,一句话,那弟兄之事便是阿四的事了,此等事弟兄们也都是看在眼中的。于公,阿四也一向尽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如今若是需我去寻个弟兄们的出路,却要弟兄们暂且忘却廉耻了。”
“你那掮客、皮条客的秉性就要暴露了么?”了然闻听陈吉所言,见有了生机,竟起了兴致去调侃陈吉的职业来,“然话说眼下如此境界,还当真不是顾及礼义廉耻的光景了。若要追求真义我等此刻只得调转方向,一路重回冷山。阿四,你是要弟兄去至在那青楼卖艺、卖身,还是要我等夺一座山头、落草为寇?”
“青楼自是去不得的,且不论花姐、笑笑她二人卖艺不卖身,一旦某日开罪了哪个相中了她俩、想要替她俩赎身的大人物,我等岂不是要暴露身份,落得个脏了屁股没人擦的天地?更兼出入青楼之人中颇有各个邦国的军政要员,一不留神将我等当中哪个假扮****的给辨认出来,招惹出个自投罗网的祸事,自是大大的不方便了。——当下只可在这西南地方寻一处与我相熟又与乌崖谷及冷山朝廷不甚僵持的山头落脚了。”陈吉手指一处可能要去的方向,不料臀部狠狠挨上了花上鼓与胡笑踢来的飞腿,一边龇牙躲闪,一边对众人述说,情景顿就轻松了许多。
“可有明了之所在?”秦难询问陈吉。
陈吉上前道,“大当家的,您如此一问可有打击属下积极性之嫌。然,这西南地方确有这么一处所在,不论乌崖谷还是冷山朝廷皆是默许其占山为王又不曾在其中安插探子、细作,我等弟兄大可在那厢落脚。”
“果不出宁某所料,阿四定是不会视弟兄们陷于生死而不顾的。”宁怡面生笑意。
“我等皆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那乌崖谷的众厮妄图以我等果腹——纵是十三玉众弟兄今日之后再难相聚,阿四如之何也只可与众家弟兄做得陌路人,从了那食人骨肉的朝廷,与弟兄们做了敌仇,阿四是拉不下面皮。”陈吉说得声情真切,“只是如若我等此次躲得过一时的险境,日后的性命安危阿四却再无能为力了。”
“是方才说起阿四你肯为弟兄们两肋插刀,却不料,还不等夸赞之言讲得完毕,你就说出些翻脸不认人的话来。阿四你真个以为十三玉已狼狈到如过街老鼠了么?”卞朗拖在众人的最后,忿忿抱怨着。还好,卞朗那埋怨的言语说得很轻,走在前头的人听不到这话的自是听不到,听到却又听不真切的,也假装没有听到。
纵览天下,冷山的天气比起旁的邦国来,可称得上是极其温暖的所在。
即便住在冷山最北端的寺庙里的了然和尚,在这座庙宇之中做了十余年的祷告僧也无有几次机缘瞧到飘雪。想起这名不副实的国度之事时,了然常常感慨不已。
于是,在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雪来临时,了然与秦难围着一壶翻滚着的香茗,坐了一天。
叽喳叫着在神龛上取食的麻雀,扑腾着翅膀离开的时候,庙宇的矮墙外响起的笃笃的踏雪而至的声响让安静的空气不再那么僵硬,了然不解,“这是哪个贼客,明明有一身的轻功还要如此这般地漏出破绽?”
秦难不以为然,瞄了眼茶具中袅袅升起的香气,看着了然正欲起身的举动,微笑道,“了然师傅,来的这人可不是于我等不利之人,不必着慌。”
一阵悉悉索索、略显生疏地开门声后,了然看清楚了这不速之客的模样——但见来人身披乌蓬蓑衣,内着如雪白衫,下身一套青灰紧身长裤;一张小白脸、满头乌金丝。
“了然师傅,这位兄弟便是宁怡了。”不等来人向秦难行礼,秦难便将来人介绍与了然知。
“我当是谁,普天之下哪儿有如此这般之笨的贼客,放着浑身的本事不使,却倒有这踏雪寻梅的兴致?——原来是个穷酸的文人骚客、小白脸子!难不成你是要投笔从戎、弃明投暗么?”纵是了然言语如是刻薄,却仍是礼节性地给宁怡斟满茶,由身后拎出一把蒲团椅来给宁怡坐。
“宁怡见过了然大师,”宁怡接过了然递来的椅子,恭恭敬敬地摆了个端端正正,回身将已掸去浮雪的蓑衣搭挂起来,又对秦难行了礼。
“你耐得住粗俗么?”庙宇大殿内堂传出稳重脚步声与这句声音洪亮的问话。
透过搭在大殿与内堂之间隔断的竹帘,映入宁怡眼帘的依然是一位一袭僧衣的大光头。
“想必这位师父就是戒灯大师了吧?宁怡这厢有礼了。”内堂里的大和尚身形还未完全显现在宁怡眼前,宁怡便向着他深施一礼。
“不敢不敢,”戒灯忙上前,慌慌张迎礼、还礼,抬眼打量宁怡,却只匆匆一眼便辨识出宁怡来,“原来是宁剑客,是方才某家言语若有冲撞,还望宁少侠多多见谅。”
此时的白面书生宁怡于江湖上之名望渺小到忽略不计,戒灯和尚就这么一打眼的功夫儿就能将其认出,了然自觉是戒灯听到了方才三人交谈。却又转念一想,据多年来与戒灯的交往、相处推断,戒灯和尚这个同道中人:一来不善与人自来熟,二来又不乐于奉承他人。不由得了然就想到了——莫不是秦难与戒灯早与宁怡有过相交,偏又将他蒙在鼓中。念及此处,心中不免就对秦难、戒灯二人生出了些不满,面上的颜色也生出了些许变化,兹是秦难等三人忙于相互的应酬而未细细察觉了然。
恰在了然如是想的档口儿,戒灯与宁怡走至在了近前。
先是戒灯察觉到了然一脸的不快,笑言道,“了然师傅,这宁怡宁剑客可不是于我等相害的仇敌,他乃是邵醒邵大剑的嫡传弟子。——可惜的是,邵大剑选了个正儿八经的书生做了这一脉单传的徒弟,怕是要从宁剑侠一代就断了这威震江湖的钝剑术的技艺传承了。”
随后,戒灯便将与宁怡的相识与了然和秦难讲了。
彼时之邵大剑邵醒和今时之江湖客秦难一般,于江湖之上是个只可闻名不可现形的传奇人物。而戒灯起初也仅是听那些四处游走的江湖客风传过邵醒这个大剑客的江湖事迹——月黑风高夜,邵大剑手持一柄木剑行侠仗义、劫富济贫。
兹是彼时之剑客不比旁的那些日后在普天之下风生水起的江湖客,彼时之剑客并未受得朝廷认可,故而为了避免于充斥正能量的江湖中招惹出麻烦来,抑或说邵醒本着对犯错误的年轻人以教育为主、打击为辅的理念,心有令上天感激的好生之德,在邵剑客的工作表上是没有杀人清单这一项的——点到为止,对那些被教训之人,邵大剑总是叮咛,知错能改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