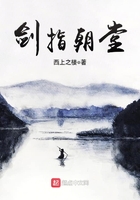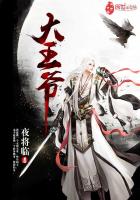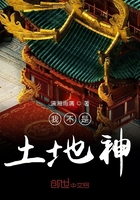明代,在西安知县姜仲能、常山知县刘利用、龙游知县王瓒、衢州知府唐瑜等人和各地学官的共同努力下,衢州地区的儒学继续向前发展。明中期以后,阳明心学在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浙西南地区则成为传播王学的重要阵地。当然,这是与李遂等地方官员的极力倡导密不可分的。李遂于嘉靖年间(1522—1566)任衢州太守。他不仅注重以德化民,政绩卓然,而且对衢州地区的儒学发展和文明进步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李遂学养渊深,于儒学“解悟贯彻”,“朔望谒先师庙,进诸生,讲解经义出其自得,学者辄闻所未闻”。在衢期间,李遂兴建了衢麓讲舍,积极倡导王学。据《王阳明年谱》记载:嘉靖十三年(1534)三月,“门人李遂建讲舍于衢麓,祀先生”。衢麓讲舍在当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明年(按:1529)师丧,还玉山,惠偕同门王修、徐霈、林文等迎榇于草萍驿,凭棺而哭者数百人。至西安,诸生追师遗教,莫知所寄。洪、畿乃与玑、应典等定每岁会期。是年(按:1534)遂为知府,从诸生请,筑室于衢之麓。设师位,岁修祀事。诸生柴惟道、徐天民、王之弼、徐惟缉、王之京、王念伟等,又分为龙游、水南会,徐用检、唐汝礼、赵时崇、赵志皋等为兰西会,与天真远近相应,往来讲会不辍,衢麓为之先也”。从中可见,一方面浙西南地区对王学十分推崇,学者之间的讲会活动十分频繁;一方面衢麓讲舍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但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此文中关于讲舍的建立时间与其他文献记载有所出入。据康熙《衢州府志》,李遂于“嘉靖五年(1526)第进士,十七年(1538)迁衢州府知府”,更有说服力的是李遂在自己撰写的《明嘉靖李遂周孝子祠记》中也说:“岁戊戌(1538),余既获守是邦,奉天子明命,崇正黜邪。”可见,李遂到衢赴任的时间是嘉靖十七年(1538),那么衢麓讲舍的建立时间最早也应该是1538年。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衢麓讲舍及其历史影响的评述。
李遂和其他阳明弟子在衢州的一系列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儒学在衢州地区的发展,“李公盖讲姚江之学者也,抱知行合一之旨,为多士式维。时乡先达王在庵提唱于前,叶敬君、方孟旋相应于后,由是士风一变,翕然崇实而黜浮,号称邹鲁,迄今三百年于兹矣”,此中的“士风一变”和“号称邹鲁”足见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
李遂不仅重教育,而且重教化,注重发挥环境的教化功能,“表德树风,兴学造士…立西安周孝子祠,常山四贤祠,修其墓,录其后”。衢州有周宣灵王庙(又称周孝子祠,俗称孝子庙),由衍圣公孔文远捐地、塑像、立庙以奉祭南宋时孝子周雄,此后历代都有祠祀。李遂在衢期间,“奉天子明命,崇正黜邪,遍诸宇尽撤之,期弗贷。方议及孝子所,群庶民充庭”。李遂在了解“孝子所”的来历之后,不但认为不能毁祠,而且亲自撰写了《周孝子祠记》,其中曰:“若等能以孝子之心为心,日励其所未至,俾若子若孙亦永永孝子之,则祠之之门也,尤在所宜祀。”对周孝子的赞赏及其对后人的劝勉溢于言辞。李遂对周孝子的表彰以及立“常山四贤祠”等举动,对促进当地教化和文明的产生积极作用也无需多言。
此外,明中期以后衢州地区的其他官员也积极提倡儒学。如推官刘起宗,对当时的府学训导刘洙润十分器重,“(刘洙润)讲明理学,推官刘起宗雅重之,请主衢麓讲舍”。同知杨日赞,“游薛中离之门,学以致良知为宗……谦虚下士,公余多暇,讲学不倦”。再如西安知县梁问孟,时人赞誉他“爱士如师傅之教生徒,抚民如父兄之育子弟”。不仅衢州如此,金华、处州等浙西南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正是由于历任地方官员的大力提倡与实践,王学在浙西南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清代,浙西南地方官员继承了兴学课士的优良传统。清朝初年“兵燹之后,弦诵寂寥”,顺治七年(1650)成晋徵知西安县后,以不懈的努力恢复发展教育,“下车课艺论文,朝夕不倦,一时秀杰,彬彬奋兴,多士德之”。西安知县伍桂生不仅振兴鹿鸣书院,而且因九华山僧人触犯戒律而将九华寺院改为书院,命名毓秀书院,使更多的士人深受其惠。光绪十九年(1893)林启出任衢州知府后,加大书院的建设和管理力度,“恂恂儒雅,温厚和平,请拨厘金增加书院膏火,讲求经学,添购书籍,以重脩聘山长,课士子”。此外,处州府推官张元枢“尤加意学校”,遂昌知县赵如瑾“尤隆礼学校,多士蒸蒸向风”。浙西南一带自古就有好学之风,贤才辈出,著述鸿巨,影响深远。清代著名学者朱彝尊对衢州名贤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列举了郑灼、刘牧、徐庸、柴翼之、徐晋卿、王宏等人的成就。南北朝时期的郑灼“励志儒学”,“尤明三《礼》”。宋代人刘牧著有《易解》《易象钩隐图》,王安石为之撰写墓志铭。徐庸,宋太常寺少卿,直集贤院,著有《周易意学蕴》。徐晋卿为皇祐元年(1049)进士,著有《春秋左传类对赋》。宋御史中丞****之后王宏,“博极群书,深解旨趣,诗赋词章泉涌,著有《易启疑》《春秋辨证》,能发先贤俟后学自悟之蕴,纵老师宿儒不克加疵其间。是盖先生天分既高,学力又至,故其醇正如此”。
南宋以来,浙西南历代地方官员对教育的重视,更推动了该地区的向学之风,地方士人孜孜于学,因而涌现了诸多饱学之士。吕祖谦、陈亮等婺州儒学代表人物及其成就毋庸赘言,衢州、处州等地都可谓人文荟萃,涌现了徐存、柴禹声、邹补之、江介、鲁贞、王玑、周积、方应祥、王光祖、王道深、詹介、樊万、王文焕、卢玑等一大批笃学明理之士,他们学识渊博,砥砺志节,其士风为人所称道。清代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齐召南所称的“衢人材辈出”、兵部侍郎帅承瀛对衢州士风民俗所作的“有邹鲁之风”等盛赞之言,对浙西南地区的文明传承作了完美注脚。
当然,浙西南地区儒学的发展是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地方官员的大力倡导之外,以下两个因素不容忽视:一是在浙西南一带任职的教谕、训导以及讲学大儒,博览典籍,学养深厚,其中以朱熹、吕祖谦、柳贯、胡翰、王阳明弟子等最为著称,他们的言传身教为当地士人起到了示范作用,从而推动了儒学的发展。二是孔氏南宗积极从事教育活动,南宗士人通过担任学官、山长等途径,推动了浙西南地区的教育发展。
浙西南地区在历史上也存在着溺女、设淫祠等一些陋习恶俗。浙西南地方官员通过积极努力,严禁与引导有机结合,移风易俗,有效地促进了浙西南地区社会风气的好转。溺女之风严重违背了人情人伦,然此风在历史上的浙西南地区较为普遍,地方官员对此予以严禁,效果显著。刘佐在正德十四年(1519)任龙游知县后,“刚毅有为,重禁溺女及使婢之不嫁者,有不奉法辄罪之,俗赖孳息”;李忱于顺治十八年(1661)任西安知县后,采取得力措施整治溺女之风,“凡民间有育女者,令乡里条其姓氏,闻于官,富者加以奖谕,贫者膳以银米,为养育之资,始终十年不懈,生息以蕃”。此外,衢州知府杨廷望、西安知县陈鹏年、伍桂生等都严厉整治地方溺女之风。郭敦(永乐初知衢州府)、潘选(正德二年知江山)、林有年(明代知衢州)等浙西南地方官员,采取强有力的举措,废除淫祠,其中林有年“改淫祠为社学,选教读令诸生肄业于中”。对于晚明时期浙西南一带的奢侈之风,西安知县贺康载“务崇俭约,食不二味,民间衣服有华诡者,必按治之,风俗一变”,他也因之被人称为“政尚严明,有西汉循吏风”。
综上所述,浙西南地方官吏积极践行以仁德爱民为核心的儒家为政思想,一方面清廉慈惠,与民相亲,重视教育;一方面擒拿寇首,消灭寇盗,荡涤污浊。宽严相济、扬善惩恶,为浙西南民众营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民风民俗得以改善,从而推动了浙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素有“难治”之称的浙西南风俗得到改观淳化。蒋光彦任江山知县期间,认识到“江民朴直,激之则悍”,因此“驯而抚之,民用归心,粮无逋,讼无终,行者让路,耕者让畔,风俗为之大变”。李遂在衢州期间对改善当地的民风民俗、促进文明教化也具有积极作用,人们称之为“政尚德化,民俗还淳”。我们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南宋以来,浙西南地区在当地官员的政治活动、孔氏南宗族人的政治和教育活动等多种力量的作用之下,儒风大振,士风民俗和社会秩序不断得以改善,文明程度不断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