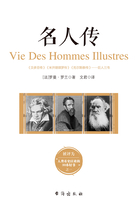所有的作者都把阿姆斯洛描写成一位极其精明的商人,对人性有着透彻的了解。他对于接触过的人,有着一种准确判断他们性格和动机的直觉。无论他们如何掩饰真实的目的,阿姆斯洛总是能够事先就看穿他们的伪装。他的判断很少出错,而且能够一眼洞察那些夸夸其谈的人的把戏。阿姆斯洛一向唯才是举,一视同仁,诚实有才能的人则总是能得到他的垂青。一个在工作中安静而有效率的人会得到阿姆斯洛一眼注意,并且予以提升。在谈话中阿姆斯洛是一个亲切的人,但是面对别人有求而来的尊敬表示,他也总保有一点矜持。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在他的语录中可以找出很多妙语,尤其在面对非难和难堪的事实时,更是能够巧妙应对。有很多展示他的精明和幽默的轶事流传在世。他懂得语言的艺术。当托瓦尔森(Thorwaldsen)经过德国时,受到了德国各地的热情款待,以示对他的尊重。在一次宴会上,阿姆斯洛被介绍与这位雕塑家结识,阿姆斯洛俏皮地说:“你看起来那么英俊,谢瓦利尔,以至于别人都会认为是你塑造出了你自己。”托瓦尔森后来回忆说自己从未受到过如此巧妙的恭维。
除去自己充满智慧和幽默感之外,阿姆斯洛也很会欣赏别人的幽默,即使有些幽默是针对他的。有一次一个人写信给他,说道:“男爵先生,请寄给我一千基尔德,然后忘了我。”这封信的简洁和直率打动了阿姆斯洛,随后他就给这个人寄去了一千基尔德,并且回复:“我已经寄给了你要的数目,并且如你所愿,忘记了你。”
当1832年阿姆斯洛去艾姆斯(Ems)河消暑,他选中了在罗姆伯格(Romerberg)的一所私人住宅下榻。而另一位充满活力的普鲁士男爵也住在这所房子里,他和阿姆斯洛一见如故。一天晚上,他们俩一起朝着著名的四塔(Four Towers)方向散步,在一场机智的谈话中,阿姆斯洛忽然停顿下来。在这一刻,一位衣衫不整的男人悄悄靠近他并且打开了他的口袋。阿姆斯洛身边的男爵先生发觉了这一切,很自然地推断这个男人的目标是偷窃钱物,不过出乎他意料的事,这个男人只是把一封信塞进了阿姆斯洛口袋里,然后就悄悄离开了。阿姆斯洛继续他的散步,毫不受刚才的事影响。直到他把手伸进口袋里,发觉了原因,然后立即说道:“啊,我明白了。”很显然这一碰触解释了刚才那个奇怪的事件。他们沿着科布伦次(Coblentz)大街继续散步,到了黄昏,他们俩决定原路返回。忽然从树后闪出一位衣衫褴褛的人挡在阿姆斯洛的路上,阿姆斯洛的同伴立即做好了搏斗的准备,不过他发现那位不速之客手上没有手枪和刀剑之类的武器,只是握着一封乞讨的信件。阿姆斯洛也没有露出惊讶和警惕的神色,很显然他也早已习惯于这种独出心裁的传递信件方式。
一个温暖的夏日,当阿姆斯洛与他的几位朋友共进午餐时,正对着他的座位的一扇窗户忽然打开了。从窗缝间,一封信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了阿姆斯洛的盘子里。客人们都大惊失色,但阿姆斯洛平静地从口袋里取出一片金子放在尚未启封的那封信上。然后他敏捷地把这封信原路奉还回去。这样新奇的行善方式很为宾客们欣赏。然而阿姆斯洛并不满意,他在没有弄明白来信的缘由和内容之后是不会罢休的。他向客人们致歉,请求离开一会。随后他走向那扇打开的窗户,明白其中奥妙之后走了回来,脸上带着满意和快乐的表情,轻声说道:“明白了。”这位富有的金融家对于这样的玩笑保有如此的兴趣,是件非常有趣的轶事。
阿姆斯洛对于自己的言行举止一向讲究和自豪,举手投足之间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仪,然而又不带丝毫的傲慢。他总是平静地叙述自己企业的开端和竞争,他步行去办公室,在犹太人街道的那幢老房子他度过的那些星期五的夜晚,在那里他享受他的白面包和烤坚果。阿姆斯洛提到那些暴发户的妄想和傲慢时总是带着居高临下的轻蔑态度。他从不和政治搅在一起,总是节制谨慎地和不同的政府打交道,虽然他对奥地利的偏爱也是显而易见的。阿姆斯洛投放了很多钱在慈善事业上。每年他都分发很多钱给那些贫苦的人们,很多请愿没有得到回应的人们都得到了温暖的资助。他的善行现在都已经无法估量。不过从成千上万提交给他的请求救济的申请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善行覆盖面很广。阿姆斯洛死后,穷人们失去了他们最慷慨,同时又是最朴素的恩人。
阿姆斯洛在一个辛苦劳作的家庭长大,他的年轻时代在不停的劳作中度过,因此很自然他没有受到很好的古典教育熏陶。之后的岁月里,他尽力学习外语和历史,并且努力锻炼身体,不过他清楚自己的缺点所在,如果有人奉承他的马术或者其他什么技艺,他都会觉得不快。法语和英语他都说得一般,实际上,他只对自己的生意感兴趣,也许是一点点空虚让他去接触学习那些外语,自然他的外语水平不会超过他的母语——德语。在女士面前,阿姆斯洛总是表现得举止动人有风度,并且活泼而勇敢,这些品质他一直保持到去世之时。他对艺术的钟爱主要体现在他对于古钱币和旧金属制品的品味上,关于绘画,他也有一些精妙的评论。除去这些爱好,他还喜爱自己的花园,在他的那些美丽的花丛间徘徊永远不会使他疲倦。
阿姆斯洛作为居住在法兰克福犹太人街区中的一员,地位与其他犹太人并没有太多不同。他的财富和影响力并不能赋予他基督教信徒的文化和政治权利。在很短的时间里,普利梅特王子(Prince Primate)于1812年授予犹太人和基督教邻居们平等的地位,不过到了1815年,犹太人们又被剥夺了这些权利,直到1853年,才又回到了他们手里。在这个时期,家族的创始人老梅耶是竞选联盟的成员,他的儿子,像法兰克福最贫穷的犹太人一样,被剥夺了任何管理城市事务的权利,因为他们不具有城市自由民的身份。尽管阿姆斯洛是虔诚的塔木德派犹太教教徒(Talmudic Judaism),但是他也一向主张宗教自由和宽容,他曾经出资资助过和他信仰的教义完全相反的犹太教派选举。在他死后留下了大约五千万到六千万基尔德的财产给他的一位侄子。给犹太社团留下了一百二十万基尔德,以及很可观的一笔财富给那些需要帮助的穷人们,他把这些在街上偶遇的人们亲昵地称为他的“信使们”。阿姆斯洛立下了严格的遗嘱维护和保存犹太街区的老企业。有些死板的犹太家族就一直反对他对犹太教义和仪式的革新,阿姆斯洛在安息日遵守教义上的戒律,但是在斋日赚钱做生意也不会有丝毫的犹豫。有一次阿姆斯洛在亚琛,大约十六万泰勒的一笔款子要他星期六去接受。他准时出现在收款的地点。当他被别人问起这件事时,他尖锐地回答:“不是每一天都适合接受十六万泰勒的。”随后他仔细地点清了款子并装进了口袋里。
法兰克福银行的生意范围非常广,不仅接待大部分德意志的邦国和公国,而且还包括一些特别的客户——各级贵族们,特别是南德(South Germany)的一些贵族,他们囊中羞涩,不得不向金融世家求助。法兰克福总行的欧洲客户远远超过了伦敦、巴黎和维也纳的分部。为了显示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德国的公侯们是多么慷慨,以及那些客户们是多么让罗斯柴尔德家族有利可图的人们,我们列出了一张大概的表,每个名字之后是他们借贷的总数:
伊森伯格·博斯特恩 1100000
罗文斯特恩·沃斯姆 1250000
撒因·维特根斯坦·贝勒伯格 300000
瓦尔登伯格·泽勒 172000
加尔夫·桑德·冯·斯泽拉瓦尼奇扎 670000
瑞特·冯·里瑟 250000
伊森伯格·瓦奇特巴赫 294000
索姆斯·里奇 300000
罗文斯特恩·罗森博格 350000
维克托·伊森伯格 王子 140000
维克扎伊 伯爵 700000
斯扎巴里 伯爵 300000
内林根·韦斯特伯格 伯爵 80000
冯·尼基 伯爵 340000
冯·胡雅迪 伯爵 500000
冯·斯泽彻伊 伯爵 1800000
亨克尔·冯·多内斯马克 伯爵 1125000
冯·弗洛伯格 伯爵 100000
冯·格兰泽·埃斯特哈泽 王子 6400000
弗雷海尔·冯·格雷芬克劳 王子 130000
斯科瓦岑伯格 王子 5000000
瓦尔德伯格·沃尔费格 王子 800000
瓦尔登斯 王子 350000
冯·瓦特姆伯格 伯爵 2070000
总 数 16021000基尔德
这个清单还很不完整,即使如此,它还是展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生意中庞大的私人客户群。
作为总结,我们可以评价一下阿姆斯洛统治下的法兰克福交易所,以及在这之下服从他意志的庞大的从属机构。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兴起之前,法兰克福与德国的其他贸易型城市相比并无优势,法兰克福本身商业发达,又与国际贸易接轨,不过它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仍然不足以让它成为欧洲金融的焦点。然而这个情况现在改变了,法兰克福倚仗罗斯柴尔德家族庞大的金融网络使自己成为领先欧洲其他城市的贸易流通中心。巴黎、法兰克福、维也纳和伦敦,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那里分别建立的企业,联合成了一个金融帝国,任何大型的金融活动都必须经过他们。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兰克福的总部对于金融活动的控制和操控作用,比其他各地的分部更加显著。其他银行和金融机构对于法兰克福总部一家独大的局面颇有微辞,他们认为阿姆斯洛可以随意操控价格来打压他的竞争对手。公共报刊上也充斥着对于金融大企业操纵经济市场的非难之辞。这些论调总是乏善可陈,千篇一律。例如这则评论:“流通的金钱越来越匮乏,以后情况会更加恶化,这不正说明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完全掌控了局势,把市场握在股掌之中了吗?”这些舆论压力对于一些小家族来说可能会起到伤害作用,不过生意和投机活动仍然是自由不受阻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具有在生意场上随心所欲、呼风唤雨的力量,不必请求任何人的批准。这种自由行动的权利实际上属于全体人们。证券交易中的意图代表着权利,如果实力较弱的投机者愿意在反对的那一方下重注,无论那些“重注”实际上是多么微不足道,这都代表了他们想成为一家大企业的管理者的企图,但是事后他们也许会后悔自己的愚蠢给自己带来了损失。发放国外贷款成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特权,他们时刻警惕着对手会踏足这块领域,分走一杯羹。有一次,一家企业鲁莽地没有经过罗斯柴尔德家族单独接下了一宗比利时的贷款业务,立刻就为自己的鲁莽感到后悔,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会用自己强大的力量挤垮任何竞争对手,所以这家企业立即向罗斯柴尔德家族俯首称臣,表示了歉意。不过在另一个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很多家族身陷财政危机之时,都是有赖财雄势大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施以援手。我们倒不是想让别人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总是善心大发,实际上,无论他们身处怎样的不利状态,他们也总是有方法扭转局面。比如在1832年,巴黎的一家著名的银行收到了来自北美一家无名银行开出的支票,因为那家银行当时没什么名气,所以也没人敢于确认这张支票的信用。这个问题困扰了巴黎银行很久。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收到很多可疑的汇票。他该怎么办呢?他自愿存放了四千万泰勒在一家银行,公众见到阿姆斯洛男爵对金融业如此有信心,推测以他的神通,一定是得到了什么好消息。如此一来,那些谣言也就烟消云散了。巴黎的企业也因此得救,同时阿姆斯洛也在这次交易中获益匪浅,因为他的这笔资金是用从他刚刚买入的无名小银行发行的支票汇出的。
一位德国记者写道:“用这种方式,阿姆斯洛成为了金融界的君主,不是浮夸的修辞,而是真实的情况。他的诸侯是那些别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只要他高兴或者他不再需要它们,只需一抬手指,就可以将它们摧毁。”
阿姆斯洛死后,法兰克福银行由他的侄子们掌管,威廉男爵和C·冯·罗斯柴尔德男爵,他们遵循家族的祖训认真经营企业。多亏了这两兄弟的谨慎和小心,企业的财富稳步增长。卡尔男爵是一位出色的艺术赞助人,拥有一批珍稀的绘画和雕塑收藏品。威廉男爵是一位虔诚的犹太教徒,一生严格按照犹太教的斋戒日期生活。
不久前卡尔男爵去世,他的兄弟开始单独掌管法兰克福企业。卡尔男爵丰富的收藏品也成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