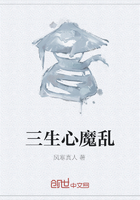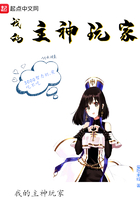这一群人兔死狐悲,聚集在梁乙埋府中,不免要吵吵嚷嚷,聒噪不休。梁乙埋连哄带骂,方将这些人暂时镇住。
打发了这些党羽之后,梁乙埋开始认真考虑起目前的局势来。
自从绥德之败以后,他在西夏国中的威信便日益减弱。以外戚控制国政,在西夏这种实力派林立的国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以前之所以不断出兵攻打宋朝,除了满足自己的野心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转移国内矛盾,缓解国内对梁氏独霸朝政,治国无能的不满。并且通过战争,牢牢把握兵权,使反对派不敢轻举妄动。但绥德一败,西夏国力大损,国内对他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昔日被压制的反对派,声音与胆子也一并增大——若在以前,借给仁多澣一个胆子,他也不敢派兵入兴庆府!这样潜在的力量,散布于兴庆府与各地。乃至于普通的西夏部落首领,在梁氏强大之时,并不敢有他想,但此时对梁乙埋的支持也变得犹疑起来。这些人一向只会追随强者。
如若秉常在当时果断一点,趁兵败时拿他开刀,他梁氏一族,此时有可能已在鬼门关相聚——不过当时秉常也有他的疑惧:梁氏一门两后,朝中党羽密布,而最重要的是,在平夏城作战的梁乙逋还控制着一支精兵。但饶是如此,当时也是梁氏地位最不稳固的时期。因此梁乙埋才会长期称病不朝,害怕的就是出现万一;也因此梁乙埋才不惜代价,要和辽国交好,借此稳住脚跟,并且迅速地再次将兵权牢牢握在手中。梁乙埋深知,他梁氏一门在西夏国中立足的根基,依赖的就是梁太后的威望与对兵权的掌握。
此时梁乙埋基本上已经稳住阵脚。但是他也知道,此时的情势,与兵败绥德之前,依然大不相同。缓德兵败导致梁氏势力的削弱,不是这么轻易就能挽回的。西夏国中,上至各路“诸侯”,下至普通将士,对梁氏衷心拥戴,特别是对他梁乙埋衷心拥戴的,已经非常的少,而不满的却在增加。只不过梁乙埋身兼国舅与国丈两层身份,一门两后的地位,加上经营十数年的积威,掌握兵权的实力,使得梁乙埋在表面上依然还能够维持着自己的地位。
梁乙埋也许算不上一个智者,但是精擅权术的他,对于这些潜在的变化,却非常的敏感。能在西夏残酷的权力斗争中成为胜利者,他依靠的,也并非仅仅是因为他的姐姐是太后。
西夏的局势,本来已经相当的微妙。力量的天平在改变,形成了一种新的非常微妙的平衡。但在这个时候,夏主秉常颁布了“大安改制诏”,这个微妙的局势,注定要被彻底打破。
梁乙埋完全出于一种本能,非常谨慎地应对着即将发生的变化。毕竟现在的西夏,已经不是他可以操控一切的时候了。
夏主秉常的“大安改制诏”,其实迎合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期望。有实力与野心的人希望借此机会掌握权力;而关心时政的贵族酋长们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他们盼望着变化,盼望西夏能中兴,虽然这一点也不妨碍他们想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社会的下层,则希望减税,并变得厌恶战争——哪怕是一个纯游牧民族,战争也不会只带来好处而不带来麻烦的,更何况西夏是一个半农半牧的国家,长期的战争,给社会下层带来的痛苦其实并不逊于他们给敌人造成的痛苦。战争得到的利益往往被上层侵吞掉大部分,而普通民众却要承担赋税加重,生产之主要责任由妇女老幼承担等种种恶果。“大安改制诏”的颁布,至少在精神上,给了这些人一个希望。
梁乙埋虽然并不能准确的把握住国人的想法,但是他却能直觉般地意识到一些东西。更何况有些情况他是明白的:秉常有大义的名份。
这是绝对不可轻视的。
梁乙埋权力的合法权便是因为他依附于这种大义的名份之上。一旦他失去这种名份,国内立时就会大乱。既便他并非通晓史事的人,也知道宋太祖的故事,以宋太祖在军中、国中的威望,一旦黄袍加身代周,也会面临着叛乱。他梁乙埋威望、才望、实力三者无一样比得上宋太祖,别说禅代,哪怕擅行废立,也一定意味着内战的开始。更何况还有一个宋朝在虎视眈眈。
因此不到万不得已,梁乙埋也不敢轻举妄动。
如果真要下手,就要有万全的把握控制住局面,至少也要能够控制住秉常。否则,远的不用说,耶律乙辛就是前车之鉴。辽主不过是太子,耶律乙辛还可以另立新君;但是秉常却是西夏国王,先帝谅诈唯一的儿子!如果不能控制住秉常,他梁乙埋的前途便已注定——他的势力会很快瓦解,梁氏一族在西夏算是彻底玩完。梁氏权力基础是依附于西夏王权的,他梁乙埋不会做自掘坟墓之事。
“投鼠忌器!投鼠忌器!”梁乙埋不断地自言自语着。理清思绪之后,他才惊觉,局势之复杂微妙,更出他预料。自己果真能控制住兴庆府吗?在某一瞬间,梁乙埋甚至有点怀疑,若是秉常亲自率军,究竟有多少原来他算在自己力量之内的部队,在那时候会动摇、观望,甚至是反戈。但是秉常有这种胆识么?梁乙埋一时间竟也拿不定主意了,若从之前来看,他绝无这种胆略;但若从他在大殿诛杀异己来看,却又似乎不无可能……
“终须先翦其羽翼!”沉吟良久,梁乙埋终于咬着牙,一拳砸在了桌案上。
“来人!”恢复平静之后,梁乙埋整了整衣服,高声喝道……
数日之后。
西夏王宫。
夏主秉常正与李清、禹藏花麻、文焕以及几个大臣商议着改制之事。在众人当中,李清表面上看来最平静,但是内心却最为激动。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有时候会执着于一些形式上的东西,并且为之感动。睿智如李清,亦不免于此,身着汉袍的李清,竟时时有一种回归故国的错觉。许多年被人有形无形的歧视,在穿上汉袍的这一刻,似乎全部得到补偿。因此,在议事之时,李清竟然几度失神。
如是几次之后,在李清再度走神之时,秉常终于发觉了李清的异样。
“李将军?”
李清几乎被吓了一跳,回过神来,忙应道:“臣在。”
“卿无碍吧?”秉常狐疑地望了他一眼。“莫非府中有何事?”
李清见连文焕与禹藏花麻等人都不禁侧目而视,不由大觉尴尬,忙找了借口,回道:“谢陛下关心,臣家一切尚好。臣是在思虑一些事情。”
“哦?是何事值得如此?”
“臣在想,改制诏颁布有些时日了,各地统军、头领、节度使、知州的态度,也应当明了了……”
秉常点了点头,却微怒道:“至今未收到一份奏表。”
文焕在一旁插道:“此事不足怪。兴庆府附近,要么是梁国相门下,要么心存观望。待沿边几个军司表示支持的奏折一到,这些人的奏折,自然就递进来了。后至之诛,他们岂能不惧?”
“状元公说得是,我曾听过这‘后至之诛’四字,似是个典故吧?”秉常点头称是,又感兴趣地问道。
“确是典故。说的是大禹大聚诸侯,有最后至者,即斩之,以立威天下。陛下改制,当法先王,立威信以行天下。”文焕郎声说道,全然不顾李清已经微微皱眉。
秉常却连连点头称是,赞道:“大禹为上古圣王,果然值得后世效法。他斩了后至者,从此他若有征召,则诸侯自然无不争先。其能成千秋之业,岂是偶然?!”
文焕笑道:“陛下闻一而知三,真英明之主。”
秉常听到这话,更加高兴,笑道:“今我等改制,亦当效法先王。若能使那些庸庸碌碌的官员知道害怕,则自然令行禁止,改制可成,中兴可期!我日前诛杀野利诸人,正是为此!”
李清在心里叹了口气,正要劝谏,方待开口,却听到一人冷冰冰地厉声说道:“若是我不肯着汉服,皇帝是不是也要给我‘后至之诛’?!”
伴着这声音,内侍尖锐的唱礼声响了起来:“太后驾到——”
众人连忙跪倒迎驾,齐呼:“太后千岁!”
李清偷眼打眼,却见梁太后满脸怒容,正盯着夏主秉常与文焕,似乎恨不得把他们的心都挖出来看看。一个内侍则满脸尴尬的侍立在身后,显然他是被梁太后命令不要通传,结果却被梁太后听到这番议论……李清又将目光移向梁太后,却见梁太后两道锐利的目光向自己射来,他连忙低下头去。
却听秉常站在那里,陪着笑说道:“母后说笑了。”
“我可不会说笑!”梁太后冷笑道,在内侍搬来的椅子上坐了,又说道:“在朝中连诛三个大臣,我还敢说笑么?天下谁不知道皇帝杀伐果断!”
“那三人违抗君命,原也该杀。”秉常不敢看梁太后的眼睛,只是低着头回话。
“果然不愧是一国之君!”梁太后冷笑道:“皇帝长大了,连祖宗都不放在眼里,原也不必把我这个老妇放在眼中。‘原也该杀!’哼!”
“孩儿岂敢。儿子这也是为了祖宗基业。”
“若果真为了祖宗基业,便不当如此草率!”梁太后厉声斥道:“我们本是胡人,穿着这汉人的袍子,便是背祖忘宗!同样的话,我已和皇帝说过很多遍——这汉袍一旦穿上,十年之后,大夏便无可战之兵,党项有灭族之祸!当年北魏孝文帝的教训,你便一点也不记得么?”
“太后此言差矣,孝文帝之时,北魏强盛一时,北魏之乱,是因为他儿子不争气,祸生萧墙而招外侮,否则尔朱荣之流何足成事?这如何能归咎于孝文帝改制?”文焕伏在地上,沉声反驳道。
“你是何人?!敢这般和我说话!”梁太后盯着文焕,骂道:“都是你们这帮奸臣惑君乱国,把好好一个皇帝带坏了。”
“太后……”禹藏花麻小声唤道,想劝解几句。
梁太后却早已开口骂道:“禹藏花麻,你不好好劝皇帝走正路,也要跟着他们胡来么?你可也是胡人。”
禹藏花麻连忙把头缩回去,不敢再说话。
殿中顿时一片沉寂。
梁太后的目光扫过众人,指着文焕,冷冷说道:“这人是宋朝降将,无父无君之徒,岂可倚为腹心?来人!立刻将此人赶出宫中,从此以后,若见此人踏入宫中一步,便取他头来见我!”
“母后!”秉常急道:“文焕确是忠臣,绥德之时,他有救驾之功……”
“正是念他救驾之功,才没有立斩他。”梁太后的话里,有不容置疑的权威,她又将望着秉常,道:“皇帝亲政了,爱做什么,也只能由得你。这江山社稷,是祖宗辛苦打下来了,终不能丧在外人之手。嵬名荣是几朝的元老,忠厚可靠,这御围内六班直,自今日起,划出一半归他直接统领。他本是御围内六班直的老统军,让他指挥,也指挥得动。”
“这……”秉常与殿中众人,听到这话,连脸色都变了。
梁太后环视众人一眼,冷笑道:“难不成还有人离间我们母子,皇帝你疑心我要夺兵权不成?”
“孩儿决无此意,只是兹事体大……”
“御围内六班直,你母后我当年也指挥得动!我若真要夺你兵权,一道手书,便能将六班直全部调走,用不着这么扭扭捏捏。我是信不过你身边这帮人!”梁太后目光逼视秉常,其中竟隐隐有几分嘲讽之意。不过梁太后这话也不算吹嘘,她不比一般女子,带兵打仗,权谋手腕,无一样没做过。以西夏宫廷斗争的血腥,其胜利者又岂会是泛泛之辈?
秉常在梁太后的逼视下,终于无视李清、禹藏花麻等人心急如焚的神情,退缩了,“是,儿臣谨遵母后懿旨。”说出这句话,秉常身子一软,几乎要感觉要瘫了一般。李清等人,脸色尽皆如锅底一般黑沉。
梁太后举手之间,便夺走御围内六班直一半武力的完全控制权,虽说这部分武力本来也不是秉常在任何时候都能指挥得动的,但对于李清诸人来说,始终是一次巨大的挫败。而文焕被梁太后一句话就赶出王宫,更是明白无误的告诉着秉常,究竟谁才是这座王宫真正的主人!但让人奇怪的是,一向坚决反对改制的梁太后,这次却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反而表现出了一点态度软化的迹象。不过,这一点,对于被挫折感笼罩的秉常等人来说,却没有注意到。
踌躇满志的秉常,甚至还没有开始真正改制,就遭遇了第一次挫折。在这个时候,兴庆府的严冬,似乎都成了一种不祥之兆。
不过,这种沮丧看起来只是暂时的。
很快,仁多澣就给秉常打了一剂强心针。在“大安改制诏”颁布一个月内,以仁多澣为首,四五个实力派的军司统军,以及部落首领,陆续将自己支持改制的奏折送到了兴庆府。有了做第一个的人,许多人对梁乙埋的顾忌就少了许多,后面陆陆续续,各军司的统军们,全部送来了支持的奏折。
终于,在大安四年快要过去之前,西夏的各路“诸侯”们,也许是出于真心的支持,也许是出于政治上的投机,也许是出于恐惧“后至之诛”,担心野利拿等人的命运在自己身上重演,总之,是一个不落的表达了他们对改制的支持。
大安改制,在名义上,终于成为了“顺天下之望”!
时间永远是最大的。宋朝的熙宁十一年,夏国的大安四年,很快就过去了。宋夏之间的战争,眼看着就过去了一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对于善忘的人来说,已经可以忘记他们不想记住的事情;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耻辱却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减。
熙宁十二年的正月,宋朝与西夏,从表面上来看,除了西夏派出使者向宋朝皇帝拜贺正旦以外,双方都是在为各自的事情毫不相干地忙碌着。
宋朝在正旦的大典之后,由鸿胪寺卿正式告知辽使,宋朝决定接受了辽国的请求,双方在对方京城,互设常驻使节,辽国由此成为自高丽国以外获准在汴京常驻使节的第二个国家。这件小小的事情,实际上传达了很多的信息:此时的宋朝,正在渐渐变得比以往更加自信,也更加开放。
不过,此事由鸿胪寺卿来传达,却也意味着对石越主导的官制改革的修订——当年官制改革之时,规定鸿胪寺负责藩属、国内少数民族、海外殖民地之事务,而不在朝贡体系之内的国家,如对辽国的外交事务,则归于礼部。这种设置本是石越试图打破朝贡外交的一种尝试,今后的宋朝必将面临更宽广的世界,虽然宋朝当之无愧地处于当时人类文明的顶峰,但是并不意味着其余的文明只能葡伏于它的脚下,古老的朝贡体系在石越看来,本就有修正之必要——正视你的竞争对手,什么时候都不会错。而宋朝本来就视辽国为平等的“大国”,朝贡体系在这里已经开了一道缝,因此石越便想巧妙的加以利用。但很快,宋廷就发现了其中的不便:当时与宋朝交往的国家,仅仅只有辽国是宋朝认为可以平等相处的国家,其余诸国,连注辇国这样的天竺强国,都被习惯性的纳入了朝贡体系之内,虽然对海外更加了解的宋廷心知肚明那并非大宋的藩属,但传统思维却没那么容易改变。至于对世界的了解日益增深之下,被宋朝许多士大夫承认可以与辽国相提并论的近西及泰西诸国(石越《地理初步》之地理概念,大抵西夏以西至中亚,称为西域,西亚至东罗马帝国称为近西,东罗马帝国以西,则为泰西),却并未与宋廷发生直接的官方交往,因此自然也被选择性的忽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礼部主客司就显得特别的清闲,也特别的刺眼,朝野上下几乎一致同意这是一个“冗司”,终于,这个机构在熙宁十二年走到了它的尽头,宋廷首先决定将其事务全部并入鸿胪寺,在一个月后,就正式宣布裁撤主客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