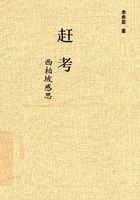我在不断的梦想中生活。
——苏沃洛夫
出发的前两天,我终于有空穿着亚运会发的大红运动衣风风火火跑到北大25楼博士生宿舍,向我的女孩描绘我的军事思想。她低眉顺眼听我白唬了半天,才说:“你怎么总在做梦?”的确,我一直如俄国元帅苏沃洛夫所云:“我在不断的梦想中生活。”
12月20日,1990年。北京,国际机场。
没有比此时飞往巴格达更迷人的了。
我真不懂妈妈干吗抱着我大哭。也许战争中女人比男人失去的更多,我们仅失去生命和肢体,女人则失去灵魂和心。对于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我深知,除非你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否则就别去冒险。
海明威《永别了,武器》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都准备献出我们的生命,但只有少数人中选,对这些少数被选中献出生命的人,也无须给予殊荣,因为他们是幸运儿。为祖国献身的人的母亲是世界上最值得骄傲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我心中的不怕死有两重含义:一是明知有危险而不怕;二是不受金钱、权力等物欲驱使。我的冒险就属于这一种,心自由,嘴也自由,行动起来才有活力。
临行前,我把我的财产——从《简氏武器年鉴》到各种军装,分送4位同事的儿子们。像去可可西里探险时一样,摄影部副主任林川和梁师傅拉着哥们儿一直送到机场,外事局小金用力捏了捏我的右手,“鸭子,一定回来,3个月后我在这儿等你。”
由于国际封锁,目前进入巴格达的唯一通道只有约旦,我得先乘中国民航飞到伊斯坦布尔,至于以后的路,只有天知道。8点10分起飞,中国民航CA-943航班蔡机长双手紧抓我的双肩,“小伙子,有什么要求直说,趁还在祖国的飞机上。”他见我一人带了这么多行李,特地给民航伊斯坦布尔孔站长写信:“老同学,设法帮助这位记者,他要去巴格达……”乌鲁木齐边防武警免收我的出境费,并送我一张入境费交讫的凭单,“希望你还从我这儿入境,入境费我先替你交了。”
19点20分途经沙迦,降落前可以看见霍尔木兹海峡外点点油轮游弋于印度洋上。
临近烟波浩渺、战云浮动的波斯湾,一股慷慨别燕蓟的孤独感油然而生。海水中总是浮现我老妈随风飘舞的花白头发,出发前一天晚上,她一直背对着我拼命地洗我换下的一大堆脏衣服。
连续飞行了17个小时后,我在伊斯坦布尔着陆。雨夜朦胧,分社的一位同志早已等候在机场,民航伊斯坦布尔办事处帮我寄存了放大机、传真机和装有钢盔、防弹背心的两只大箱子。
土耳其,这个地跨欧亚的文明古国,悠久的历史可溯源到公元前700年,曾历经东罗马、拜占庭及奥斯曼等盛极一时的帝国,随着军事采邑制的衰落而沦为英、法、德、俄、奥诸国的纷争之地。
这次我匆匆逗留并在那儿转机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就曾是东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首都。这座原名君士坦丁堡的古城,其城市布局与我国的长江重镇武汉有点相似,分隔欧亚两大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将其分为三个部分,呈鼎足之势。博斯普鲁斯海峡北通黑海,南达爱琴海和地中海,地势相当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根据1923年的《洛桑条约》和1936年的《蒙特勒公约》,博斯普鲁斯海峡归土耳其管辖,但外国包括黑海沿岸国家如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商船,均可自由出入。一旦此海峡被封锁,黑海顿成“死海”,它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这里比北京时间晚6小时,早晨起床对表,乌黑的煤烟袅袅而来,空气中弥漫着穆斯林的祈祷声。想不到这座土耳其的重要港口城市居然还缺水,所有人家全用容器贮存水,浴池中也是水,饮用水得去买。在伊斯坦布尔大桥旁,停泊着一条30万吨级的伊斯坦布尔自来水公司的大船,它是专门用来运水的油船。
几只棕头鸥在小楼上盘旋、降落,小雨犹未绝。大喇叭传来祷告声,庄严神圣。
土耳其是个穆斯林国家,伊斯坦布尔这个土耳其最大的城市里的清真寺更是数不胜数。我有幸走进了著名的古迹——“蓝色清真寺”和与其隔街口对峙的“圣索菲亚教堂”。建于17世纪的蓝色清真寺高43米,全寺共有260个窗门,屋顶呈圆拱形,名实一致,寺内主要色调是蓝色,它是世界上唯一建有6座宣礼塔的清真寺。与它遥遥相对的是被誉为“世界七大建筑奇迹”之一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这座代表东罗马帝国建筑艺术高峰的教堂,外观宏伟,内部装饰精致富丽,为伊斯坦布尔最大的教堂。我对伊斯兰清真寺与基督教教堂在一个广场上和睦相对大为赞叹。
托普卡珀宫则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留下的建筑,距今约有500多年历史。据说,宫内有很多房间,可住4000人以上。与北京故宫一样,托普卡珀宫也设有“珍宝馆”,陈列历代皇帝收藏的古玩珍器。在那里,我惊喜地发现还有中国明清两朝送给历代苏丹王的瓷器。
次日,我乘约旦航空公司波音-727飞往安曼。安曼机场的警察将我的6包行李全部打开,直弄得防化服上的滑石粉白烟乱冒才甩手而去。
如果人生的乐趣在于这一秒钟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我的巴格达之行则饱尝这种提心吊胆的乐趣。在安曼小住一日,我登上了飞往巴格达的伊拉克班机,遇到的安检更加严厉。尽管我已把防化服和传真机都扔在了安曼分社,可我托运的行李还有48公斤重,按规定伊航只许托运20公斤。看到我前面的日本NHK记者大把地从西装上衣口袋中挥洒出成叠的绿票子缴超重托运费,我却分文没有。我耐着性子娓娓动听地给工作人员解释为什么我现在没钱,其窘态不亚于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他同情地将48公斤改成了30公斤,在收了我一把清凉油之后,又改成20公斤。
自联合国安理会第660、661号决议(8月3日,安理会通过第660号决议,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撤军;8月6日,通过第661号决议,下令对伊实行贸易禁运及国外资产冻结)生效以来,安曼成了伊拉克与外界交往的唯一通道。为了保住这条生命线,伊航别出心裁地要求旅客亲手将自己的行李搬上飞机货舱,以免有炸弹混入,这害得我又一通忙乎。坐在身旁的加拿大电器工程师埃尔萨第,是回来清理他在科威特的财产的。听说我要在巴格达待上3个月,他猛地吹了一声口哨,说1月15日以后巴格达就不存在了。在飞机上,我像其他旅客一样得到一张白色的指令:“根据革命指挥委员会第229号命令,在你抵达巴格达5天之内,必须到指定地点做血液检查。”我这才发现,此时逆着外逃的人流进入巴格达,决不是件轻松事。
一下飞机,我和日本NHK记者榎木丸吾及一名法新社记者就被带到候机室一角填写各种表格,并交了一张标准像。我们被告知,所有记者必须住进指定的拉希德饭店,每天费用180美元。日本人“嘿嘿”地连连点头,可我全身上下仅有300美元。因为按惯例新华社外事局仅给我300美元现金。也许这的确能阻止贪污,可对我这样的战争暴徒则无异于送死。窘极无奈,我挺直胸脯走上前,“我是中国人,我没有那么多美元,我的同事在机场外等我。”一位西装男子转身去请示。日本记者榎木趁机对我说:“We are controlled(我们被软禁了)。”我忙朝他挤了一下右眼,“Help each other(互相帮助)。”
在中国使馆帮助下,我终于获准暂住新华社巴格达分社,一座英国式的三层洋房。巴格达的冬夜寒冷刺骨,可中国驻巴格达使馆的小客厅却温暖如春。大使郑达庸是北大东语系校友,他热情地表示“欢迎小字辈”,对我这个胆大包天又四处捣蛋的小师弟自然格外照顾。武官曹彭龄亦北大毕业,其父曹靖华当过北大俄语系主任。武官本人一身儒风,怎么看也不像武官,更像个文化参赞。在曹武官宿舍的地毯上,他用茶杯、咖啡罐、腰带摆了态势图,向我介绍一触即发的战争。在最近的140天里,伊拉克已在南方修了2200公里的甲级公路。在北纬31°线集中了它的全部装甲单位,如著名的“麦地那光明师”、“大汉谟拉比师”;“依赖真主师”则进驻库特,摆出决战的架势;北部三省库尔德人居住区仅部署了一个轻装甲师。我不禁对这种面对进攻却分散兵力的防御表示意外,怀疑这种依靠三条纵向公路的战术原则。曹武官点头同意,因为仅从图上作业看,伊拉克将一战即败。
呼吸着冰凉的夜风,我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日本海军将领的诗句:“战未毕,雨季之郁闷天空,犹在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