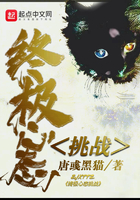岛屿造就两种东西:雕琢控和侵略欲。台湾的文化守贞是表现之一,而日本更典型。资源有限,四围都是危机之海,只得对拥有的东西苛求极致,而后试图扩张(当然,没什么能作为侵略理由,包括整个民族内心的不安全感)。日本比台湾更深地印证了东方人所能达到的虔诚与考究,对自然、对艺术、对制造、对饮食、对生活的规则。那些本来也属于中国,而现在,失了虔诚,也就没了恭谨与考究。
日本与“内地”有一点相同:“个体”的排位总在最末。有一点不同:他们的每个个体都绝对信仰自己的群体根性,哪怕错误,亦抵死坚持。劣根性吗?却也是一个并不庞大的民族繁衍存续、始终保有鲜明特征的依托。一面是现代文明的发达,一面是传统的传承,日本在此间实现的平衡恐怕无人能及,全赖“信力”。除了信仰群体,日本人还相信最微小的事物中也蕴含真理,“只会做豆腐”的小津安二郎、发明了东方威士忌的鸟井信治郎、寿司之神小野二郎或《留住手艺》里的每一个平凡工匠、推理作家、AV女优,以及大大小小的企业家、政客乃至战犯,无论正确与否,都坚信自己是在努力掌握某一种真理。这种有点偏执的态度,转化成可怕的执行力,其中还不乏创造性。
偏执之信,也是悲伤之信,像海啸后盛开的樱花(《津波そして、桜》,获第84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提名),在支撑繁衍的同时,成就一种美,而美亦是民族或群体的向心力之一。当然,如同国家不应大于人、社会不应大于人,民族也同样不应大于人。信的价值,在于给人以存在的线索、攀援而上的力量,以及过程中遵循的规则。
“2011海啸”和“中国”,被称为日本社会再次奋起的“两个催化因素”。经历了多年的茫然无措,日本忽然重现积极姿态,以期恢复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影响力。持续的市场兴奋令投资者习惯在电子邮件落款:“向安倍致敬”(《日本为何突然奋起?》,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2013年05月10日)。我不能站在经济或政治角度预言日本的未来,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其实向往日本的生活——这向往与“惯性”的批判与抵制并存。不管怎样,最好我们也有足够的“信力”与之抗衡,也养成不输于斯的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