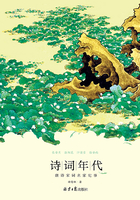(科索沃,1998)
普雷卡茨根本都算不上一个城镇,只不过十来间农舍,沿着夹在几处低矮的褐色小山丘之间的一条土路一字排开。远处是阿尔巴尼亚的高山,四周是科索沃冬季死寂的田野。农舍有红色磁砖铺就的屋顶,厚厚的白灰墙,还有传统样式的院子一这是一种防御型的建筑,也许过去800年都没有怎么变化过。草地从公路边开始,漫延至小山的山顶,之后消失在一片片难看的胭脂栎丛中。如果从这样的胭脂栎丛中穿过,矮树枝会抽打人的面孔。这样的胭脂栎丛,你可不想躲进去。
1998年3月5日,天还没有亮,数百名塞尔维亚特种警察在普雷卡茨周围的山顶上各就各位。山上有迫击炮的炮位、坦克、重型火炮、20毫米加农炮,还有数十辆配备有重型机关枪的装甲运兵车。自从尼古拉·齐奥塞斯库1989年放出他的罗马尼亚秘密警察以来,这还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政府针对自己的公民采取的有预谋的军事攻击,而1989年的那次行动基本上是一个垂死的政府最后的挣扎。此前,则必须要追溯到纳粹时期。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一个省,离意大利仅只200英里,旅游者冬季来这里滑雪。自1945年以来,这里一直都没有发生过战争。现在,它的城镇之一将被从地图上彻底抹掉。
袭击从一阵火炮开始,遭轰击的是一桩农舍,很快就升级成为针对整个村庄的地面攻击。身着黑色油脂制服的警察从装甲运兵车上跳下来,一窝蜂奔向湿糊糊的褐色小山丘,用自动武器扫射,用火箭发射筒发射榴弹。迫击炮弹落在农舍上,点着了房子。据说有阿尔巴尼亚游击队的分离主义者藏在镇子里,而塞尔维亚人根本就不想冒险:他们不准备让那些王八蛋投降,也不准备让他们藏在里面。如果必须的话,所有人都得死。
妇女儿童到处躲藏,后来意识到自己也会被打死,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所以冒险冲过炮火往树林里跑。男人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有些人回击,另外一些人只是躲藏起来,无论哪一种,他们都死掉了。他们死掉了,身后的房子垮塌在身上。自动武器射穿渣煤砖墙打死他们。他们想投降而走向大门口,结果照样被打死。
“军人喊话,要我们一个挨一个出来,否则就打死我们。”一个名叫塞里夫·贾萨里的人,他的女儿后来告诉人权工作者说,“我表兄举起双手出来,他们就在门口开枪打死了他。我们逃跑,刚刚逃出第一道封锁线,士兵就追上了我表弟纳茨米,他一路搀扶着他母亲巴迪杰。他们抓住他,撕下了我们给他穿上的女人衣服,命令他躺在地上,然后再站起来。这样来回做了好多次。之后他们朝他头上和背上开枪,我看见他的身体被子弹击中后不停地扭动。”
塞尔维亚人射击的下一个人是这个姑娘17岁的弟弟,叫里亚德,他们朝他开了两枪。他倒在地上,他姐姐和母亲抓住他的胳膊,将他朝树林方向拖。“我们通过了房子外面的大街上设的第二道封锁线。全副武装的军人穿着绿色制服,衣服上有黄色和黑色的记号,他们的脸上也涂着同样的记号。”贾萨里的女儿说,“我们躲在树丛里,到了山上,我们遇到一些认识的人,他们把我弟弟里亚德运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贝齐尔的妻子萨拉来了,她说他们开枪打中了贝齐尔的腿,他要她带着孩子走。几天之后,我们听说贝齐尔死了。”
贝齐尔·贾萨里是一个富有的阿尔巴尼亚家族的成员,据说在科素沃参与了一个阿尔巴尼亚人独立运动。科索沃约有90%的人属于阿尔巴尼亚人种,但仍然是由塞尔维亚人控制的前南斯拉夫共和国的一部分,1989年取消了它的自治地位。
11月的时候,3名戴着面罩的阿尔巴尼亚游击队员出现在一个葬礼上,此人是在塞尔维亚警察和游击队之间的交火中被打死的,自那以后,这个地区的局势一直十分紧张。“科索沃解放军是为科索沃的解放和国家统一而斗争的惟一武装力量!”其中一个游击队员喊道。哀悼的人共有2万之众,他们都大喊“U-C-K!”这是阿尔巴尼亚语“科索沃解放军”的缩略词。科索沃的抵抗运动由一位长时期的反战主义者领导,名叫伊布拉西姆·鲁哥瓦,但这个抵抗运动也有一支武装派别,随时准备将战斗拖进山区。
科索沃解放军出现在葬礼后不久,立即就开始埋伏袭击警车,狙击检查站。2月下旬发生了一次汽车追击事件和枪战,结果导致4名警察和5名科索沃解放军士兵的死亡。另一名伤势严重的科索沃解放军士兵,据说爬到了附近一个名叫里科萨恩的村庄,躲进了阿哈默特·阿哈默迪的家里。跟贾萨里家族一样,阿哈默迪也是一个富有的家族,据传也与科索沃解放军有联系。
2月28日,塞尔维亚人组织反击。攻击直升机用机关枪和火箭袭击城镇,穿黑色制服的警察把人从房子里拖出来,拉到屋门口台阶上开枪打死。有26个人被打死了。证人说,阿哈默迪家年龄在15岁以上的男子跟妇女和儿童分开,之后被毒打,然后在后院里用猎枪朝他们头部开枪。有一个人连眼球都给挖出来了。后来到那个房子参观过的记者报告说,地上散落着牙齿和毛发,附近的树丛里还挂着一根人类下颚骨。
过了短短的一个平静时期,人们埋葬死者,之后,警察到达普雷卡茨。这个小镇离一个废旧的军需品工厂只不过几百码远,军需厂也改成了塞尔维亚特别警察的军营。3月5日早晨,警察冲出大门开始攻击。一些狙击手连营房都懒得出来。普雷卡茨有55个人死了,仅贾萨里一个家族就死了30个人。
贾萨里家族只有少数几个人逃了出来,其中一个是11岁的小姑娘,叫贝萨尔特,她躲在母亲经常做面包的一块厚板子底下。她记得,炮弹在房子周围响了几个小时,她叔叔阿丹姆唱民歌,“这样,家族就不会失去对生活的信心。”炮击结束以后,全家人的尸体散落在她身旁。24小时后——中间经过了另一轮袭击——好几名警察冲进房子里寻找幸存者。有一个警察在贝萨尔特跟前停下来,但她装死。他把手伸到她胸前,摸到了心跳,因此将她抓起来,带到了军需厂。她浑身溅满鲜血,到了军需厂后哭叫着要跟她姐姐在一起。
大屠杀发生两个星期后,我赶到了科索沃,是在3月一个寒冷的夜里。我跟一位老朋友一起开车去的,他叫哈罗德·多恩博斯,是一位荷兰的新闻记者,1992年以来他一直都驻扎在萨拉热窝。出于明显的理由,塞尔维亚人不给记者发放准入证,但是,哈罗德知道一条通往蒙腾内格罗的边境土路,边境上的哨兵是蒙腾内格罗人,他们根本不管塞尔维亚人要什么。从蒙腾内格罗出发,我们很容易就越过边境到达科索沃。
第二天早晨,我们很早就起床了,想一直开到德伦里卡——这是科索沃解放军的一个乡村据点。我们穿过一个荒凉的褐色平原,一直开进山区,汽车窗外不停地闪过一些小城镇,阿尔巴尼亚边境上的高山在远处时隐时现。在塞尔维亚人看来,枪炮就是翻过那些高山运进来的,阿尔巴尼亚到处都是武器,而科索沃解放军完全依靠来自边境对面的援助。塞尔维亚军方据说有就地正法的命令,任何翻过山峰的人都要打死,士兵们也经常伏击翻越山路往科索沃运送武器的阿尔巴尼亚人。
据说在阿尔巴尼亚有科索沃解放军的训练营,因此,塞尔维亚人调集了大批重型武器在阿尔巴尼亚边境上——远远多于阻止武器走私所需要的数量。人们担心的事情是,塞尔维亚陆军会越境到达阿尔巴尼亚,扫平那里的训练营。人们还担心局势会升级,变成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一场全面战争。这样一场大灾难有可能将希腊和土耳其拖进来,按照最糟糕的预计来说,甚至有可能使联合国分成两派。另一种猜测是,科索沃的战争有可能在马其顿王国触发类似的一场战争,因为马其顿也有一批难以控制的阿尔巴尼亚人,而且希腊和保加利亚有可能参与进来瓜分马其顿人的领土,因为那两个国家一直宣称马其顿的某些领土分别属于他们。有300多名美国军人驻扎在马其顿以防出现这样的多米诺效应,但是,按计划美国军人将于今年夏季撤出马其顿。
我们经过的城镇一片死寂,看上去空荡荡的。一栋接一栋建了一半的房子,阿尔巴尼亚人扔弃了那些房子,他们没有钱完成建房,因为失去了在塞尔维亚人控制的生意中的工作。半个小时后,我们转向一条土路,开到了靠近一条河边的铁路隧道,结果是一条死路。我们停下来,拿起了笔记本,步行穿过隧道,进入一个空荡荡的褐色山谷,周围是灌木丛生的小山。
我们担心会有科索沃解放军的狙击手——真是愚蠢,我们两个人都穿着黑色衣服,跟塞尔维亚秘密警察一样颜色的衣服——但我们更担心塞尔维亚人的狙击手。这里是德伦里卡的中部,是一个警察可以封锁但又无法控制的地区,科索沃解放军可以藏在里面,但又无法防御。这是一片无人之地,可能会被人打死,也可能得到邀请进屋喝一杯茶,这取决于谁先看到你。
我们行走了一个小时,最后看到十几个正在修路的阿尔巴尼亚人。由于塞尔维亚警察控制了公路,看来在连接德伦里卡各个乡村的蜘蛛网一样的土路上,有很多修路工作正在展开。那些人带领我们到了其中一个人的家里,并派人前往邻村去问科索沃解放军的司令官,看看我们可否继续前进。我们坐在地上,喝土耳其式的咖啡,看见卫星电视上正在播放关于美国警察的节目。一个小时以后,那个人回来了,很抱歉地说答案是不行,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科索沃解放军还没有做好欢迎我们的准备。
我们走到屋外,可以听到几英里外塞尔维亚人在轰击一些村庄。炮声在山间回荡,如同夏季的暴风雨。我们仔细打量身边那些农民的脸:男人们粗糙和没有刮过的脸,他们一生除开辛苦的劳作之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不可能看出他们是否知道真正的战争意味着什么。无法判断他们是否明白每天都有这样的悲剧在发生,世界各地都一样。不知道他们是否明白,无论从哪种可能性来说,都不会有人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出面调停。他们是否明白,塞尔维亚当权者为了保持权力会不惜一切手段,就跟世界上的大多数政府一样?
根据神话,1389年,以猎鹰形式出现的圣伊利加造访塞尔维亚的拉萨尔王子。那是与土耳其人进行一场盛大战争的前夜,在科索沃的平原上,拉萨尔纠集了巴尔干半岛上很多的军事精英:波斯尼亚的军阀、阿尔巴尼亚的贵族,还有军服上缝着萨满骨的匈牙利骑兵。可以理解,拉萨尔很是紧张——18年前,土耳其人歼灭了整整一支塞尔维亚军队——不知道是否先撤退等到另外一个日子再战还好些。圣伊利加给了拉萨尔一个选择:地上的一个王国和天上的一个王国。拉萨尔聪明地选择了天上的王国,继而展开战斗,在土耳其人手上迎接自己的死期。
那场战斗后来就成为著名的科索沃盆地(被称作黑鸟战场)之战,它在塞尔维亚人的心灵里占据了相当优越的地位。正是在科索沃盆地上,塞尔维亚的领袖第一次选择了死亡而不是被征服,正是在科索沃盆地上,“只有团结才能救塞尔维亚人”这一句塞尔维亚人指导性的格言,才第一次以浴血的荣光付诸实践。
那场战斗近600年之后,对触发整个巴尔干冲突负有责任的人斯洛波丹·米洛舍维奇站在了那个古老的战场上,促使一大群愤怒的塞尔维亚人投入了狂热的民族主义热潮。“没有科索沃,南斯拉夫根本就不存在!”他喊道,一句话就使自己立即进入政治舞台的中央,“没有科索沃,南斯拉夫就会分崩离析!”
然而,科索沃却不是塞尔维亚人的诞生地。最早的塞尔维亚人是公元600年从萨克森和现在为捷克共和国的地方南迁过来的,而且在接下来的600年当中一直都没有永久性地安居下来。塞尔维亚帝国的黄金时代是14世纪30年代,当时,一个叫斯迪芬·杜赞的凶残贵族在战斗中击败了自己的父亲,勒死父亲后继续扩充自己的帝国,一直发展到了现在的科索沃和希腊。他建立了无数正统的修道院和教堂,最后自封为王,成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统治者。
不过,这个统治者人尚未死,帝国先亡,几十年内,土耳其人在科索沃盆地击败了塞尔维亚人。此后300年,土耳其人残忍地扑灭了另一次起义,结果大部分塞尔维亚人逃出了科索沃。他们留下的空缺被阿尔巴尼亚人填补上了,阿尔巴尼亚人从山上迁移下来,带来了他们粗野的山民习惯。
传统的阿尔巴尼亚社会基于一种氏族制度,之后进一步发展成为兄弟亲族制度和巴耶拉克制度。巴耶拉克制度确认一个地方领袖,称为“巴耶拉克尔”,巴耶拉克尔将保证提供完成军事任务所需要的相当数量的人力。换一个时代的话,阿丹姆·贾萨里和阿哈默特·阿哈默迪极有可能被认为是巴耶拉克尔。那个组织方式后来也逐渐废弃,但氏族制度——主要用于在发生族仇时确定忠诚的对象——看来却存留下来。
在世界的这个角落,如果发生对于男子荣誉和尊严的冒犯,则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仇杀。对男子的不敬包括称某人为撒谎者,侮辱他的女性亲戚,不理会他招待客人的盛情,或者偷窃他的武器。传统规定,这一类的冒犯行为必须予以报复,即必须杀死冒犯者家族中的任何一名男丁。但这样一来便会引起另一轮暴力行为。迟至19世纪末期,5名成年男性的死亡当中,有1名是死于族仇的,而且在今天的阿尔巴尼亚,据说仍然有一项传统存留着,亲族中如果有人被打死,报复的时候,要为亲族尸体上的每一粒子弹杀死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