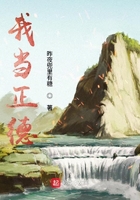王政和被惊醒了。
他已经过了五十,这个年头岁数的士大夫,最讲究的就是养生。天大地大,不如自己的身子骨大。
在平均寿命最多四十的大明,士绅阶层平均寿命肯定在六十以上,活到七十八十甚至九十的比比皆是。
劳心不劳力,又讲养生,饮食平衡,作息起居十分讲究,看医进药没有困难,除非是遇到当时中医难以医治的急症,或是天生的基因不好,不然活到七老八十,并不困难。
王政和这个分守道,做的十分憋屈,辽阳城中他说话已经不算,只有儒学一群官员还算听他的,但指挥这么一群大头兵,实在也是没有什么乐趣可言。
城外的民户和官绅,倒是一天到晚的找他申诉,什么水源被抢了,田骨田皮不清,又有什么军户和民兵械斗的事情,王政和也是一律不理……这样的事,说的再多也伤不到辽阳镇的皮毛,自己也不耐烦管这样的事,仍然一律推到各卫去管,反正实土卫所,各卫都有刑房经历,由着他们去捣浆糊便是。
不管事,就没进项,原本辽阳镇的驻守是总兵的事,各地的兴修建筑,比如修宽甸六堡,这样的大工程是巡抚亲自来督管,底下各堡的修筑,道路,驿传,都司衙门虽管,但还是分守道总其责,地方政务公事,还是文官掌总。
现在却是乾坤倒转,辽阳镇几乎做足了巡抚和州县加驻军的所有活,军屯一兴,干脆将所有的民政事务都给包办了……偏还说不出什么话来,军屯你不叫军镇来管?这道理怎么也是个不通。
至于地方上兴修,比如海港船只,人家是挂在顺字行的名下,盐场铁矿,是整顿各卫下的炒铁和煮盐百户,冠冕堂皇,虽然整个掉了个儿,但偏叫你说不出什么话来,一切都在大明既有的体系之下的动作,偏偏王政和看在眼里,一切都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仅就整个辽阳来说,已经变的叫他快认不出来,可偏生他这个城中的最高等级的四品文官,连说一句话的余地也是没有。
心情大恶之下,索性就诸事不理,每日衙中转转,然后便是回后宅,写信,看花,养鸟,看鱼,倒也悠闲。
只是心中一口恶气难消,每日最大的心愿,就是想看着张惟功在辽阳倒台。
他的后台当然还是申时行,只是现在申阁老刚刚上位,面临着大政更张的重大举措,而上头还压着一个张四维,一成首辅和次辅,矛盾自生,张四维的最大利益格局便是晋商之利,而以惟功的人脉和权势,张四维想堂而皇之的压住辽阳和顺字行,也是需要布局谋划,所以虽然张居正已经离世,朝野中反是一点儿动静也没有。
上头没有安排,王政和就只能隐忍,但这晚外头阵阵轰响,将好梦之中的他惊醒起来,叫这位道台大人终于有忍无可忍之感了。
“说是要抓捕东虏和北虏潜伏在城中的奸细。”
“哼,倒是冠冕堂皇。”
王政和披衣而起,从后宅一路走到二堂,过仪门,吩咐人将大堂正门开了,几十个家人长随伴当簇拥着他,倒也是威风凛凛。
待大门开了,外头火光大盛,他看到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将对面的一大群建筑围的水泄不通,在士兵之后,一长串绳子上牵着大队的被捕人员,有小商人打扮的,也有伙计模样的,普通百姓穿着的,其中倒真有一堆蒙古人……这些蒙古人是借着贸易的名义长久住在辽阳城中,或是归化了的鞑官,以前各卫所里都有一些,辽阳这还算少,要是沈阳广宁,那边的鞑官才叫一个多,沈阳等卫城里,少说是几百上千的蒙古鞑官,都是正经的编束成伍,大明对这些归顺的鞑官也是信之无疑,这种恢宏气度固然是鄣显了天朝的自信,可也是有无穷的隐患。
远的是英宗年间的曹吉祥叔侄之乱,冲阵上前,杀到宫门前谋反的就是蒙古鞑官。
再往后去,努儿哈赤夺沈阳,辽阳,打开城门在城中散布谣言,动摇军心的,便是这些蒙古鞑官。
一看到果真抓了不少鞑子,王政和从鼻孔里冷哼一声,冷冷扫视了眼前的诸多军士一眼。
在场的将士却是丝毫不理,仍然肃立如山。
王政和尴尬之极,他的伴当长随也是怒形于色,可对面的辽阳镇将士仍然不为所动。
“那边是谁?”在这寂静如死的当口,一个骑马的长相如黑铁塔般的青年军官怒驰而至,手中马鞭一指,怒道:“这里抓细作,你们出来做什么?”
“你这黑厮寻死么?”一个长随上前怒道:“这是我们老爷,分守道王大人!”
“哦?”那个青年军官征了一下,接着扬脸道:“王大人我知道,若是平时也罢了,此时抓细作,一会小心打响火铳,子弹飞来飞去的,王大人官再大,也不能防着子弹吧?”
这么一说,众人心里当真十分忌惮,要是所说是真,一会真的打响了,刀枪无眼,伤着了被打死了,那才真是自己找来的冤枉。
只是这黑大个说话十分讨厌,毫无恭谨之意,简直是指着王政和的鼻子在教训。
王政和当分守道多年,此前做过一任知府,两任知县,一路上来,何尝见过这样跋扈的军官。漫说这样一个普通的武官,便是总兵副将一级的,看到他这个正经二甲进士底子的文官,哪一个不是卑躬屈膝的请安问好?不说远的,就曹簠在的时候,同样是钦差驻守辽阳总兵,曹总兵对自己那个恭谨的劲头,张惟功能比吗?
两个总兵,无非一个就是右都督兼辽阳总兵,一个却是全部勋阶衔都齐了,还有一个少国公的勋位在那里。张惟功在仪制上堂而皇之的凌驾于诸多文官之上,也就是倚仗于此。
现在好了,将骄骄一窝,眼前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位份的武官,居然也是有隐隐和自己分庭抗礼的感觉了。
王政和没有发火,在他看来也是不值当的事情,只是盯着那个青年武官,冷然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什么官职?”
“哦,末将是辽阳镇标下千总指挥佥事郭宇,见过王大人。”
郭宇在马上行了个军礼,连马也没有下。
王政和气的脸都白了,终忍不住道:“谁教你的这怪里怪气的礼节,请安打千不会?”
“回王大人,我们总镇大人说过,打千屈膝,还有个军人样子没有,象个男子汉不象?标下当时就在队伍之中,寻思这哈腰下跪,一手按地,确实是个奴婢样,咱当兵吃粮,保家卫国,是堂堂男儿汉,不能用这等礼节,我们大人还说,用这样礼节拜哪个大人,屈了自己,也屈了人家,两榜进士出身的大人们,不能不明白这个道理。”
这郭宇看起来是个黑大个儿,说起话来却是诙谐有趣的紧,但王政和听在耳中,却每一句都是顶撞和恶毒的嘲讽,他几乎要背过气去,怒吼道:“国朝体制,品阶相差二品者,位高者立,位卑者拜!”
“对啊,我和大人没差两品以上啊。”郭宇颇为疑惑的道:“下官是指挥佥事,从四品,大人是分守道,正四品,我们之间,不差品,只差一阶而已。”
“混帐……”王政和指着郭宇道:“本官是文官四品,你是武官!”
“回大人话,朝廷的典章制度,也是本镇扫盲学习的课程之一。下官当时背过,太祖皇帝定制时只提过品阶,连伯爵和驸马怎么避让都规定好了,可没提文武分开来算啊。”
“武职官品级不如文官,这是祖制。”
“大人你的意思是说,太祖高皇帝的话不算祖制?”
“你……”
王政和脸已经成了猪肝色,对面执行军务的士兵们虽然不敢擅动,脸上都带了笑容。
武人在大明社会地位之低下,除了少数混到高层的将领外,普通的中下层武官和士兵在文官眼里就是猪狗不如的地位,加上边军中不少发配的刑徒犯人,这形象就更加别提了。
可现在辽阳镇的形象和地位,在惟功费尽心力的拉拔之下,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军户那里自然不必提,民户们对镇兵的印象也是极佳,郭宇怎么可能在王政和这里伏低做小,将自己视为奴仆一般的去叩拜对方?
哪怕对方真的是绯袍大官,以前自己敬畏有加的大人物,也是一千一万个不成!
“好,本官迟早有一天与你们总镇大人分说此事。”
王政和醒悟过来,对方人多势众,自己奈何不得人家,再吵下去,脸都要丢尽,当下愤愤一指,转头就进了衙门,他的长随伴当们当然也是赶紧跟了进去。
这些人,有门政上的,有伺候上房的,也有跟班,递茶递毛巾把的小兔子,大人物身边,少不得这些人。他们跟在王政和身边,也是头一回见到老爷被一个小武官顶的这般不客气,却又一点儿办法没有。
真老虎顿时就成了纸老虎,所有的长随仆役都在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最后关闭衙门大门的时候,都是变的轻手轻脚,仿佛外头的士兵,随时都会打过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