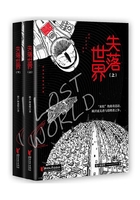一
刘堪无疑是一个短靴狂热者。
方东一第一次与他正式见面时就注意到了,在后来的一系列会诊中,他证明了这点。
方东一觉得很特别,似乎也符合了刘堪的个性。
刘堪是个终日惶惶不安、相当保守的中年男人。
四件款式相同反复替换的条纹衬衫,一只刻不离身的彩色水壶,以及一双没有四季概念的棕褐色短靴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
靴子是旅行式样的。
朋克头,耐磨的厚质皮,还有粗糙的、看上去总好像没系扎实的鞋带。
他总是揣着那只孩子气的塑料玩意,急的时候就打开盖子猛喝,咕噜噜,咕噜噜,好像一头河马。
方东一并没有窥探别人的恶习,仅仅只是,有点好奇。他说不清是为什么。这个数日前不小心被他撞倒在地而又装作若无其事的狼狈男子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冷淡莫奈的外表武装起的,是一块深奥的磁石,至少对方东一而言,有着奇特的吸引力。
不过,他从未注意过刘堪的脚,最起码第一次没有。
方东一和刘堪第一次会面是在正式会诊的第三天。
他刻意把他按排在最后,仿佛意识到与这个男人见面必须储备足够的勇气。
这不合逻辑,完全不合,纯粹是“第六感”在作祟,认定这男人身上蕴藏着某种令他感兴趣的“奇异”。
然现实是,当方东一一眼就认出刘堪的同时也清楚地从他眼里读到了“忘记”二字,因此,除了正常的、和初诊有关的,他什么也没问。
“第一次我们随便聊聊。”
“好。”
刘堪很拘谨地把身体坐端正,露出一丝腼腆,然后,把水壶端正地竖在方东一面前,接着,又觉得不放心,便又拿过来揣进怀里。
“别紧张。”
“不,我不紧张,不紧张……”
其实,他紧张得很。
方东一琢磨着该从哪里着手比较合适。
“这样吧,从最平常的开始,说说你自己,生活、工作、兴趣爱好,什么都可以。”
他考虑了一下。
“我是个记者,在《健康与卫生》杂志社工作,编辑主持一个两性健康的专栏。”
方东一注视着他的眼睛不太自然地眨了眨。
“很奇怪是吧?一个大男人……”他略微倾斜的左臂膀痉挛似地抽动了一下,“我以前是妇科医生,干了不少年,后来结了婚,觉得待遇太低就放弃了。”
“不过,也没选择现在的工作,而是去报考电影学院,那时年轻气盛挺冲动的,说辞就辞,一点考虑的余地也没有,也难怪,谁叫我老大不小了还抱着个导演梦不肯放呢?很蠢,是不是?”
“我不觉得。”
方东一坦率地回答。
“在‘生存’与‘理想’的抉择中,绝大多数人都放弃了想要的而选择了该要的,你有这样的勇气,我很佩服。”
“这不是勇气,是胡闹。”
刘堪决断的口吻有些误解方东一在刻意安慰他的意思。
“遭遇了失业和落榜的双重打击之后,我只好接受杂志社的邀请,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人情,若不是我当医生的时候经常帮他们写稿,他们绝对不可能会想到我。”
此时,刘堪的目光躲开了方东一的视线,为了保护身为中年男子所剩无几的自尊,他尴尬地在方东一的桌子上搜寻,方东一这才发现自己的疏乎――忘了给刘堪倒杯茶。
他立刻站起身,但此时,方东一意外地发现,刘堪的搜寻纯粹只是神经质的本能反应,现在,他的嘴巴正贴在水壶口上。
方东一这才知道,那塑料瓶子也并不只是拿在手中的玩具而已。
“工作不顺导致情绪压抑,这很可能是你始终觉得不快的原因……”
“我想应该不是。”
他停止了喝水。
“哦?”
方东一吃了一惊,他没想到刘堪的思路那么敏捷,难怪缪森觉得他不像个心理有问题的人。
“其实,我自己觉得没什么,是我父母,还有一些朋友,他们认为我应该来看看,所以,我就来了。”
“你好像很清楚自己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不坦率地说出来呢?”
“我想…我想……”
他脸色明显变难看了。
“还是…和我的妻子有点关系……”
“你妻子?”
“刚去世没多久。”
“两个月之前,我们一起去郊外旅行,车子开到郇山公路中段发生了车祸,我活了,她却死了。”
“死在我怀里,我亲眼看着她断气,却,却……什么也帮不了,帮不了……”
他弯下腰,将上半身卷进凹陷的臂弯里。
一种极压抑极怯弱的哭腔从椅背的纤维缝里传出来。
方东一又一次被这样的弃情抑郁所吸引。
他失去了自制力,并体会到一种比眼前这个男人更难受的难受,但不像是从刘堪身上传递而来而是仿如从他妻子亡魂中分离出的一小块,针灸般地折磨着方东一的心穴。
“今天就到这里吧,关于你妻子的部分,我们下次再说。”
刘堪闷闷地点着头,方东一放开抚慰在他肩头的手好让他站起来。
这时,他看见刘堪的左臂膀又痉挛似地抽动了一下。
方东一禁不住双目低垂,那一瞬间,他终于看清了这个动作的真貌。
他在拉裤腿。
那是他紧张时的习惯动作。
也就是这个小小的动作让方东一觉察到了隐蔽在刘堪裤腿下的秘密。
一双朋克旅行短靴的秘密。
二
刘堪离去的那天黄昏,方东一怀着忐忑的心情,急匆匆地赶去赴梅紫的约会。
梅紫工作的医院边上有家口味不错的平价餐馆,梅紫嫌那里太脏老嚷嚷着要换个地方,可方东一觉得很实惠,若将来把房子买在这里,还有个现成的“食堂”搭伙有什么不好呢?
“在这儿买房子?!你脑筋是不是有问题啊?”
“有什么问题?”
“离我父母家近,你上班也方便。”
“那我父母呢!”
梅紫赌气地白方东一一眼,厌烦地打开醋壶盖把筷子匙子全泡进去。
“别这样,别人怎么吃呢?”
方东一皱皱眉。
“我管他。”
梅紫很不高兴。
方东一伸手夺去她手里的餐具,重新把壶盖盖好。
“你怎么那么霸道?”
梅紫收回了孩子气的无聊举动。
他生气了。
梅紫想着待会儿要去见他父母,何必在这个节骨眼把局面弄僵呢?于是,除了乖乖吃饭,轻轻叹息,没再发出任何声音。
“怎么,心情很坏?”
“还不是为了工作,一天到晚净伺候些半死不活的,烦死了。”
方东一突然意识到梅紫说这话的口气和缪森还真像。
“结婚后我想休息一段时间,要不先把孩子生了,只要能离开医院,怎么样都行。”
“年纪轻轻的不工作在家干什么?”
“带孩子呀!”
梅紫杏眼圆瞠煞有架势地,方东一差点扑哧一声笑出来。
“你是这样的人么?”
“我就知道你不爱我,不肯养我,你都不知道我在外面……”
“这是两码事好不好?”
方东一打断她,觉得她想得实在太远太多。
“我不是不肯养你,而是养不起你。”
“只要你能留在中山,就一定、一定、一定养得起我。”
梅紫狡猾地咬了他的耳垂,乐淘淘地结束了这个话题。
方东一冷不妨一个激灵。
显然,不光是来自耳垂的刺激。
方东一告诉梅紫他遇到了一个奇异的病人。
梅紫问:“有多奇?”
“说不出来,总之怪怪的。”
方东一回答。
“没病去中山干嘛?他不怪才怪!”
方东一被梅紫的抢白堵了嘴,他正想说刘堪之所以怪就是因为他不像病人。
这时,门铃响起来了,梅紫借机理顺留海,把衣领拉妥贴。
这小小的细微动作让方东一对女朋友产生了刮目相看的喜欢。
为什么她有时候,忽然,就变得优雅可爱起来了呢?
“爸、妈,我来了。”
梅紫恭敬有礼地对着方东一的父母点头微笑。
方东一难以至信地望着身边那张判若两人的漂亮面孔,几乎不认得她了。
三
方东一如愿以偿地忙碌起来,上午会诊,下午写病史、继续学习主任的档案。
这纯粹是浪费时间,那些文件里根本没有任何让他感兴趣的东西,于是,只好把注意力转移到那三个病人身上,相比之下,还是临床试验生动有价值多了。
会诊让方东一深刻地体会到,缪森在收病人的时候和他们打贫纯属他个人的私好,并非只是无聊时的消遣,只因,他对于那两个病患的概括实在是又贴切又精辟。
23岁的卓欣,即使是面对自己的医生,也难以克制想要曝露身体的冲动,她不停地把衣服的纽扣打开又扣上,扣上又打开,最后,还是决定站起来把已经让她忍无可忍的裤子从里到外脱个干净,这时,方东一很平静地问她:“还记得第一次不想穿衣服是什么时候?”“记得!当然记得!”她思索片刻,很坚定地回答。
“十三岁,哦不,是十四岁,十三岁那年我妈还没改嫁。”
“和妈妈有关么?”
“不晓得。”
她摇摇头,挺认真的样子。
“那父亲呢?我是说,你继父,他对你好么?”
卓欣的双颊立刻绯红起来,两只手不自觉地往胸口滑去。
“他……他……对我很好,很好的,真的很好……”
“有多好,能不能具体说给我听听?”
“不行耶,我怕说不好……”
她越发羞怯的同时,四肢却兴奋地把椅子摇得嘎嘎作响。
“看得出,你继父他一定很爱你,是不是?”
“是的,他爱的。”
“很爱很爱的……”
她故意把声音压得比蚊子还小。
“那比起你妈妈呢?”
方东一进一步刺探。
“不好说,这不好说,他说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
她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嘴里不停地嘀咕着。
方东一觉得够了,不必再继续问下去了。
穿戴整齐的卓欣又恢复到年轻可爱的小女孩模样,倘若走在马路上,没有人会相信她是个随时可能对着男人裸体的‘花痴’。
张大林对卓欣一直很有好感,这使方东一更确信卓欣的病情和那个同样年长她三十多岁的“继父”有关,不过,张大林很快就放弃了这样的妄想,因为卓欣在前不久的一次集体会诊中兴奋地对他展示了自己胸部,患有轻度强迫症的张大林当场就呕吐了,他无法忍受自己的眼睛看到如此污秽的女体。
“我不不不要再参加集集集体会诊诊了。”
他难以容忍地对方东一提出抗议。
“她和你一样也是病人,集体会诊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互相了解,试着接纳自己也接纳别人,从而更坦然地面对自己的病情。”
“不不不要,我就就是不不要!”
张大林的结巴因为这件事而变得越来越严重。不过,短短几次失约之后,他还是重又回到了三人行的队伍中,或许是因为觉得寂寞,又或许是对这样的自己感到厌倦了,总之,他又恢复了自信,不再害怕卓欣的胸、抑或其他什么部位了。
至于刘堪,他是三人之中最“正常”的一个。这使得缪森对他毫无印象。但是,非正常中的正常对一个专业的心理医生来说,无疑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诱惑,引诱着方东一不停地想要从这个男人身上参透些什么,如同参透一面能够透视自己灵魂的镜子。
方东一无时无刻不在思索着缪森所提到的有关“噩梦”的事,但目前,他还没有找到恰当的时机来引入这个话题。
这天,他们依旧围绕着刘堪的妻子和他的短靴展开。
“说说你妻子。”
“为什么?我说和她有关你就当真了?”
“我也就是说说,人都不在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刘堪的状态显然比前两次稳定,他似乎已渐渐习惯了这样的交流,不过,他们之间依然存在着一些沟通上的误会。
方东一完全没有怂恿刘堪用会诊来缅怀亡妻的意思,他一心只想冶好他,而引出导致刘堪忧郁的症结是最为关键的一步,所以,任何机会他都不可以放弃,刘堪必须明白这点。
“我希望我们之间能更自然一些。”
“我想听你想说的,而不是该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