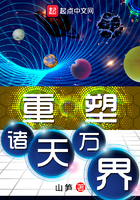“恋舞最后一次见你是什么时候?”
方东一接着问下去。
“25日。”
“那天是25日。”
“在这之前,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日子没见到她了,可是,那天,我预感她会来,不晓得为什么,就觉得她会来找我。”
“没想到,刚上班,她就打电话来了,说今天无论如何要见我一面,我估摸着日子,该是她发病的最后一天,显然,她没有找到令她满意的猎物,最终只得退而求其次地回到了我的身边。”
“我觉得自己可悲极了,甚至有些深恶痛绝,和她做爱什么时候成为我的义务了?我不是她的丈夫,而她也并不爱我,那是他丈夫应该做的事情,不是我。”
“可是,我知道,一旦她站在我的面前,我就无法不去拥抱她,亲吻她,抚慰她,那一刻,悲也好厌也好,全都会消失不见,我真希望它们不要消失,也不该消失,它们理应在最关键的时候提醒我,对于这样的女人,的的确确是不该心存爱念的。”
“于是,我推掉了下午所有的病人,只等着她一个人的到来。”
“然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恋舞的来访并不是为了她体内跃跃欲试的欲望,而是要我再为她说一次谎,伪造一份假的妇科健康证明给她。”
宋怀南暂时停顿下来。
方东一奇怪他们之间居然也有了默契,宋怀南的停顿是因为他确信方东一已经猜到,对于恋舞这最后的请求,他竟然拒绝了。
“我不想再帮她了。”
“不想再和她一样执迷不悟下去。”
“你的意思是,你终于,决定,要放弃她了。”
宋怀南浓密的双眉此刻恍恍然变花白了、稀疏了,好像丢了根似的象碎羽一样要纷纷往下掉了。
“事实上,那不是我的心里话,当时的我,只是太疲瘁了,疲瘁到连三思的力气也没有了,然而,就因为那些话,那些并非出于我本意的意气用事的话,她离开了我,就这么永远地,离开了……”
“恋舞的去世纯粹是个意外,你无需承担这个责任的?”
方东一这才体会到宋怀南的内心世界的确无时无刻不与恋舞联系在一起,喜悦是同等的,悲苦是同等,就连彼此维护的、对病魔抗争到底的人性的尊严也是同等高尚的,除却爱情,他们显然是一对不可分割共患难的战友。
“最起码,她的不告而别是证明了我的无心筑成了大错。”
“她觉得我已经放弃她了,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立场和权利再来纠缠我了……”
宋怀南的话,让方东一胸口阵痛连连,他想到了刘堪,想到了自己同样因怯懦而对他说出的那些违心决绝的话。
刘堪又何尝不是因为觉得他已经放弃了自己,而悄然消失的呢?
此时此刻,方东一和宋怀南一样在扪心自问着:
当真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么?
“后来呢?后来你到底有没有帮她?”
“她提出请求之后,我就立刻回绝了。”
“可是,她对我做了一件我怎么也想不到的事情。”
方东一不语,他想像不出恋舞会对宋怀南做出什么更惊人的举动。
“她沉默片刻,然后,用很悲切的声音对我说,你终于想通了,不再爱我了,是么?”
“我没有回答,因为我不晓得该怎么回答。”
“接着,她转过身体,我知道她想干什么,对这样的行为我简直烦透了,于是,便对她说,你别这样,不要再对我做这些,除了这个,难道,我们之间就没有别的了么?”
“可是,她依旧脱,一件一件,例行公事似地脱。”
“我受不了,受不了这个女人事到临头还在侮辱我的感情,于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她说了刻薄无礼的话。”
“我说,现在的你,是真的和动物没什么两样了!”
方东一的脸色即刻就变阴沉了。
“你不该这么说。”
宋怀南颧骨上的肌肉频频抽动,为了这句不该说的话,他很可能要用一辈子去后悔。
“然后……然后……”
抽搐越发强烈了,他几乎有些说不下去。
“然后,她忽然,整个人倒下来,直挺挺地跪在我脚下,冰冷的地板上。”
方东一着实吃了一惊,这样的场面,是连他身为心理医生的预知力都无法料到的。
“当时,我几乎被她吓到了,站在那里,完全动弹不得。”
“接着,她的语音又恍恍惚惚传了过来,那声音,那语句,刹那间就把我的毅力击溃了。”
“她说,如果你不爱我了,那么,就可怜可怜我吧。”
方东一喉咙里涌出一股荡气回肠的郁气,堵得他非常难受,难受到只有用小刀刺破咽喉释放它才能缓解的地步。
此刻,宋怀南的颧骨却静谧了下来,仿佛,疼痛席卷而过后的坦然,徒留那么一点点的空洞和虚妄。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她对她丈夫的爱情已经彻底粉身碎骨了。”
“她赤裸裸,孤独独地跪在那里,摒弃人格,毫无尊严地乞求我的怜悯。”
“可是,却显得那么地瑰丽,那么地悲壮……让我整个人从内而外地为之颤抖起来。”
“因为,她裸露的,并不是那已如行尸般枯萎的肉体,而是她的魂,她所剩无几却依旧为之深爱着、忠诚着的灵魂……”
方东一艰涩地试图想像那副画面。
可是,他做不到。
正如宋怀南所言,他也失去了三思的力量,所有的感知统统归结到悲痛的经络上来。
就连这痛,也是无法再用任何言语加以描述的了。
这时,宋怀南更加静谧的语调继续向他传递过来: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恢复正常的思绪。”
“那一刻,我的脑袋就像是被巨浪颠覆过又迅速恢复宁静的海滩。”
“爱、感动,道义、责任,种种情绪终又回到了沙滩上面。”
“其实,它们从未被颠覆过。”
“那是我的脚印,我因为爱着她而和她一样孤独地在海滩上踱过的一个又一个难以磨灭的脚印,直到这一刻,我才得以面对那贯穿了终始,且必将持续到亡时的真实存在――刘堪,是恋舞的宿命;恋舞,是我的宿命;而纠缠在恋舞身上的贪婪和欲望,却是我们共同的宿命。”
“我是逃不开她的,无论她是活着,还是死去了,我还是会一个人在沙滩上孤独地漫步,就像,她常常为刘堪做的那样。”
“于是,我对她说,我不怜悯你,你真要那份证明我可以给你。”
“她的眼睛立刻就死灰复燃了。”
“接着,我又说,不过,你必须和我交换。”
“她问,交换什么?”
“我把她从地上抱起来,就像很多年以前,第一次,抱起那个沉浸在焦灼和害怕中的少女一样,深深地,深深地拥抱她。”
“然后,在她耳边说道:我要交换的,只是让我最后再爱你一次的权利。”
方东一的热泪立刻冲出了眼角。
宋怀南没有看见,方东一也完全沉浸在他的叙述里,毫无知觉。
“我们无言地做了爱,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
“然后,她就走了,带着我送给她唯一的一件东西,永远地消失在了我的世界里。”
四
恋舞从诊所大门出来,就开始奔跑。
她并不知道,刘堪跟踪了她,此时,正躲在不远处的喷水池边偷看着。
他们其实离得很近,近到拐个弯就能够撞见,但是,刘堪利用圆形水池的有利地势绕了一圈,巧妙地避开了她。
刘堪一直跟到了诊所的里面。
他看着恋舞挂的号,进的门,当然,也看见了那个叫宋怀南的妇科专家的介绍。
不过,刘堪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在门口等待将近2个半小时,而这段时间里,他始终都盯着目标一步也没敢离开,但是,他并没有看见恋舞走出宋怀南医生的房间。
她不是应该很忙碌的么?不是应该有很多化验要去做么?
可为什么一直都呆在里面呢?
或许,他们先前就认识,说不定,这个宋怀南和当年给恋舞看病的医生是同一个人。
时间都过去那么久了,他们在里面到底谈了些什么呢?
…… ……
刘堪没法这么苦思冥想下去。
可是,除了苦思冥想,他又没有丝毫的办法可以冲进去一探究竟。
蹊跷!
这事越来越诡异,越来越蹊跷了!
接着,恋舞出现了。
她仍然没有到楼上去,而是把什么东西揣进口袋里就急匆匆地跑到大街上去了。
恋舞疾步走出诊所大门的时候,刘堪看得非常清楚。
正因为看得很清楚,他才能确定自己不是神经错乱,这样的判断不是被猜疑逼疯下的冲动。
刘堪看见的是一个仓皇失措的恋舞。
一个对他来说陌生得不能再陌生的恋舞。
她出门前整齐的头发明显地被捣乱了。
眼睛红肿着,面色却很红润,接近病态的红润。
甚至,让人想到要用“躁动”来形容。
她腋下夹着皮包,两只手紧紧地扣住胸前的衣服,好像刚才,有什么事情发生过,以至于慌乱中没有时间将衣服的纽扣恢复原状。
恋舞走过刘堪眼前也是一霎那的事情。
不过,刘堪还是瞟到了她交错的手腕一下的那半截衣服。
扣子的确被胡乱地扣错了,使得她的下半截衣服揪成一个显而易见的凸起,即使隔着距离也一眼就能看见。
刘堪呆住了。
他停止了他的苦思冥想。
他开始怀疑眼前这个一晃而过的女人到底是不是恋舞?
如果是,那么现在,还有谁能阻止他不将亲眼所见的这一幕和那扇禁闭了两个多小时的,诊所办公室门内的男人联想到一起呢?
傍晚时分,刘堪到家时,发现恋舞已经回来了。
她褪却了连日来笼罩在她身上的那件沉甸甸的黑色大衣,穿上了薄薄的针织衫,如同换了一个人那么清爽。
她热情地招呼他,端茶,准备丰盛的晚餐,心情显得相当好,和下午走出诊所的女人截然不同。
刘堪暂且把心头的问号一个一个压下去,食不知味地吃着她的晚餐。
心想:冷静,千万要冷静,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说什么都是无用的。
于是,刘堪决定从最可靠的东西上下手,也许,获得证据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饭后,他假装要找本重要的资料,独自溜进书房里,然后把门虚掩,迅速地在堆满容器的书橱里寻找一张新面孔。
不料,就在这个时候,恋舞进来了。
“刘堪。”
她柔声叫道。
刘堪打了个冷战,慌忙从书架上随便抽了一本回过头去。
“我今天去做检查了。”
她把纸片递给他,指尖微妙地颤动着。
刘堪不说话,只是盯着她的眼睛看,笔直地,不打算轻易放手地往里面看。
“你…怎么了?怎么不说话?”
她有点惑然。
“哦,没什么,你放在桌上,等下我看看。”
她点点头,往书桌边走去。
“今天又去逛街了?”
她的背影本能地怔了一怔,然后,线条马上就恢复了正常。
她优雅地把身子转回来,对刘堪微笑。
“你怎么知道?”
“这不是你新买的么?”
刘堪随手拿起书橱隔板上的一只陈旧的古董烟灰缸。
她不动声色,丝毫瞧不出破绽。
“是啊,路过地摊,就忍不住挑了一个,我觉得它挺别致的,你说呢?”
“是,是很别致,很别致……”
刘堪看了烟灰缸一眼,将它放回原位。
“我先去洗澡了。”
她就打算这么走了。
刘堪把手里的书插回书架,重新摆出搜索的样子。
恋舞看了他一眼,没再多说什么,就悄悄离开了书房,并按照刚才的样子,把房门虚掩。
浴室里水声响起来了。
刘堪放下书,重新打开书橱,拿出那只古董烟灰缸。
他呆呆地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脑海中一片空白。
然后,不经意地,将烟灰缸从左手换到了右手。
一个男人的名字跃入了眼帘。
很熟悉的三个字。
看似模糊,实际却很深地烙在那烟灰缸的底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