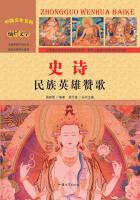“喔。”胡雪岩只答了这么一个字,等他说下去。“今儿中午,刘中丞派人来请我去吃饭,告诉我说,你有东西寄放在别处,问我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是不是朱宝如夫妇在捣鬼?胡雪岩心里很乱,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雪岩,”德馨又说,“以咱们的交情,没有什么话不好说的。”胡雪岩定一定神,想到刘秉璋手中不知握有什么证据,话要说得活络,“晓翁,你晓得的,我决不会做这种事。”他说,“是不是小妾起了什么糊涂心思,要等我回去问了才明白。”
“也许是罗四姐私下的安排。”德馨踌躇了一下说,“刘中丞为此似乎很不高兴,交代下来的办法,很不妥当,为了敷衍他的面子,我不能不交代杭州府派两个人去,只当替你看门好了。”
很显然的,刘秉璋交代的办法,一定是派人监守,甚至进出家门都要搜查,果然如此,这个台坍不起。到此地步,什么硬话都说不起,只有拱拱手说:“请晓翁成全,维持我的颜面。”
“当然,当然,你请放心好了。不过,雪岩,请你也要约束家人,特别要请罗四姐看破些。”
“是、是。谨遵台命。”
“你请回吧!吴知府大概就会派人去,接不上头,引起纷扰,面子上就不好看了。”胡雪岩诺诺连声,告辞上轿,只催脚夫快走。赶回元宝街,问清门上,杭州府或者仁和县尚未派人来过,方始放下心来。“如果有人来,请在花厅里坐,马上进来通报。”交代完了,仍回百狮楼,螺蛳太太正陪着乌先生在楼下闲谈,一见了他,都站起身来,以殷切询问的眼色相迎。想想是绝瞒不过的事,胡雪岩决定将经过情形和盘托出,但就在要开口之际,想到还有机会,因而毫不迟疑地对螺蛳太太说:“你赶快寻个皮包,或者帽笼,捡出一批东西来,请乌先生带走。”
“为啥?”
“没有工夫细说,越快越好。”
螺蛳太太以为抄家的要来了,吓得手软心跳,倒是阿云还镇静,一把拉住她说:“我扶你上楼。”
“对!阿云去帮忙,能拿多少是多少,要快。”螺蛳太太咬一咬牙,挺一挺胸,对阿云说道:“拿个西洋皮包来。”说完,首先上楼。“怎么?”乌先生问,“是不是京里有消息?”
“不是。十之八九,是朱宝如去告的密,说罗四姐有东西寄放在外面。刘中丞交代德晓峰,要派人来——”
一句话未完,门上来报,仁和县的典史林子祥来了。“有没有带人来?”
“四个。”胡雪岩提示了一个警戒的眼色,随即由门房引领着,来到接待一般客人的大花厅,林子祥跟胡雪岩极熟,远远地迎了上来,捞起衣襟打了个千,口中仍旧是以往见面的称谓:“胡大人!”
“不敢当,不敢当!四老爷。”县衙门的官位,典史排列第四,所以通称“四老爷”,胡雪岩一面拱手还礼,一面说道,“现在我是一品老百姓了,你千万不要用这个称呼。”
“胡大人说哪里话,指日官复原职,仍旧戴红顶子。我现在改了称呼,将来还要改回来,改来改去麻烦,倒不如一仍旧贯。”
“四老爷口才,越来越好了。请坐。”揖客升炕,林子祥不肯上座,甚至不肯坐炕床,谦让了好一会,才在下首坐下,胡雪岩坐在炕旁一张红木太师椅上相陪。“今天德藩台已经跟我谈过了,说会派人来,四老爷有啥吩咐,我好交代他们照办。”
“不敢,不敢!上命差遣,身不由己,县大老爷交代,我们仁和县托胡大人的福,公益事情办得比钱塘县来得风光,叫我不可无礼。”林子祥紧接着说,“其实县大老爷是多交代的,我带人到府上来,同做客人一样,怎么好无礼?”
这话使得胡雪岩深感安慰,每年他捐出去“做好事”的款子不少,仁和县因为是“本乡本土”,捐款独多。如今听县官的话,可见好歹还是有人知道的。
“多谢县大老爷的美意。”胡雪岩说,“今年我出了事,现在所有的一切,等于都是公款,我也不敢随便再捐,心里也满难过的。”
“其实也无所谓,做好事嘛!”林子祥说,“哪怕抚台晓得了,也不会说话的。”
“是,是!”胡雪岩不知如何回答。“现在辰光还来得及。”林子祥说,“今年时世不好,又快过年了,县大老爷想多办几个粥厂,经费还没有着落。”
“好!我捐。”胡雪岩问,“你看要捐多少?”
“随便胡大人,捐一箱银子好了。”胡雪岩只觉得“一箱银子”这句话说得很怪,同时一心以为县官索贿,却没有想到人家是暗示,可以公然抬一个箱子出去,箱子之中有夹带,如何移转,那是出了胡家大门的事。
“现银怕不多,我来凑几千两外国银行的票子。等一息,请四老爷带回去。”
林子祥苦于不便明言,正在思索着如何点醒胡雪岩,只见胡家的听差进来说道:“仁和县的差人请四老爷说话。”
差人就在花厅外面,从玻璃窗中望得见,林子祥怕胡雪岩疑心他暗中弄鬼,为示坦诚,随即说道:“烦管家叫他进来说。”
这一进来反而坏事,原来乌先生拎着一个皮包,想从侧门出去,不道林子祥带来的差人,已经守在那里,乌先生有些心虚,往后一缩,差人拦住盘问,虽知是胡家的客人,但那个皮包却大有可疑,所以特来请示,是否放行?
“当然放。”林子祥没有听清楚,大声说道,“胡大人的客人,为啥盘问?”
这官腔打得那差人大起反感,“请四老爷的示,”他问,“是不是带东西出去,也不必盘查?”
“带什么东西?”
“那位乌先生带了个大皮包,拎都拎不动。”
这一说,胡雪岩面子上挂不住,林子祥也发觉自己在无意中弄成一个僵局,只好继续打官腔:“你不会问一问是啥东西?”
“我问过了,那位乌先生结结巴巴说不出来。”见此光景,胡雪岩暗暗叹气。他知道林子祥的本意是要表明他在他心目中,尊敬丝毫不减,但形禁势格、今非昔比,要帮他的忙,只有在暗中调护,林子祥将差人唤进来问话,便是一误,而开口便打官腔,更是大错特错,事到如今,再任令他们争辩下去,不特于事无补,而且越来越僵,面子上会弄得很难看。
转念到此,他以调人的口吻说道:“四老爷,你不要怪他,他也是忠于职守,并没有错。那皮包里是我送我朋友的几方端砚,不过也不必去说他了,让我的朋友空手回去好了。”
“不要紧,不要紧!”林子祥说,“几方端砚算啥,让令友带回去。”
胡雪岩心想,如果公然让乌先生将那未经查看的皮包带出去,那差人心里一定不服,风声传出去,不仅林子祥会有麻烦,连德馨亦有不便,而刘秉璋说不定会采取更严厉的措施,面子难看且不说,影响到清理的全局,所失更大。
因此,他断然地答一声:“不必!公事公办,大家不错。”他随即吩咐听差:“你去把乌先生的皮包拎进去。”林子祥老大过意不去,“令友乌先生在哪里?”他说,“我来替他赔个不是。”
对这一点,胡雪岩倒是不反对,“不是应该我来赔。”说着,也出了花厅。
林子祥跟在后面,走近侧门,不见乌先生的踪影,问起来才知道已回到百狮楼楼下了。
结果还是将乌先生请了出来,林子祥再三致歉以后,方始辞去。面子是有了,里子却丢掉了。乌先生一再引咎自责,自嘲是“贼胆心虚”。螺蛳太太连番遭受挫折,神情沮丧,胡雪岩看在眼中,痛在心里,而且还有件事,不能不说,踌躇再四,方始出口。
“还要凑点钱给仁和县。快过年了,仁和县还想添设几座粥厂,林子祥同我说,县里要我帮忙,我已经答应他了。”
螺蛳太太先不做声,过了一会才问:“要多少?”
“他要我捐一箱银子,我想——”
“慢点!”螺蛳太太打断他的话,“他说啥?‘一箱银子’?”
“不错,他是说一箱银子。”
“箱子有大有小,一箱是多少呢?”
“是啊!”胡雪岩说,“当时我也觉得他的话很怪。”
“大先生。”一直未曾开口的乌先生说,“请你把当时的情形,说一遍看。”
“我来想想看。”胡雪岩思索当时交谈的经过,将记得起来的情形,都说了出来。一面回想,一面已渐有领悟。“莫非他在‘豁翎子’?”乌先生说。“豁翎子”是杭州俗语,暗示之意。
暗示什么呢?螺蛳太太明白了,“现在也还来得及。”她说,“趁早把林四老爷请了回来,请乌先生同他谈,打开天窗说亮话好了。”
乌先生不做声,只看着胡雪岩,等候他的决定,而胡雪岩却只是摇头。
“事情未见得有那么容易。箱子抬出去,中间要有一个地方能够耽搁,把东西掉包掉出来,做得不妥当,会闯大祸。”他停了一下,顿一顿足说,“算了!一切都是命。”
这句话等于在濒临绝望深渊的螺蛳太太身后,重重地推了一把,也仿佛将她微若游丝的一线生机,操刀一割,从那一刻开始,她的神思开始有些恍惚了,但只有一件事,也是一个人的记忆是清楚的,那就是朱宝如的老婆。
“阿云,”她说,“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一口气咽不下,哽在喉咙口,我会发疯。我只有想到一件事,心里比较好过些,我要叫起黑心吞没我活命的东西,还狠得下心,到巡抚衙门去告密的人,一辈子会怕我。”
阿云愕然,“怕点啥?”她怯怯地问。“怕我到阎罗大王那里告状告准了,无常鬼会来捉她。”
“太太,你,”阿云急得流眼泪,“你莫非要寻死?”螺蛳太太不做声,慢慢地闭上眼,嘴角挂着微笑,安详地睡着了。这一睡再没有醒了,事后检查,从广济医院梅藤更医生那里取来的一小瓶安神药,只剩了空瓶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