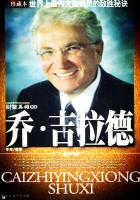这年杭州的春天,格外热闹,天气暖和,香客船自然就到得多,这还在其次,主要的是胡老太太做生日,传说如何如何豪华阔气,招引了好些人来看热闹。何况光算外地来拜寿的人,起码也增加了好几千人。到得开贺的第一天,城里四处,城外三处,张灯结彩,“清音堂名”细吹细打的寿堂周围,车马喧阗,加上看热闹的闲人、卖熟食的小贩,挤得寸步难行。只有灵隐是例外,因为三大宪要来拜寿,仁钱两县的差役以外,“抚标”亦派出穿了簇新号褂子的兵丁,自九里松开始,沿路布哨弹压,留下了极宽的一条路,直通灵隐山门。从山门到寿堂,寿联寿幛,沿路挂满,寿堂上除了胡雪岩领着子侄,等在那里,预备答谢以外,另外请了四位绅士“知宾”。一位是告假回籍养亲的内阁学士陈怡恭,专陪浙江巡抚刘秉璋;一位是做过山西臬司,告老回乡的汤仲思;另外两位都是候补道,三品服饰,华丽非凡,是张安明受命派了裁缝,量身现做奉赠的。
近午时分,刘秉璋鸣锣喝道,到了灵隐。藩臬两司,早就到了,在寿堂前面迎接,轿子一停,陈怡恭抢上前去,抱拳说道:“承宪台光临,主人家心感万分。请,请!”
肃客上堂,行完了礼,刘秉璋抬头先看他的一堂寿序,挂在西壁前端,与大学士宝鋆送的一副寿联,遥遥相对,这是很尊重的表示,他微微点头,表示满意。
这时率领子侄在一旁答礼的胡雪岩,从红毡条上站起身来,含笑称谢:“多谢老公祖劳步,真不敢当。”
这“老公祖”的称呼,也是乌先生想出来的。因为胡雪岩是布政使衔的道员,老母又是正一品的封典,自觉地位并不下于巡抚,要叫一声“大人”,于心不甘,如用平辈的称谓,刘秉璋字仲良,叫他“仲翁”,又嫌太亢。这个小小的难题跟乌先生谈起,他建议索性用“老公祖”的称呼,地方官是所谓父母官,仕绅对县官称“老父母”,藩臬两司及巡抚则称“老公祖”,这样以部民自居,一方面是尊重巡抚,一方面不亢不卑反而留了身份。刘秉璋自然称他“雪翁”,说了些恭维胡老太太好福气的话,由陈怡恭请到寿堂东面的客座中待茶,十六个簇新的高脚金果盘,映得刘秉璋的脸都黄了。
稍坐一坐,请去入席。寿筵设在方丈之西的青猊轩。这座敞轩高三丈六尺,一共六间,南面临时搭出极讲究的戏台,台前约两丈许,并排设下三席,巡抚居中,东西藩臬,大方桌前面系着平金绣花桌围,贵客面对戏台上坐,陈怡恭与胡雪岩左右相陪,后面另有四席,为有差使的候补道而设。偌大厅堂,只得七桌,连陪客都不超过三十个人,但捧着衣包的随从跟班,在后面却都站满了。
等安席既罢,戏台上正在唱着的《鸿鸾禧》暂时停了下来,小锣打上一个红袍乌纱、玉带围腰、口衔面具的“吏部天官”,一步三摆地,走到台前“跳加官”。这是颂祝贵客“指日高升”、“一品当朝”,照例须由在座官位最高的人放赏,不过只要刘秉璋交代一声就行了,主人家早备着大量刚出炉的制钱,盛在竹筐中,听得一个“赏”字,便有四名健仆,抬着竹筐,疾步上前,合力举起来向台上一泼,只听“哗喇喇”满台钱响,声势惊人。
接下来便是戏班子的掌班,戴一顶红缨帽,走到筵前,一膝屈地,高举着戏折子说道:“请大人点戏。”
“点戏”颇有学问。因为戏名吉祥,戏实不祥,这种名实不符的戏文很多,不会点会闹笑话,或者戏中情节,恰恰犯了主人家或者哪一贵宾的忌讳,点到这样的戏,无异公然揭人隐私,因而成不解之仇者,亦时有所闻。刘秉璋对此外行,决定藏拙,好在另有内行在,当下吩咐:“请德大人点。”
他指的是坐在东面的藩司德馨,他是旗人,出身纨绔,最好戏曲,当下略略客气了两句,便当仁不让地点了四出不犯忌讳而又热闹的好戏,第一出是《战宛城》,饰邹氏的朱韵秋,外号“羊毛笔”,是德馨最赏识的花旦,演到“思春”那一段,真如用“羊毛笔”写赵孟頫字,柔媚宛转,令人意消。
正当德馨全神贯注在台上时,有个身穿行装的“戈什哈”悄悄走到他身旁,递上一封信说:“师爷派专人送来的。”
陈师爷是德馨的亲信,此时派专人送来函件,当然是极紧要的事,因而当筵拆阅,只见他面现诧异之色,挥一挥手遣走“戈什哈”,双眼便不是专注在“羊毛笔”身上,而是不时朝刘秉璋那边望去。
他是在注意胡雪岩的动静,一看他暂时离席,随即走了过去,将那封信递了过去,轻声说道:“刚从上海来的消息。”
刘秉璋看完信,只是眨眼在思索,好一会才将原信递给陈怡恭:“年兄,你看,消息不巧,今天这个日子,似乎不宜张扬。”
“是!”陈怡恭看完信说,“这一来,政局恐不免有一番小小的变动。”
“是的。”刘秉璋转脸问德馨说,“请老兄在这里绷住场面,我得赶紧进城了。”
德馨也想回衙门,听刘秉璋如此交代,只能答应一声:“是。”于是刘秉璋回身招一招手,唤来他的跟班吩咐:“提轿。”接着向陈怡恭拱一拱手,正待托他代向主人告辞时,胡雪岩回来了。“怎么?”他问,“老公祖是要更衣?”“不是!”刘秉璋歉意地说,“雪翁,这么好的戏、好的席,我竟无福消受,实在是有急事,马上得回城料理。”“呃、呃。”胡雪岩不便多问,只跟在刘秉璋后面,送上轿后方始问德馨,“刘中丞何以如此匆匆?到底是什么急事?”“此处不便谈。”德馨与胡雪岩的交情极厚,以兄弟相称,“胡大哥,有个消息,不便在今天宣扬,不过,消息不坏。”胡雪岩点点头不做声,回到筵前,直待曲终人散,才邀德馨到他借住的一间禅房中,细问究竟。“为什么今天不便宣扬呢?”德馨说道,“李太夫人在武昌去世了。”
去世的是李瀚章、李鸿章兄弟的老母。胡老太太做生日,自然不便宣布这样一个不吉利的消息。但这一来,李氏兄弟丁忧守制,左宗棠暂时去了一个政敌,对胡雪岩来说,当然是有利的,亦可说是喜事,不过只能喜在心里而已。
“一下子两个总督出缺,封疆大吏要扳扳位了。不晓得哪个接直隶,哪个接湖广?”
这一问,恰恰说中德馨的心事。总督出缺,大致总是由巡抚调升,巡抚有缺,藩司便可竞争,刘秉璋与德馨,各有所图,所以都急着要赶进城去打听消息。不过德馨既有巡抚嘱咐,又有胡家交情在,不便就此告辞,心想何不就跟胡雪岩谈谈心事。
“湖广,我看十之八九是涂朗轩接,直隶就不知道了。”涂朗轩就是湖南巡抚涂宗瀛,他替曾国藩办过粮台,与李瀚章昔为同事,今为僚属,由他来接湖广总督,倒是顺理成章的事。
“那么湖南巡抚呢?”胡雪岩笑着掉了句文,“阁下甚有意乎?”“只怕人家捷足先登了。”“那也说不定。”胡雪岩想了一下说,“你先要把主意拿定了,才好想办法,倘或老大哥根本没有这个意思,也就不必去瞎费心思。”“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爬,岂能无意。不过鞭长莫及,徒唤奈何。”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胡雪岩说,“等我来打个电报给汪惟贤,要他去寻森二爷探探‘盘口’。”此事不便假手于人,胡雪岩又拿不起笔,因而由他口述,让德馨执笔,电报中关照汪惟贤立即去觅宝森,托他向宝鋆探探口气,藩司想升巡抚,该送多重的礼。
德馨字斟句酌,用隐语写完,看了一遍说:“宝中堂他们兄弟不和,森二爷或许说不上话。是不是请汪掌柜再探探皮硝李的口气?”
“好!我赞成。”于是德馨改好了电报稿子,胡雪岩叫进贴身小跟班阿喜来,他专替主人保管一个一离家就要带着的西洋皮包,内中有个密码电报本,胡雪岩与德馨亲自动手,将密码译好,夕阳已经衔山了。
“我本来不打算进城,现在非回去一趟不可了。”胡雪岩说,“电报要送到上海去发,我派一个妥当的人去,叫他在上海等回电,如果是两三万银子,我先替你垫。多了就犯不上了。”
“是,是。一切拜托,承情不尽。”于是胡雪岩与德馨一起进城,两人品秩相同,但胡雪岩曾赏穿黄马褂,所以仪从较现任藩司的德馨,更为显赫,只是他的“高脚牌”只作陈列之用,出行只是前面一匹顶马、后面四匹跟马、八抬大轿的轿班,一共三班,轮流换肩——胡雪岩的轿班,在家亦是“老爷”,一回家就会听见丫头在喊:“老爷回来了,赶快打水洗脚。”不过替胡雪岩抬轿虽是好差使,却很难当,因为既要快,又要稳,快到能跟着顶马亦步亦趋,稳到轿中靠手板上的茶水不致泼出来。因此,两人虽是同时动身,胡雪岩的轿子起步就领先,很快地将德馨在身后抛得老远了。回到元宝街,老远就看到张灯结彩,灯烛辉煌,但寿堂中却颇安静,因为既已排定贺寿的日期,除了极少数的至亲以外,不会有人贸然登堂。胡雪岩下了轿,在寿堂中略作寒暄,随即着手处理德馨谋官之事。
正唤来得力的家人在交代时,只见螺蛳太太扶着一个小丫头的肩,悄然而至,看到胡雪岩有事,她远远地在一张丝绒安乐椅上坐了下来。“你明天一大早就动身,在上海等消息,等北京的回电一到,马上赶回来。越快越好。”等家人答应着走了,螺蛳太太一面起身走近来,一面问道:“你不在灵隐陪老太太,怎么回城来了?”“出了两个总督的缺,连带就会出两个巡抚的缺,德晓峰想弄一个,我只好进城来替他料理。”说到这里,胡雪岩发觉螺蛳太太神色有异,定睛看了一下问道,“怎的,你哭过了?”
“不要乱说!老太太的好日子,我哭什么?”螺蛳太太紧接着问:“客人来得多不多?”“该来的都来了。”胡雪岩说,“三品以上的官,本来没有多少,从明天起就要一天比一天忙了。我最担心后天,大家都说要去看热闹,不晓得会不会有啥笑话闹出来?”
原来贺寿的日期,已经重新安排,第三天轮到外宾。“洋人拜寿”这四个字听起来,就会逗人好奇,都说不知道洋人拜寿是怎么个样子,是磕头还是作揖?吃寿面会不会用筷子,不会用用啥?叉子叉不住,只怕要用手抓。诸如此类等着看笑话的议论,不免使胡雪岩不安,怕闹出笑话来失面子。
“喔,”螺蛳太太倒被提醒了,“有份礼在这里,你倒看看。”说着,便向窗外喊一声,“来人!”进来的是螺蛳太太的亲信大丫头瑞香,她已经听到了螺蛳太太的话,所以进门便说:“洋人送的那份礼,送到老爷书房里去了。”
胡雪岩心想,这个把月来,所收的寿礼,不知凡几,独独这份礼送到他书房,可知必有来历,便即问说:“是哪个送的?”
“我也不清楚。”螺蛳太太说,“是拱宸桥海关送来的,我想大概不是洋行里的人,是个洋官,所以叫他们送到书房里,等你来看,有份全帖在那里,你一看就晓得了。”“好!我到书房里去看。”
“对!外面要开席了,我也要去照个面,敷衍敷衍。你呢?在哪里吃?”
“太累,吃不下什么,吃点粥吧。”“老太太的寿面不能不吃。”螺蛳太太转脸吩咐,“瑞香,你关照小厨房下碗鸡汤银丝面,鸡汤太浓,要把浮油撇干净。”于是主仆三人各散,胡雪岩一个人穿过平时就沿路置灯、明亮好走的长长的甬道,来到他的书房镜槛阁。这镜槛阁是园中一胜,前临平池、后倚假山,拾级而上时,那扶手是以铁杆为芯,外套是在景德镇定烧的,朱翠相间,形如竹节的瓷筒,阁中有一面极大的镜砖,将阁外平池、池中鸳鸯、池上红桥、池畔垂杨,一齐吸入镜中,这是仿北京玄武门外,什刹海畔恭亲王的别墅鉴园的规模所造,而精巧过之。
胡雪岩进得阁来,在镜砖面前站了一会儿,看远处楼阁、近处回廊,都挂着寿庆的灯彩,倒影入池,复又重生于镜,镜中有镜,影中有影,疑真疑幻,全不分明了。正看得出神时,听得有个娇嫩的声音:“老爷,房门开了。”
胡雪岩抬头看时,这个小丫头仿佛见过,便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梅。”“喔,你是新派过来的吗?”“不!我老早就在这里了。”
“老早在这里?为啥不常看到你?”胡雪岩一面说,一面踏进书房,触目一大堆礼物,便顾不得跟小梅说话,先找全帖来看。
全帖的具名是“教愚弟赫鹭宾”。原来是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此人在华二十多年,说得一口极好的京腔,也识汉文,仰慕中华文化,兼且是朝廷的有顶戴的客卿,所以用他的英文名字的发音,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做“赫鹭宾”。
全帖以外还有礼单。寿礼一共四样,全喜精瓷茶具、一个装糖果的大银碗、整匹的呢料,另外一个老年人用的紫貂袖筒。
“来啊!”
他心目中使唤的是专管镜槛阁的两个大丫头,巧珠、巧珍两姐妹,但来的却是小梅。
“两巧一巧都不巧。”小梅答说,“都跟老太太到灵隐去了。”胡雪岩看她语言伶俐,料想也能办事,便即说道:“你也一样。你去寻两个人来,把这四样东西搬到外面,叫人马上送到灵隐给老太太看。说是——”
这要说赫鹭宾就是赫德,这位“洋大人”戴的也是红顶子,那就太噜苏了,怕传话的人说不清楚,所以停了下来。
“老爷要啥?”“我要写字。”
小梅听说,立刻走到书桌前面,掀开砚盖,注了一小杓清水,细细研墨。胡雪岩便坐了下来,提笔蘸墨,很吃力地在全帖上批了六个字“即总税司赫德”。
小梅因为墨渖未干,便拿起全帖,嘟起小嘴朝字上吹气。正吹得起劲时,瑞香来了。
见此光景,她先是一愣,接着便呵斥小梅:“出去!这地方也是你来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