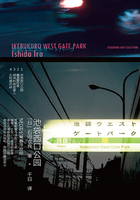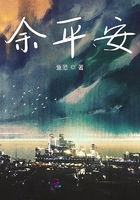“你以前不是犯了事吗,如何又到太原做官?好不荣耀啊!”薛良见左右无人,就问道。
“以前的事你不要再提起,你因何晓得我在这里?”李福达摇手道。
“昨天在路上看见你,因随从人多,不好相叫,今天特来问候。只是我流落此地,盘缠已经用尽,想请你资助资助,不知愿意不?”薛良问道。
“这没问题!只是你既然来了,也须耽搁几日,待我准备盘费,送兄回府如何?”李福达见自己的底细薛良知道,心中另有打算。
薛良还认为这是李福达的好意,连声称谢。随即李福达吩咐备下夜饭,两人相对而饮,非常要好。
吃过饭,李福达便吩咐家人道:“将我这位老乡的铺盖安置在书房。”两人又谈了一回,各自回房了。
李福达回房后暗自思忖:我的踪迹并无人晓得,今日被这个无赖识破,倘若他将我的前事告诉别人知道,这还了得!不如先下手为强,将他杀死,就绝了后患了。暗暗打算一番,李福达便叫来两个心腹家人,悄悄嘱咐道:“今日来的这人,与我有宿世冤仇。我留他住在书房,原要害他性命。现在给你们快刀一把,今夜三更时分结果了他,把尸首抛在荒野地面。做得干净,先赏二十两银子,日后还有抬举你们处。你们肯去不肯去?”
两人欣然应允道:“老爷请自管安睡。小的们别的做不来,些些小事,包管做得万妥万当。”
李福达大喜。两人欣然出去,准备半夜行事。
再说薛良,吃了夜饭,坐了半晌,关上书房门,正要上铺去睡,忽然一阵腹痛,便走出书房想找茅厕大便。当天夜晚月色微明,他见一边有路可通,就穿过去。走到马坊所在,有一块空地,便想在地上解手,忽隐隐听见隔墙有一人说话:“住在书房这人,老爷为何要杀他?”
另一人道:“你没听见老爷说与他有仇吗?”
薛良一听,惊得魂飞天外,连大便也不敢拉了。他心中暗想:想不到这个贼寇,如此心狠。如果再延误,性命恐怕也保不住了,还是赶紧逃命为上。于是就轻轻走过马坊,见有一堵泥墙,便从低处跳出。幸喜下面已是大路,拔腿便跑。
薛良一口气不知跑了多远,正好碰到太原府知府赴宴回来,薛良跑得收脚不住,直冲了知府的道路,被差役拿住,喝问道:“你是何人,敢冲撞知府大人的轿子?”
薛良正寻思要揭发李福达,苦无门径,现在看见是太原府正堂的灯笼,连忙连声喊冤。
知府喝道:“你有何冤事,黑夜叫喊?”
薛良道:“小人是逃出来的,有天大的事相告。不敢当着众人明言,求大人带小人到私衙密禀。”
知府就吩咐带薛良回衙。一进衙门,知府便问薛良有什么事相告。
薛良禀道:“小的本是代州人,与妖贼李福达是同乡。以前听说他逃亡到了别处,昨天撞见太原卫指挥使张寅,细细一认,却正是李福达。小的前去探望,李福达嘱咐小的不要说破,留小的过夜。小的道他好意,哪知他竟要杀我灭口。小的偶尔腹痛,走到外边出恭,听见隔墙有谋害杀死我的议论,便越墙逃出。特来上告!”
知府道:“这指挥使张寅,果是李福达改名的吗?你不要撒谎!”
薛良道:“小的如果认得不真,怎敢谎告!”
知府一想:这李福达是个叛逆重犯,未见捉获,现在改名易姓,逃在此地为官,既然有人检举,一定不会是假的,看来必须速速将他抓获才好。于是,就连夜去禀告专门管官员的都院。都院闻知,便传令中军,带领兵士,协同知府、知县捉拿李福达。
再说李福达的两个家人,三更左右进入书房,却找不见薛良,忙禀报李福达。李福达知道薛良逃走了,大惊失色,心里惴惴不安,不能安眠,忽然听到外边有人马嘶叫喧嚷的声音,又听到敲门的声音非常急切,便叫家人开门,只见中军兵士和府县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一拥而入。
后面走进两位官员,一见李福达,喝声:“拿下!”
李福达辩解道:“我无罪!为什么捉拿我?”
知府道:“你是李福达!现有薛良检举,还有什么辩解的!”
李福达见事情败露,只好俯首就缚。
知府将李福达在太原的家属都锁押起来,查盘资产,封锁门户,然后一面着地方看守,一面带了人犯,同众官回衙审究。
在审讯中,薛良与李福达当面对质,薛良说得凿凿有据。薛良自称是李福达的老乡,他指控太原卫指挥使张寅就是正德七年(1512年)在陕西洛川谋逆劫掠的头领李午,而李午就是在代州崞县传播邪教的李福达。他还找来了李福达的两个旧相识--李景全、韩良相做证人。李福达见难以掩饰,只得承认。
太原都院、知府、知县见李福达招供,也不动刑,将他监禁在狱中,禀复上司,请旨定夺,然后移文京师,捉拿李福达的三个儿子。
当时太原人都风传:“如今这世道,有了钱,强盗也做得官了!”
这时正在京师郭勋家中炼金银丹药的李福达的三个儿子大仁、大义、大礼听说父亲李福达被捕,忙聚到一起商议对策。想来想去,也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只好求郭勋出面说情。
三人一同求见郭勋,长跪不起,涕泪交流。
郭勋见三个内兄弟跪在地上,当即答应帮助他们说情。
案子当时转到了山西按察使徐文华手里。徐文华详细盘问,还着令召来李福达的亲家杜文柱、同族李俊来辨认。两个证人均认定这个张寅就是李福达,李福达本人却又突然矢口否认,对指控他在陕西洛川谋逆等罪名一概不承认,坚持说自己就是山西徐沟县乡绅“张寅”,根本不知道什么邪教教主“李福达”。
徐文华毫不理会李福达的辩解,采信了证人所言,认定张寅就是李福达,就此定案,并将案件审理情况报告给了布政使李璋和巡按御史张英。
李璋、张英见此案证据确凿,审理程序严密,没有提出异议,打算按报结案。
正在此时,徐文华被提拔进了京师,做了大理寺右少卿。而顶替他的山西按察使李钰为显示新官上任之力度,决定联手山西巡抚毕昭重新审理此案。
就在这种情况下,郭勋寄书山西巡抚毕昭,教他释放李福达。毕昭是一个非常会奉承权势的人,见郭勋有书来托,反要将薛良问成诬告之罪。
在提审时,李福达仍一口咬定自己是被薛良等人诬告,还拿出徐沟县同戈镇的《张氏宗谱》作证,上面明明写着张寅的名字。而且,当初薛良来举报李福达时,称李福达身上文有龙虎形状,而现场经过认真查看,张寅身上并没有所谓的文身。
就这样经过查勘论证,最后认定张寅是被薛良诬告,应判决张寅无罪释放,薛良因诬告他人,流放边境。
只是,判决还没执行,毕昭就退休了。此案又悬而未决,搁置下来。
案子审审停停,拖了三年。
2 马巡按铁面无私定铁案武定侯书信讲情受牵连
既然巡抚毕昭大人已经认定张寅是被薛良诬告,为什么久久不肯结案执法?嘉靖五年(1526年)五月,新任山西巡按御史马录上任,对此案心生疑窦。马录为人正直,不肯攀附权贵,也不贪图钱财。“难道毕昭大人送了人情,然后又怕牵连到自己,故而不肯结案?不管是不是这样,我定要重新审理这个经年积案,将此案弄个水落石出!”
马录一向严谨务实,他在反复翻阅案件卷宗的基础上,做了决定。
“我应该先前往山西徐沟县微服私访,那里是张寅待过的地方,也许能够找到答案。”
“常大人,张寅可是李福达?”马录在徐沟县咨询乡绅、给事中常泰。
“张寅正是李福达!”常泰果断地说。
“张寅就是李福达!”接着,马录又前往代州,走访了谳狱郎中刘仕。刘仕是老代州人,对乡情掌故知之甚详,他也认定张寅、李福达为一人。
马录还派人到陕西洛川调查取证,访问当地乡民,得到了同样的答案。
同时,他又派人赴代州、洛川寻找认识李福达的老人,请他们到庭审大堂听张寅的口音,进行辨别。
接着,马录又命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钰、佥事章纶、都指挥使马豸反复审讯李福达,使他在公堂对簿时再不能翻供。
经过一番努力,所有审案记录、证词、口供等案卷都汇集马录处,所有的证据证言都证明:被拘的“张寅”就是洛川的“李午”,也就是崞县的“李福达”。
“武定侯郭勋差人前来下书!”案情刚刚确定,马录正准备上奏将李福达正法时,忽然有一天,巡捕官前来禀报。
衙门规矩,一应封口书函,不许投进,武定侯投来书信,不会是有所嘱托,想徇私舞弊吧?马录心中暗想。
“请按衙门规矩当堂宣读武定侯郭勋的来信!”马录吩咐武定侯的差官。
差官一听,大惊失色。
马录并不管顾那差官的反应,拆开书信一看,果然不出所料,郭勋在书信中为李福达开脱。信中说:
马大人:
本官与张寅是至亲好友。薛良本是乡中一无赖,此案是因他嫉妒张寅富贵而前往官府诬告。祈望马大人能明断是非,手下留情。
随信寄来礼品,望笑纳。
武定侯郭勋
“好一个武定侯,身为国戚大臣,居然为聚众谋反的大盗说情,难道王法都不要了吗?”马录看后,勃然大怒,冲差官呵斥道。
“马大人!王法固然重要,只怕私情也是重要的。”郭勋派来的差官自恃是侯府家人,并不慌张。
“你是何等贱人,敢如此讲话!来人哪,拉下去,重打二十大板!”马录吩咐道。
“只怕打不得。”差官连忙回道。
“先打了再讲!”马录喝道。
“小官自知冒犯大人,求您看在我家侯爷面上饶了我吧!”左右一声吆喝,拖下差官便打,打过二十板之后,差官忍受不住疼痛,苦苦哀求道。
“看在你家主人面上,再打二十大板!”
“大人,小人再不敢了,求您饶了我吧!”这样,差官一共挨了四十大板,直打得皮开肉绽,哭爹叫娘。
“这四十大板,让你知道我巡按衙门的规矩。回去回报你家主人,叫他小心行事!”马录吩咐将差官放出。
差官受了刑罚,失尽尊严,抱头鼠窜而去。
马录依然判“张寅谋反,妻子连坐”,同时禀奏山西巡抚江潮。
江潮的性格也很秉直,对于郭勋的所为也很不齿。
“对李福达应处以死刑,对郭勋也应进行惩戒。你我二人应联名上奏朝廷,并附上郭勋写来的密信。”江潮和马录联名在奏章上写道:
启奏陛下:
李福达曾经召集教徒数千人,杀人很多,虽然隐姓埋名、销声匿迹,还是暴露了。他的相貌并没有多大改变,就是将他处死,也尚有余辜。
武定侯郭勋私下结交叛党,还无所顾忌地替李福达开脱罪责。纵使郭勋不知道李福达过去反叛的事情,而他包庇叛逆,不知避讳,还是应该给予惩罚警戒。
山西巡按马录、巡抚江潮
嘉靖接到马录和江潮的奏报,立即将奏章交给了负责纠察官员的都察院处理。
都察院的御使们接了谕旨,不敢怠慢,尽快调阅了有关卷宗与档案,核对相关物证,提审证人,又认真核对了郭勋的笔迹,审查的结果与马录所奏一样,就上奏皇帝:马录对李福达的判决适当,同意判决。
嘉靖当即批示:
李福达及其儿子处斩,妻女配给功臣为奴,财产由官府没收。
这时,李福达一案似乎已经是铁案如山,任由郭勋有通天手段也难以翻案了。
事后,嘉靖对郭勋的做法也感到很生气,就召见郭勋并当面斥责了他,声色俱厉地要求郭勋向都察院说明自己结交李福达的缘由,否则就以通敌罪严惩。
郭勋惊恐万分,立即上疏报告自己认识李福达的经过,请求嘉靖开恩,并替李福达说好话,开脱罪责。
其实,当时郭勋是嘉靖朝权倾一时的重臣,这是因为,嘉靖皇帝是弟继兄位,不是父子相承,嘉靖皇帝初即帝位时,要把自己的亲生父母加封皇帝皇后的尊号,群臣听后都不同意,只有郭勋、桂萼、张璁等人支持嘉靖皇帝的主张,与群臣为敌。嘉靖五年(1526年)秋冬之际,护法派大员杨廷和、蒋冕、毛纪等相继离朝,九卿及中下层朝官经过左顺门的大规模廷杖和随之而来的逮治、流配,也变得噤若寒蝉。而郭勋、桂萼、张璁三人则从此平步青云,深受嘉靖宠信,权倾一时。
嘉靖想起郭勋的拥立和侍卫之劳,加上李福达在审讯中也替郭勋开脱罪责,也就不再追究他了。
郭勋缓过了一口气,紧接着便开始积极地私下运作,准备为岳父李福达翻案。因为只有推翻此案,才能恢复嘉靖对自己的信任。郭勋为了彻底洗净自己身上的污点,又唆使李福达的儿子李大义到刑部去击鼓鸣冤,递交诉状,请求为父雪冤。
这样,案子又回到了都察院,左都御史聂贤和原审判官高世魁都知道郭勋是李大义的幕后指使者,便将李大义的状纸搁置一边不问。
郭勋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对李大仁说:“如果这招不能救出你父亲,你就先逃吧。免得被他们抓住白白送死。”
这些话传出之后,大臣们都非常生气:作为朝廷的重臣,郭勋不但与罪犯来往,还为谋逆国家的重犯亲属出谋划策,这无疑是通敌叛国。于是,大臣们纷纷上奏弹劾郭勋。
有的道:“李福达杀人如麻,潜踪匿形。今罪行暴露,就是被处以极刑,尚有余辜。武定侯替他开脱,也应该法办。”
有的道:“郭勋暗通逆贼,明受贿赂。李福达就是处死伏法了,也不能轻赦郭勋。”
其后参劾郭勋的,一本凶似一本,竟说他党护叛逆,心怀叵测,要给他坐上谋反的罪名,非灭族不可蔽辜。
给事中王科、郑一鹏、程辂、刘琦、郑自璧、赵廷瑞、沈汉、秦祐、张逵、陈皋谟,御史程启充、卢琼、邵豳、高世魁、任淳,南京御史姚鸣凤、潘壮、戚雄、王献,评事杜鸾,刑部郎中刘仕,主事唐枢等纷纷上疏,弹劾郭勋,请求将他连坐治罪。
常泰、聂贤等上言称郭勋应以知情故纵论罪,依法律当连坐治罪。
生命攸关之际,郭勋不得不反复上疏替自己开脱,说自己是由于支持议礼而触犯众怒的。嘉靖对郭勋的说法深信不疑,对谏官群起而攻郭勋之事似乎也恍然大悟,于是,就命令锦衣卫取李福达供词及人证,将李福达一案移交至锦衣卫镇抚司等候会审。
这时,谏官们都感觉到了嘉靖的犹豫反复,情急之下,一个个更是激切上疏,弹劾郭勋,陈说李福达的罪名,要求依律惩处。
嘉靖帝接二连三接到群臣弹劾郭勋的奏疏,也下旨严厉斥责了郭勋,警告他要奉公守法,不要亵渎了自己的勋爵。
官员们见皇帝对郭勋只是斥责,而没有把郭勋移交给司法机关,认为是嘉靖有意偏袒,更加频繁地上疏,言辞也更加犀利。甚至有人还指出郭勋的其他罪行,如郭勋曾侵吞军饷数万两白银,私自占用军匠等。这些弹劾奏疏如雪片般飞来,从四月到年底,几乎日日不断,可以说对于郭勋的攻击铺天盖地。郭勋成了众矢之的,到了没有退路的境地,他不得不一次次上疏辩解。
3 议大礼郭勋张桂结同党为自保借刀杀人定阴谋
“如今自己惹火上身,骑虎难下,这该如何是好?与其担惊受怕,不如谋求同党的支持。”郭勋如坐针毡,“当今之计,我一方面要上疏为自己解释开脱,一方面要寻求张璁、桂萼二人的帮助。如今张璁、桂萼是皇上的心腹宠臣,而他们和我同是当年支持皇上的议礼派,他们又受过我的帮助和提携,应该不会像马录那样再一次使我陷入难堪。”
这时,郭勋不由得想起了当年的大礼议之争,想起了他和张璁、桂萼一同支持嘉靖皇帝的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