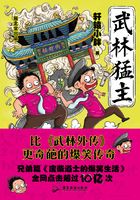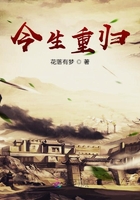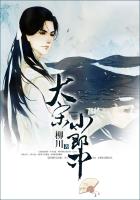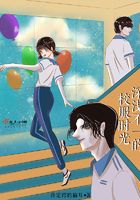“如果依了他们的主张,将所谓的法度摆在我皇权之上,那我大明皇帝的权威还往哪里摆?天下是我的天下,臣民是我的臣民;我要谁生,谁就能生;我要谁死,谁就不能活!”想到这里,嘉靖皇帝顺手把这份不识时务的奏本扔进了炼丹炉中,然后召司礼监掌印太监传旨,将陆粲、刘希简一起革职下狱,并明确表示,刑部官吏互相偏袒,魏应召的审判必须推翻。
因为怕自己的本意再妄遭揣测反驳,嘉靖皇帝命令将他的这份圣旨先发到东厂,由东厂的李青亲自送到刑部督审,并由李青指定一名刑部侍郎亲自主持复审。
这下,看哪个胆大的奴才还敢故意歪曲我的本意!嘉靖恨恨地思忖着。他突然发现炉火已经不旺,赶紧续炭,并用力地扇起来。
5 逞皇威三道圣旨铸冤案顺权势不畏人言畏昏君
“听说为了张孙氏被杀一案,皇上十天内连降三道圣旨,把刑部魏应召、陆粲和刘希简三位大人下狱,还把都察院右都御史熊浃大人给免职了!”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京师。
“魏应召、熊浃、陆粲、刘希简这几位大人可都是青天大老爷呀。如果三法司里的官员都像这几位大人那样不避斧钺,咱老百姓就有指望了。”酒肆茶楼之内,街谈巷议之中,老百姓无不称赞魏应召、熊浃、陆粲和刘希简。
京师的一些商户及士绅,还派人给被囚的三位主审官送酒菜,以示慰问。右都御史熊浃解职在家,每天都有人来拜望,为避嫌疑,熊浃一概不予接见。
京师上下都眼巴巴地盼着刑部的最后审理结果。
第四次复审的主审官是刑部侍郎许赞。刑部侍郎是刑部副长官,从二品。许赞出身官僚世家,他的父亲吏部尚书许进曾因为不肯攀附大宦官刘瑾而被免职,许赞也因此被逐出了翰林院。刘瑾倒台后,许赞才得以复出。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当他从大名府推官、御史、编修、临淄知县、江佥事、光禄寺卿升任刑部侍郎后,他非常珍惜自己的功名前途。虽然他骨子里尊重法律,有一种正义感,但在封建皇权制度下,特别是在昏君嘉靖的领导下,任何正直的大臣都不得不变节以适应封建专制制度,所以,他一直默默地谋政。据说在审理各种案件时,许侍郎从来不多开口,因此他颇有一种语迟威重的风度,而刑部上下的官员,提起许侍郎来,也总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感觉。听不见人说他的坏话,但也看不见他做出哪一件业绩。
当刑部把圣旨发到许赞头上时,他犹疑了一下,还是顺从地接了。
跟着,许赞组织了一个二十余人的复审机构,并于当天就把案卷从都察院调回了刑部。显然,许赞组织这么大的复审机构,是想把将来复审的判决责任推给大家共担。
第二天,张福和张柱、张秀萍都被传到了刑部,而且被监禁了起来。
接着,东厂贴刑李青奉旨督促刑部速速按圣意复审,但李青到刑部去了三次,都被许赞派人挡了驾。
从许赞的表现来看,他似乎是想为张柱翻案。因为如果要维持最初的原判,他何必要挡李青的驾呢?人们纷纷猜度着复审的结果。
转眼间十天过去了,但刑部仍然没有结案。
据说许赞已经派出二十多个人去什刹海一带察访,已经得到了新的证据,但审判结果如何,没有人能猜透。
其实,许赞早已将复审的奏章写好,他之所以迟迟没有上报,是为了仔细观察一下京师百姓的态度。
从许赞的一生来看,他虽然为人比较正直,能主持公道,但他的父亲和他因正直吃过大亏,他已经变得非常保守。
现在,案子一方是张福背后的东厂和嘉靖皇帝,一方是张柱背后的民心。他虽然暗中同情魏应召、熊浃、陆粲和刘希简,但他绝对不会再干那种傻事。
在接到圣旨的那天,许赞已经意识到,这个案子不按嘉靖皇帝的旨意办根本不行。如果自己违背嘉靖皇帝的旨意,魏应召、熊浃、陆粲和刘希简的下场就是自己的下场。好不容易重新混到刑部侍郎的从二品职位,许赞可不想因此而重新被拍下去。他深知,要想不断升迁,既不能得罪皇帝,也不能得罪东厂和锦衣卫。
与民心相比,皇帝和东厂的权势更厉害。他已经把案子压了十几天,对于民间的议论也听够了。尽管知道民间的舆论都是同情张柱和张秀萍,而对东厂怨声载道,但他知道,顺从了皇帝,无非在百姓中落个执法不公的名声,他认为那是自己要在官场中生存、晋升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皇权远远大于法制,东厂大于刑部,要保住自己的职衔,只能百分之百地照嘉靖皇帝的旨意办事。
打定主意后,许赞在九月初一公开升堂审理了张孙氏被杀案。
刑部衙门外挤满了老百姓,他们不但关心张柱和张秀萍的命运,更关心魏应召、熊浃、陆粲和刘希简的命运。张母、许夫人都已经到场,迫切等待复审的结果。
为了避免场面混乱,许赞只准二十一名复审官员进入大堂,而没有传唤三班衙役和刑部书吏。审判过程很简单,许赞叫一个,大牢内押出一个,上堂来并不问讯,主审官许赞直接宣读以下判决:
四冰果商贩张柱杀死张孙氏,斩立决。
张孙氏之子张福被无辜收监,赏银五两当堂释放。
张福之妹张秀萍与凶犯张柱关系暧昧,诬陷其兄,杖责一百,逐出京师。
刑部郎中魏应召受贿枉法,即刻发往云南充军。
张柱的邻人李真、王云乱作伪证,与魏应召一道充军。
审判榜文贴出,京师上下哗然。
可怜无辜的张柱成了皇权与法制斗争、正义与邪恶斗争的牺牲品,他怀着满腔冤屈,怀着对张秀萍、魏应召、熊浃、陆粲和刘希简的感激,怀着未能尽孝的遗恨,怀着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巨大仇恨,于当天被押赴刑场处斩。他的人头落地之时,也是人们对法制精神绝望之时。
看到无辜的儿子人头落地,张母悲愤难忍,她将儿子收拾埋葬后,于当天夜间跳进了护城河。这个柔弱的苦命的老太太,以她的死来控诉这个权势大于法制的黑暗专制社会。
纤弱的女子张秀萍被杖责后,带着遍体鳞伤和满腹屈辱悬梁而死。大义灭亲者不但未得到赞扬,反而做了维护皇权的牺牲品。
然而,老百姓有他们自己的审判,人们感念张秀萍的大义,将她的尸身与张柱合葬在一起,这对被东厂和封建制度摧残致死的善良男女,到九泉之下终于能有个终身伴侣了。人们想以此来安慰他们屈死的亡魂。
一场令人瞩目的官司,以嘉靖皇帝、东厂和张福的完全胜利结束了。
除了张福、李青和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嘉靖皇帝,当时京师的上下人等,人人都说这是一个大冤案。
张柱等人的鲜血,保住了嘉靖皇帝和东厂的权威,也保住了刑部侍郎许赞的乌纱。然而,主持正义的魏应召被流放,熊浃被革职家居十年,陆粲、刘希简被廷杖下狱。陆粲后来谪贵州都镇驿丞,迁永新知县后,因思念母亲请求归家。母亲死后,丧期还未满,陆粲就郁郁而终。刘希简也被贬为县丞。这样忠孝正义的官员落得如此下场,不能不让人感叹。
明知张柱冤枉的嘉靖皇帝在接到刑部送来的张柱已按律处斩的报帖后,假装同情地说了声:“可惜了二十多岁的年纪。”然后就又坐到八卦炉前炼他的仙丹去了。
此时,正是秋风萧瑟,落叶飘零之际,魏应召和夫人满腔悲愤地辞别那些前来为他们送行的同僚和百姓,然后向大家深施一礼,拭干挂在眼角的泪珠,大踏步顺着两旁长满荒草的小径向前走去。
“当今皇上心胸狭窄、刚愎自用,一心一意要处死张柱,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一切审讯推勘,都只能是这种专制意志的文书化而已。”魏应召向夫人感慨。
“老爷,你现在后悔吗?”
“不后悔!”
“我看当今皇上是假信神。”许氏说。
“何出此言?”魏应召问。
“信神的人本该相信因果报应。然而,从皇上的作为来看,他骨子里根本不相信因果报应,只相信皇权高于一切。”许氏说。
“这就是当皇帝的好处,凌驾于一切之上。所谓的仁义道德无非都是给臣民上的紧箍咒。”魏应召感叹,“夫子的理论并不能制约皇上,反而为虎作伥!”
“当今还有比夫子的思想更好的思想吗?”
“应该让法律高于一切!皇权也应受法律的制约。”魏应召振振有词地盯着远方说。
“老爷你这是痴人说梦,如果皇权受到法律的制约,那还叫皇上吗?我看皇上炼丹只是为了自己能够长生不老,好继续享受当皇帝的好处。”许氏感慨。
魏应召陷入了沉默。
而那些前来送行的官员和百姓们望着魏应召夫妇远去的背影,无不默默地向苍天发问:这样的天,何时是个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