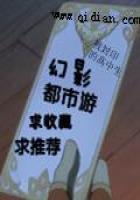他那哭声好大哟,从办公室门口传到了走廊上。把其他办公室的干事们、科长们,差不多都引了出来,汇集到了这干部科办公室的门外边。
这些个平常在安静的办公室内工作惯了的干部们,一时被打破了安静,就七嘴八舌地发出了嘈杂的询问声:“谁呀,哭得这么伤心?”“哟,这不是市公安局的尤副局长吗?他是遇到什么太为难的事情了?”“可不是他还是谁?尤大秀才是遇到什么难缠的兵了吧?”“手握大权的公安部门头头,谁敢欺负他呀?”“……”
程长泰不去理会门外的议论,把尤经纶扶到了椅子上,递上一条毛巾,低声对“悲痛欲绝”的老尤说:“哎,哎。尤局长,尤局长,别激动,别激动,有什么话你就说。别哭,别哭,大家都来看笑话哩。”
“看笑话,有什么笑话好看的!”右手接过毛巾,尤经纶的脸阴得快晴得也快。他放下捂脸的左手,那双从不与人对视的乜斜眼里,一滴眼泪也不见。捂脸的手上,干燥得要发裂。苦瓜也似的尖脸上,一滴水都没有。见此形状,门口的多数人都摇头嬉笑地散去。还有几个不愿离去的“好事之徒”没有挪动脚步。看那架势,硬是要待出一个结果来不可。尤某人也顾他们不得了,抬头不直视程科长:“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呀,我这个局……啊,我这个副局长还怎么当呀?”
程科长试探着问:“怎么,你与舒局长闹意见了?”
尤经纶的尖削脑壳一摇,嗫嚅地说:“不是。我们两个的关系好着哩。”
他与局长舒成铭“亲密无间”的关系,市委组织部干部科长当然是清楚的。程长泰随后又问他:“那是,和局里其他的哪位领导同志有点不协调了?”
尤经纶的乜斜眼一阵眨动。他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当众说起了谎话:“也不是。我们局党委常委如今的一班人,都紧密地团结在舒成铭同志的周围,就像是一个人一样!”
不是和同事闹矛盾,程长泰疑疑惑惑地接着问他:“那,是与你的夫人……”
尤经纶苦瓜脸一整,提高了一点声音说:“哎,看你程科长猜到哪里去了。我们老两口结婚这么些年,关系一直好得很,还从来没有红过脸,更没有吵过架。这么说吧,我和老伴可以够得上是相敬如宾、举案齐眉!”
一时间,程长泰好像是堕入了五里雾中,他用手搔了搔头发,说:“那——,是谁敢到太岁头上动土,把你这位博学多才、满腹经纶的大笔杆子、大局长给气成了这个样子呀?”
“文人”局长不文明,口中却带起了渣子:“妈的。我找下面的一个科长谈话,他说和我只有工作关系不肯和我谈,还甩门而去。我随后挂电话他,妈的,他在电话里边更是劈头盖脸、连讥带损地把我撸了一大通。不等我答一句话,妈的,他就把电话给甩了。程科长你给说说,我这个局长,啊……,我这个副局长,还怎么当呀?”说到此处,他似乎又要哭了,嗓子硬硬的,嘴巴扯了两下,再补上一句,“没办法,我,我才找到干部的娘家来。”
听到这儿,脑子灵光又了解不少情况的干部科长,已经猜到了可能是怎么一回事。进而又猜到了如此大胆,敢把直接的顶头上司给顶撞得气急败坏地跑到市委组织部来哭鼻子告状的人是谁了。然而程长泰却又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揣测,便试探着问道:“尤局长,你说的是钟子忱同志吧?”
尤经纶也不怕旁边的人耻笑,竟然大言不惭地大声说:“不是他那个本事不大、傲气不小的钟子忱,在我们公安局还会有哪一个?我老尤工作了好几十年,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像他小子那样目无尊长、顶撞领导的下级。他还当是运动期间啦,还敢那么嚣张地对抗领导!”
程长泰不禁在心里边暗笑,“嗨,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告下面状的。”可他嘴里却问道:“这件事情,舒局长知道吗?”
尤经纶忽然有点嗫嚅地回答:“我,我在来市委之前,找、找过他。”
程长泰接着又问:“对于这一件事情,他又是什么态度呢?”
尤经纶似乎又有点儿起火了,又大声说:“他呀,还不是欺软怕硬不敢去碰那杆红缨枪,就叫我去找姓钟的谈。人家那样地羞辱我,他还要我再忍、再让。啊——,对了,我到市委来反映情况也是他的意见。”
程长泰点了点头,又问:“尤局长,今天到部里来要我们做点什么事呢?”
尤经纶尖削脑袋一昂,乜斜眼一瞪:“找部里讨一个公道哇!”
程长泰心中不耻,脸上仍微笑着说:“讨公道?尤局长,话可不能这么说吧?对于这位钟子忱同志,部领导、市领导同志都并不陌生,我更是有所了解。他可是个一贯表现很好,事业心很强的好同志,待人接物也通情达理。1963年树他为全市十位优秀青年之一的材料,还是我到你们市局了解、收集并整理的。他在运动中的表现,更是有目共睹、早有公论,也不是一两个人可以肯定,一两句话就可以否定的。”
这时候,老尤低哼了一声,老程停了下来等他说话。可是对方并没有开口,接着把自己要说的话说下去:“作为市公安局的老同志、老领导,在运动中又是同一个观点的。在一起几十年了,尤局长你对他小钟应该比别的同志更多一些了解。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有点把矛盾,有些意见不大一致,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时一事的不协调,就全盘地否定一个人啊。你来反映的问题,不管我有什么看法,我都会如实地向部领导汇报。必要的时候,我还会向书记们汇报。我不能,也无权堵塞领导的言路。至于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呢,只不过是供你尤局长参考参考。”
话不投机半句多。尤经纶立即起身往外就走,口中并未停:“我不跟你这个不分是非曲直的干部科长多费口舌。哼,我找部长去,我找市委书记去!”
尤副局长到市委告预审科长的状无果而归,倒把笑料丢到了本市的最高领导机关。他像阿Q般咬牙切齿地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妈的,总有一天你姓钟的……”
那一天,老尤终于等到机会了。额外加到预审科的劳动教养案件审批工作,出了一点子纰漏。处理得不好,就有可能要“闹出人命”来。
“丁零零、丁零零……!”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了,市公安局第七科内勤办公室的电话铃声相当刺耳。让默默庆幸即将平安地过去了一天的干警们,不由得有点儿不太妙的感觉。那电话是从三十里外的桐子岭区劲川煤机厂保卫科挂进来的,说的是:该厂青年工人盛夏,管不住他那个水性杨花的老婆韩春。他多次请求厂保卫科和派出所,对她进行管教。可是,她屡教不改。从她所在的班组到车间,该谈话的都谈了,学习班也办了几次,还治安拘留过两回。每回放回去过不了几天她又旧病复发,已是无药可救了。前些时,盛夏又强烈地要求政府,把自己实在管不住的老婆收去严加管教。最近,市公安局的局长们集体审批劳教案件,决定送韩春劳动教养三年。可是,当派出所民警会同厂保卫科干部于下午两点钟去带人时,盛夏却反悔不干了。他甚至跑进厨房操起菜刀,将民警和保卫干部们赶出门外,把自己和老婆反锁在屋子里。他还手舞着菜刀大喊大叫:“哪个要进来把我老婆捉走,我就和他拼了!”
双方在屋里、门外相持了两个来小时,盛夏一点儿道理都听不进去。他翻来覆去地大叫大喊:“谁也莫想进来带走我的老婆。哪个要是破门进来,我就和他同归于尽!”
他一边大喊大叫,还一边把菜刀往窗台上拍得“啪啪”直响,弄得民警和保卫员们哭笑不得,把他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他们只好向市公安局报告、求助了。经过了一番电话往返折腾,直到下班之前几十分钟才打进了市公安局七科,找到了劳教案件审批组的李定组长。
这位老李原在劲川中学读书,初中毕业后进桐子岭煤机厂当车工学徒,次年被提拔到厂保卫科当干部。1966年全国性大动乱的前二年,开展“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劲川市被中共雅峰省委定为全省的“四清”运动试点城市。作为要害部门之一的市公安局,肯定是清理的重点单位。一些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或者个人历史不是很“清”的干警,被确定分期分批地调离出去。同时,再从基层单位的保卫部门抽调一些政治条件比较好的同志进来补充干警队伍。于是,李定有幸被调到了市局一科,他小“猴哥”的诨名也变成为“猴子李”。在公安业务方面,老李不算很冒尖。而在运动场上,他倒是一把好手。尤其铁警五项,是他的强项。手枪射击,他更是勇冠全局。因此,在他“猴子李”的诨名前边又被加上了“神枪”两个字,他诨名的全称就成了“神枪猴子李”。大动乱时期他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没有少受皮肉之苦,但他始终有一脸的不笑也像在笑的“猴笑”。
学弟钟子忱升任“典狱长”,把他和张安带到了七科。对那种给别人断后,炒现饭、热现菜、擦屁股、补漏洞的活儿,他从心里头腻歪,脸上还是不脱“猴笑”。到了七科,按资格,凭本事,李定当上了一名劳教案件审批组的组长。可是,他旗下没有一兵一卒,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有了案件依法自己一个人不能办,就请预审办案组的哥儿们来伸一把手。尤其是学弟张安的第二办案组,从张组长到众组员都快成为他老李的“猴兵”了。
此时,接过了桐子岭煤机厂保卫科打来的紧急电话,李定就赶紧向学弟钟科头报告。钟子忱就叫他向局汽车队要汽车,还叫上正准备下班走人的张安连夜赶去处理。
李“猴哥”几经周折挂通了电话,好不容易找到了局汽车队那位满脸星星闪白光的邴望兴队长。老小子听老李一说是请他给派车子,他当时就回道:“什么什么,你们七科也、也——要用小车子?我老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更没有派过。预审科长出去就要坐专车,只怕局里没有这个规矩吧。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这个车子,我老邴可不能派。凡是不符合原则的事情,我邴望兴从来都不干!”
老李一听,“猴火”直冒。他“咚咚咚”一路小跑冲进钟科头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如此这般地一说。脾气同样火爆的钟子忱一听,就大吼起来:“好你个只值角把钱的街标灯,你老小子公报私仇哇!”
原来,省里领导不支持把已经终审的邴迎玉案件翻过去,钟某人就坚决把邴迎玉送去劳动教养三年。她不服,向省劳教办公室申诉,钟某人又坚决予以驳回不给她取消劳动教养的决定。邴望兴老小子对此一直怀恨在心,时刻窥伺着报复钟某人的机会。这一次,预审科“求”到了汽车队即邴望兴的头上,正是他拿钟某人报复出气的机会。
钟子忱越想越来气,他双眼一瞪,朝着李定、张安老哥俩狠劲一挥手:“走,我们骑自行车去。不就是三十来里路吗?把车子踩快点,个把小时就到了。”
老钟领着哥俩,一边往楼下去一边朝内勤办公室大声吩咐道:“为群同志,你给劲川煤机厂保卫科或者桐子岭正街派出所再挂一个电话去,请他们无论如何再坚持个把小时。再特别强调一次千万不要激化矛盾,更不要强行砸门、破窗冲进屋。一定要等我们赶到之后,再商量处理的办法。”吩咐完了,他还没有停嘴,气呼呼地说:“汽车队那条只值角把钱的老狗,哼,回头老子再找他算账!”
钟子忱说话声音大,根本不打算保什么密,不怕别人听了去。走廊当头竖着那一盏讨厌又可怜的“探照灯”,他连看都没有看一眼。
一路之上,他心里边直窜火,精力不大集中。三个人相跟着,他打头。大约行了十来里路,在过一道铁路与公路的交岔口的时候,那车子的前轮却给心中气愤难平的老钟添起了麻烦。趁他分神没有掌握好龙头的当儿,那车轮子“趁机”打了一下滑滑到了钢轨和副轨之间。只听见,自行车“咣——当!”一家伙,把钟子忱给摔了一个四肢抢抱地球亲!他趴在地上,好一会儿动弹不得。李定、张安跳下车来,避免了连环撞到一块。他俩跑上前去,一左一右地将钟子忱搀了起来。“啊哟,不好。”突然,机警的猴子李大喊,“上边来汽车了!”
老哥俩赶紧把老钟往路边抬,弥勒张的脚下一滑,“咕咚”三个人一起跌到了干沟里。差不多在这同时,一辆卡车从老钟刚才卧倒的地方“呼”地直冲而过。下边很快传过来“嘣”的一声响,那躺倒在路上自行车后轮,被卡车扎了一个正着!
把老钟扶到路上,老李和老张扶起各自的车子。张安口齿不大清楚地问李安:“谁带黑哥哥?”
骑车技术略胜一筹的小猴哥当仁不让:“当然由我老李带了。”
摔着地时,老钟的双手掌和面部的额头、鼻子、双颧等突出的部位,分别被沥青路面“啃”去了一层薄皮,当时只觉得麻木,这时候疼痛刺激大脑,骂声也跟着出了口:“哎——哟。狗日的只值角把钱的邴老狗,你等着,老子跟你没完!”
他丝毫不去检讨自己没有抓好自行车把的过失,把责任全部算到了并不在跟前的局汽车队长的身上。气归气,骂归骂,都解决不了眼前的实际问题。剩下的20来里夜路,还得往前赶去。沿途的坑坑洼洼,没让摸黑赶夜路的老兄弟们少吃苦头、多添气恼!老兄弟们好不容易赶到了桐子岭煤机厂职工宿舍区,这时天早就黢黑了。没有吃晚饭,也都不觉得太饿。尤其是钟子忱,一肚皮填满了气更是鼓鼓的。他们一到把自行车一架,就立即站到了盛家门外的路灯下边。回到“娘家”来的“猴子李”,也顾不得与“娘家人”亲热寒暄。不过,他不笑也像笑的“猴笑”常年都给人以亲切的感觉。此刻他心里头发急,脸面上竟然还是“笑容”依旧。
等来了“援兵”的保卫干部,立即大声朝门里喊了起来:“小盛啦,市劳教办公室的钟主任他们三个人来了。你打开门让人家进去,有什么话你就对他们说嘛!”
一听此言,门里的盛夏再也没有边拍菜刀边扬言要拼命了。不过,门仍然没有打开,钟子忱只好上前一步去。隔着门大声说:“小盛同志,根据你自己的要求,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经过了认真研究,才决定送她去劳动教养。目的是促使她改邪归正,回来之后不再到处乱跑乱搞和你好好的过日子。到了劳教单位之后,只要她接受教育、痛改前非,确实有了进步,我们还可以根据劳教单位介绍的情况,酌情给她适当地减期。”
门里的盛夏急忙问道:“真的可以减期?”
老钟大声回答:“我说话算话。小盛,有什么问题,你随时可以到市劳教办找我。”
“哪个晓得你们市劳教办大机关的门是朝东还是朝西哟?”盛夏连说带问。
老钟告诉他:“就在市看守所里面。看守所在什么地方,你该晓得吧?”
“我晓得。”小盛又问道,“到看守所,我去找哪一个呀?”
老钟一字一顿地大声说:“就找我钟、子、忱。”
这时候,盛夏提高了声音,问的却是与他老婆送劳教的事不相关的题外话:“你叫钟子忱呀?是那年在人民广场开十万人大会,控诉林彪、四人帮的那个钟子忱吗?”
钟子忱心中一惊,一位普通工人竟然还记得自己在几年前大会上的发言,他很受感动,连忙说:“啊,是的,是的。我就是那一年在广场大会上发言的钟子忱!”
盛夏接着问:“你这个钟子忱,我可以相信你。你现在说的话,真的算得了数?”
“当然算数!”钟子忱提高了声音,有点像是对他发誓似的说道。接着,他又放缓声音说,“听你说话的口音,是离劲台县城不远的人吧。我的老家就在城关,我们两个人还是个真同乡呢。你小盛让同乡吃了这么久的闭门羹,太有点儿不够意思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