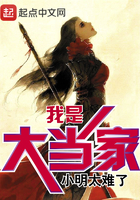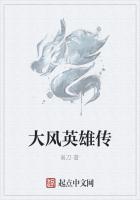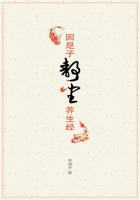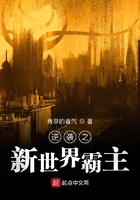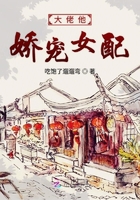1980年,秦安大地湾遗址在一期文化遗存的发掘中,共清理出完整的和复原的陶器生活用具120余件,其中彩绘的约有三分之一。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些彩绘陶片。彩绘绝大多数是紫红色,比陶土色略深一些,但不甚醒目(红色彩绘仅发现了一片,系红色矿物颜料绘于陶器内壁,是陶烧制后绘上去的)。这批出土陶器的图案以钵形器口沿外一圈宽为2~4厘米的宽带纹和口沿内一圈细线纹最为常见。
在出土的20多件钵形器和部分陶片的内壁上,考古工作者发现有10余种不同纹样的彩绘符号。这些纹样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类似水波状和类似生长植物状的纹饰,水波状的纹饰具有一定的连续性,类似生长植物状的纹饰连续性不强,但都属于装饰性的图案花纹;另一类是以直线或曲线并列或相交而成的彩绘纹样,无连续性。无独有偶,考古工作者后来又在大地湾仰韶早期钵形器口沿外的宽带纹上发现了10多种均单独使用的刻画符号。专家推测,一期彩绘符号也好,二期刻画符号也好,这两类象形符号可能都含有记事的意义,应属于中国汉字的雏形。
中国文字的产生,至今仍不可考。众所周知,商周时代的甲骨文和金文已是我国成熟的文字,但它不是最早的文字。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推测,夏代汉字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在《尚书》、《竹书纪年》等先秦典籍中都有对夏代世系、史事等情况的比较详尽的记载。”可以想像,如果没有成体系的文字,夏代的世系、历法要被记载下来流传后世是不可能的。
比夏代更早的还有黄帝时代仓颉造字的传说。《辞源》上介绍:仓颉,传为始创汉字者。《荀子·解蔽》、《韩非子·五蠹》、《吕氏春秋·君守》等典籍中对此均有记载。《淮南子》中还有黄帝命仓颉造字的说法。《晋书》上说“仓颉既生,书契是为,科斗篆文,类物象形”,说明仓颉造的字是类物象形的“鸟篆”。另外,陕西白水县还留存有仓颉墓及纪念他的庙。综合史书记载和现存遗迹分析,仓颉应当确有其人,他曾对中国汉字的改革、发展和创新作出过重大贡献。但可以肯定地说,仓颉也不是中国汉字的首创者,距今5000年左右的黄帝时代也不是中国文字的源头。
从我国古史传说中黄帝史官仓颉“广伏羲之文,造六书”的记载,我们可以推知“六书”是仓颉在伏羲造字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的。据此我们可以把我国文字的起源追溯到伏羲时代。《尚书·序》载:“古者伏羲氏主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兴焉。”《帝王世纪》载:“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纹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三皇本纪》、《资治通鉴》等古籍皆有是说。上述记载说明伏羲在我国文字的初创中作出了很大贡献。那么,伏羲所“造书契”是不是就是我国最早的文字呢?我国最早的文字到底是从什么时候产生的呢?众多的考古成果为我们揭开了谜底,作出了回答。
我国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半坡、山东大汶口等遗址出土的陶器上,都发现了先民用以记事的象形符号,特别是山东大汶口陶器和浙江良渚玉器上的符号象形而抽象,且具有一定的规律,并已试读出“灵”、“鸟”、“斤”、“戌”等字音。我们知道,规范汉字是以象形字为基础的,而象形字的前身便是各种较为简单的记事符号。已故著名学者郭沫若先生在谈到西安半坡出土彩陶上的刻画符号时说:“(彩陶上的那些刻画符号)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彩陶上的那些刻画标记,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也撰文指出:“西安半坡所发现的仰韶文化的陶器口沿外,往往刻画着简单的文字。这些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所以,毫无疑问,早在6000年左右的仰韶、龙山时代,我国就已经出现了文字。但这还不是中国文字的源头。大地湾一期考古的成果表明,早在7800多年前,我国的汉字就已经萌芽。
专家分析,纵向看,从彩陶符号到刻画符号是循着由少到多、由简至繁的规律发展的;横向看,当时散居渭河、黄河流域的部落、氏族,使用着一些共同的符号。而大地湾彩陶上那些介于图画与文字之间的符号,不仅有些符号与陕西半坡、山东大汶口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基本相同,而且还早于西安半坡和山东大汶口陶器上的记事符号1000多年。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大地湾一期彩陶上的刻画符号是中国文字的雏形,或者说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原始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