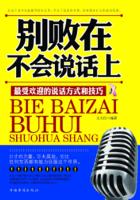1875年5月10日,沙皇来到柏林,向俾斯麦表示俄国不能容忍德国发动对法国的新战争。俾斯麦矢口否认有进攻法国的意图。他把这一消息归咎于法国交易所经纪人特别是与交易所有关的德卡兹的阴谋诡计。但无论俾斯麦怎样解释,人们认为那仅是一种遁词,因为他为恫吓别人而拉响的“战争警报”太逼真了,人们不能不信。俾斯麦有口难辩。
沙皇离开柏林之前,向俄国所有驻外使节发了一个通电:“皇帝离开柏林,完全相信,和平的愿望在这里已经占优势,和平的维持已经有了保证”。电报在报纸上披露时,后一句“和平的维持已经有了保证”却刊为“现在,和平已经有了保证”。这样念起来,造成一个印象,只有在沙皇来柏林以后,欧洲和平才得到保障。似乎沙皇是和平的使者,而俾斯麦是战争的祸首。
1875年的“战争警报”交锋,法国外长德卡兹取得了这一回合的胜利,而俾斯麦这个外交老手却失算了。俾斯麦本想先声夺人,以一场“假战争”吓住法国人,可不成想却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文诡而计谲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已经燃起,德国已经与俄国、英国和法国开战。跻身列强的日本尚未明确表明自己站在哪一方。一天,德国首相贝特曼在首都柏林接见了日本大使。日本大使来访的原因是:自德国参战之日起,一项禁止生产外国定货的法律开始在德国生效。而在此前,日本曾向德国的“克虏伯”和“火神”公司定购了大批大炮和钢甲,并且这些定货业已制作完毕。日本大使要求消除这一令人遗憾的误会,因为日本正准备“与某一大国”交战。关于“某一大国”的提法是意味深长的,而日本大使脸上的微笑也同样意味深长。大使的要求很快得到了满足。因为大使已明白地作出暗示:日本进攻俄国,已是不久将来的事。
几天过后,日本大使再次出现在贝特曼的办公室里。这一次,他手持一份最后通牒,德国必须立即从它占领的中国领土上撤走。日本照会的措辞令人难以想象的粗暴,与日本的外交风格大相径庭。贝特曼和他的国务大臣冯·雅戈夫惊奇地发现:日本1914年的这份照会(最后通牒)竟是德国大约二十年前(即1895年)向日本递交的一份侮辱性照会的翻版,其精确之至,甚至连标点符号的使用都完全一样。在1895年的那份照会中,德国曾要求日本放弃《马关条约》(《马关条约》是日本与中国在甲午海战以后于1895年4月17日签订的条约。由于俄国、德国和法国外交上的干涉,日本被迫放弃该条约条款所规定的对辽东半岛的占领)。德皇威廉二世被日本外交的这一伎俩气得火冒三丈。但是,日本的外交官却矢口否认日方有过任何欺骗行为。是的,日本大使的确说过日本准备与“某一大国”交战。但是,难道德国不是一个大国吗?
列强签订《非战公约》
1927年4月,法国外长白里安照会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建议法、美签订一项双方承担不向对方开战的义务的条约。美国接过了法国的建议,提出签订一个不是法美双边的、而是许多国家参加的公约,共同“谴责”把战争作为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
经过一年多的谈判,1928年8月27日签订了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即《非战公约》。有48个国家签字,包括当时的各个帝国主义列强国家。公约在文字上是堂而皇之的,主要的条款是:不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国际争端只能用和平方法解决。
然而,这项公约对帝国主义列强的约束力有多大呢?当时这些帝国主义列强都玩弄花招,提出了各自的保留条件,使公约的效力大打折扣:
法国在缔约时提出了要保留“合法的防御权”;
美国提出,各国有权进行“自卫战争”。这当然更加冠冕堂皇,这里所说的自卫,不仅包括对国家领土的保卫,而且还包括依据门罗主义对美洲其它国家的“保卫”。
英国则提出,对各国所不承认的国家和所谓自己不能保卫安全的国家可以有行动的自由。
至于日本,也宣称满洲对它自卫的重要性而可以诉诸战争。
这样一来,列强不仅保留了诉诸武力的权利,而且真正发生战争,公约也无能为力。帝国主义列强就是这样玩弄“和平”、“非战”的把戏,而事实上从不愿意让《非战公约》束缚自己的手脚。
谈判中挑选座位的学问
1956年4月,日本农林相河野一郎率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日苏渔业谈判时,会见了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经过一番寒喧后,布尔加宁按着让客方先行就座的规矩,要河野自己选择室内座位,河野环视了一下室内布置,就近选了一把椅子说:“我就坐在这儿吧。”布尔加宁说“好”,便在河野的对面坐了下来。河野后来回忆说,他选的椅子在方向上是背着光线的。谈判中他很容易看出对方的表情,甚至布尔加宁在谈判中露出倦容他也看清了。这样河野可以根据主人的情绪变化来掌握谈判的进度和措辞。河野在回忆录中洋洋自得,宣称这是他在外交谈判的经验中得来的一个秘诀。
勃兰特审时度势定政策
德国地处欧洲中部,如何处理与其东、西两面邻国的关系,历来是德国外交的重要问题。在对待东方邻国的关系方面,每一届政府都有自己的“东方政策”。
维利·勃兰特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他曾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任联邦德国政府总理,提出了“新东方政策”,在欧洲政治舞台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遏制政策”。联邦德国作为西方集团的一员,它的“东方政策”也明显带着集团对峙的特点。50年代,联邦德国拒不承认战后欧洲边界,特别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之间的奥得——尼斯河边界线,也拒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声称只有自己“在国际事务中代表全体德国人民”。联邦德国不与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交的任何国家(除前苏联外)建立外交关系。这样,联邦德国实际上把自己同东方国家隔绝起来了,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受到了限制。
进入60年代以后,维利·勃兰特开始考虑改变联邦德国同东部邻国的关系。勃兰特把德国的前途同它所处的国际环境联系起来,通盘考虑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勃兰特认为,60年代美国和前苏联已经陷入“核僵局”,双方都掌握巨大的核武库,都不敢轻易发动战争,这样,欧洲就获得了“和平的机会”,因此,联邦德国必须改变50年代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不能实现德国的统一,不能摆脱苏联的威胁和美国的控制。联邦德国为解决德国问题必须与前苏联合作,只能以“承认战后现实”换取前苏联的“谅解”。他说:“为了推动政治现状的改变,我们必须接受领土的现状。”因此,勃兰特决心修改联邦德国一直坚持的立场,不再把重新统一放在首位,而是先承认现状,然后再谈统一的问题。勃兰特指望以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力量为后盾,以保持东西方“均势”下的缓和为前提,谋求联邦德国的安全和发展,通过和平方式,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及前苏联和东欧各国进行政治渗透和经济扩张,为最后吞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重新统一德国”逐步创造条件。这些就是勃兰特“新东方政策”的主要内容。1969年9月,勃兰特出任联邦德国政府总理,马上宣布推行“新东方政策”。他派人出访美国和前苏联,得到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支持。勃兰特不仅分析了国际局势的变化和联邦德国的处境,而且看准了前苏联和美国的政策动向,因此,他的“新东方政策”得以比较顺利地实施。当时前苏联正在谋求西方国家承认德国分裂的现状,承认欧洲现状,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而分化西欧与美国的关系,逐步把美国势力赶出西欧。而美国则担心反对“新东方政策”会导致美国在北约盟国中的孤立,因为西欧盟国支持联邦德国的政策,因此美国只好竭力把“新东方政策”纳入美国政策的轨道。这样一来,两个超级大国都对勃兰特开了“绿灯”。勃兰特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利用美苏的需要和担心,来推行“新东方政策”的。首先,勃兰特与前苏联和波兰签订了条约,保证互不侵犯,承认欧洲各国现有边界,这两个条约被称为“东方条约”。其次,东西方在柏林问题上的对峙得到了解决,前苏联承认了西方国家(美、英、法)在西柏林的地位,并保证对西柏林和联邦德国之间的交通负责。这样,东西方关系上的一个重大问题以前苏联的让步获得了解决。
通过东方条约和西柏林协定,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联邦德国摆脱了50年代那种僵持的、封闭的状态,并进入了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活动余地迅速扩大。更为重要的是,“新东方政策”还意味着通过缓和和合作,通过相互接触、交流、对话,增进了解,克服分裂,为最后统一创造条件。“新东方政策”在70年代初结出果实,但它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70年代。80年代末,德国统一的完成就可以看出“新东方政策”的深远影响。
赫鲁晓夫影射尼克松
理查德·尼克松在赫鲁晓夫担任苏共总书记时是美国的副总统。他曾访问过莫斯科,并与赫鲁晓夫有过多次语言交锋。赫鲁晓夫十分反感这个对共产主义制度持强硬立场的美国领导人。
1959年9月,赫鲁晓夫应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邀请赴华盛顿进行正式访问。赫鲁晓夫认为尼克松是反对和抵制他出访美国的,因此他十分不希望尼克松参加他与艾森豪威尔的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