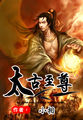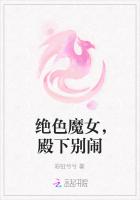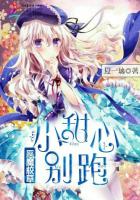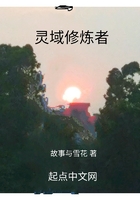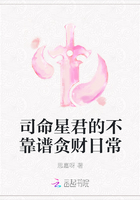上述事实,也许会使不了解中国人特性的人,得出中国人完全不可能有宗教这个结论,这当然很自然。确有人也这样直说了。密迪乐先生在他的《中国人及其叛乱》一书中,就指责古伯察先生的一些结论过于宽泛,密迪乐先生表明这是“对人口众多的中国人的高尚生活,一种毫无根据的诬蔑”。密迪乐先生一直乐意承认,对几百年来的宗教辩论的结论,中国人从不关心,对把这些结论当做信仰的民族行为,他们也不感兴趣。但密迪乐先生坚决否认中国人“缺乏对永生的渴望,缺乏对伟人的崇敬,缺乏对崇高的事业的执著,缺乏奋斗的热望,没有一颗向往崇高、向往圣洁的心灵”。此外,威妥玛爵士,是权威的中国通,这使他有资格对中国人有无宗教信仰作出评述,他最近表明:“要是认为宗教不仅仅是单纯的伦理,我可以否认中国人有宗教。他们确实有崇拜对象,确切地说,是许多偶像混在一起崇拜,但没有信念;他们有无数各种初级的偶像崇拜,他们也会嘲笑这些崇拜,但不敢怠慢。”
对待这个有趣的难题,我们不想介入。详细讨论一下也很容易,但我们不敢肯定能否把问题弄清楚。在我们看来,探讨这个问题有一个切实的方法,要比抽象的讨论更能达到目的。道教与佛教对中国人影响深远,但中国人并没有因此成为道教徒,也没有成为佛教徒。他们是儒教的信徒,不管在这个信仰之上加上什么,或者减少些什么,中国人总是儒教徒。我们打算探讨一下儒教在哪些方面存在欠缺,使之不能成为中国人应有的一种宗教,并将以此结束我们的讨论。为此,我们将引用“中国学”的一位杰出学者的结论,他的结论是不能轻视的。
花之安博士,在他的《儒教汇纂》一书的最后一章“儒教的缺陷与错误”中指出了儒教的种种不足。与此同时,我们得承认,儒教有关人际交往的许多论述很卓越,不少观点还能与基督教的天启观念发生共鸣。我们引用其中二十四条,并作一些评论。
一、儒教否认与现存的神有任何关系。
二、不去区分人的灵魂与肉体。无论从生理上还是生物学上,都没有人的清晰界定。
关于人的灵魂,从无明确的教义,这使得学习儒学的外国学生很困惑。对很多普通人而言,儒家教导的最终结果是,完全不知道灵魂,只知道那是一种肉体上的活力。一个人死后,传统的说法是灵魂升天,肉体入土。但有一种相对直接的观念认为“灵魂”或者气息消散在空中,肉体入土为安,这与真正的儒士的不可知论的唯物主义完全符合。中国人通常对下面一个问题不感兴趣:他有三个灵魂?一个灵魂?还是从来没有灵魂?他对这件事,如同他对吃饭是哪些肌肉带动哪个器官,只要这过程还顺当,他才没有兴趣去管那些帮助消化的肌肉被解剖专家称作什么名称。同样,只要他自己的消化器官很好,靠它为生的人还活蹦乱跳,他才不会去关心自己的和他们的灵魂(要是有灵魂的话),除非他看到这件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与粮价联系上了。
三、没有解答为何有人天生就是圣人,有人生来却是凡人。
四、据称,人人都有获得完善道德所必需的才能,却没解答与此断言相对立的事实。
五、儒教在批评罪恶时,不够坚决、不够严厉,因为除了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评判之外,没有提到惩罚手段。
六、总体而言,儒教对罪恶审查不深。
七、儒教发现无法解释死亡。
八、儒教没有调适手段,恢复人的理想本性。
九、祈祷,以及祈祷的道德力量,在儒教中没有地位。
十、尽管一直强调诚信,但诚实为一切的前提,一直被忽视。
十一、准许和容忍一夫多妻制。
十二、承认多神论。
十三、相信算命、选日子、预兆、梦境,以及其他想象物(比如凤凰等等)。
十四、把内在伦理与外在仪式混为一谈,使之成为一种独裁制度。
十五、孔子对古代社会制度的立场变化不定。
十六、断言一些优美音乐会陶冶人们的情操,这是荒唐的。
十七、夸大榜样的影响,孔子本人就是一个范例。
要是真如儒教所言:君是皿,民是水;杯是圆的,水就是圆的;盘是平的,水也就是平的——那么何以中国的伟人没有强烈感染那些研究伟人生平的人,并修正其性格?这一切按他的理论,就很难解释。要是真如儒士所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那么,为何实效会那么差?下面的第二十条中提到的对“贤人”的神化,与刚才第八条指出的“圣人”欠缺调节手段,两者是相矛盾的。不管圣人有多么“贤良”,他也只能提出好的建议。一旦建议不被采纳,他不但毫无办法,反而不再提了。
我们一直觉得,孔子有一段话很富启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只对贤人提建议,这些建议都很好,但并非预防性的。要是不能起到预防作用,那就需要一服补药。一位旅客被强盗洗劫并打伤,却同他大谈什么参加旅行团的重要性,说他不接受劝告因而吃苦头,流血,精神受刺激,这完全没用。这位伤员已因流血过多而昏迷了,他不是不知晓这一切,事实上他一向知道。他现在需要的,不是指责他违反常规的各种后果,而是油、酒和一个疗伤所,而首先需要明智且乐于助人的朋友。对身体残疾的人,儒教还时常有所帮助;而对道德和精神上的“伤员”,儒教就无效了。
十八、对儒教而言,社会生活需要****,女人是奴隶。孩子在长辈面前,处于下属的地位。
十九、孝顺父母,到了视之为神明的程度。
二十、儒教的本质,如孔子所总结的那样,即崇尚贤人,比如人的神化。
二十一、除了没有真实伦理价值的祖先崇拜,没有一个关于永生的明确概念。
二十二、希望现世现报,潜意识中助长了私心。要是这不是贪婪,也起码可以说是野心勃勃。
二十三、整个儒教没有给大众任何慰藉,不管是在他们生前还是死后。
二十四、整个中国历史表明,儒教在给人新生的希望,让人有更崇高的生活和作为方面,是无力的。现在,在现实生活中,儒教已与道士巫术和佛教观念融为一体了。
有关中国不同信仰的奇异结合,我们已谈了不少。中国人自己也完全明白,无论儒教还是同它混在一起的各种宗教,都不能给人以新生,让人有更崇高的生活和作为。有一篇佚名作者的寓言故事,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在天界里,有一天,孔子、老子和佛祖相遇,他们一起感叹江河日下,人心不古,他们的卓越教导在“天朝”看来没有什么进展。讨论一番后,他们共同认为,原因肯定在于他们的教义尽管受到赞赏,但要是没有一个永恒的典范,人类就不能实行这些教义。他们决定,每位教宗都应该到人间找一个可担重任之人。他们马上分头行动。找了一通后,孔子遇见一位神色庄重的老人,老人并没有离座欢迎这位圣人,而是请孔子坐下,谈起古代的教义,以及这些教义当今怎样被蔑视、施行的真实情况。老人言谈中表现出对古代的信条极为纯熟,并有深入洞察。这让孔子很高兴,他们交谈了很长时间,孔子要走了,但孔子起身时,老人却没有起身相送。孔子找到一无所获的老子和佛祖,把自己的奇遇告诉了他们,建议他们去拜访这位坐着的哲人,看看他对他们的教义是否一样精通。老子很兴奋地看到,这位老人对道教的熟悉,差不多赶上了老子本人,其口才与热情也堪称典范。与孔子一样,老子也发现尽管这位老人态度虔诚,却一直坐在那里不动。轮到佛祖,他也碰到了同样惊奇而可喜的成功。老人还是没有起身,但他对佛教奥义的洞察,却是人间罕见的。
这三位教宗聚在一起讨论,他们一致认为:这位罕有其匹而又令人赞叹的老者,就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他不仅可以分别介绍“三教”,而且可以证明“三教合一”。为此,他们三个一起又来到老人面前。他们解释了上次拜访他的目的,老者的智慧又是怎样激起他们崇高的愿望,并说希望他来振兴这三个宗教,使之最终“普渡众生”。这位老者仍然坐在那里,专注地倾听,然后回答说:“各位圣主,你们的善行比天高比海深,你们的计划极好。但你们不幸选错了去完成这项伟大使命的代理人。我的确看了这些‘道’之本和‘德’之书,钻研经典,并且也真的多少有点明白它们是崇高的、相一致的。但是,有一个情况你们没有考虑到,或者没有注意到:我上身是人,下身却是石头。我擅长于从不同观点来探讨人的各种责任,但因为我自身的不幸,就永远无法用其中任何一家教义拯救人世。”孔子、老子和佛祖各自长叹一下,就从人世消失了。此后,他们不再下凡,寻找能向大众展示三教教义的凡人了。
经常有人把当前中国的状况比作公元一世纪的古罗马帝国。无疑,中国现在的道德状态,远高于彼时的古罗马帝国,但在中国,正如在古罗马,宗教信仰接近垮台。我们可以像史学家吉本评论古罗马那样,来评价中国:对一般人而言,所有的宗教都真实;对哲学家而言,所有的宗教都是骗局;对政治家而言,所有的宗教都可利用。中国皇帝与古罗马皇帝一样,可以说是“祭司、无神论者和神”的三合一!儒教正是如此,混合着多神论和泛神论,把这个帝国带到现在这种状况。
我们已严肃地说过,比起单纯的无神论,那种漠视无神论是否对错的做法更坏。在中国,多神论与无神论是骰子上相对的两个方面,不少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程度不一地相信两者都对,完全没感到之间有什么冲突。
中国人天性上,就对最深远的精神法则绝对漠视,这是中国人心灵中最可悲的特点。他们随时乐于接受行尸走肉,接受一个没有精神的灵魂,接受一个没有生命的精神,接受一个没有来由的秩序,接受一个没有上帝的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