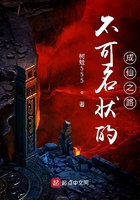转入后半夜,阿芙睡得正酣,裴炎安坐于案边闭目养神。
门外传来了缓缓脚步声。
他蓦然睁眼,起身下意识地回望阿芙,见她翻身向内,酣梦正甜。
行至门前,拉开一道缝隙,声音低而快,“动作放轻一点。”
贺小川一怔,蹑手蹑脚地扒着门框,不知是进是退。
抬头瞧见裴炎一脸赶客的神色,便即刻松了手,规规矩矩地走到一边,嘴里嘀咕:阎王下了凡,比佛祖开杀戒还稀奇......
“有心思说胡话,不如多放点精力在办案上。”裴炎当然是听着了。
贺小川自不敢公然跟裴炎顶嘴,转口便改了话端,“裴大人,慎行已从京师回来了,要不要......”
他淡淡道:“让慎行去塑乡。”
“塑乡?”贺小川声音一提,转眼又瞧见裴炎似刀子般的目光,忙压低嗓子,“嫂子被带去了塑乡?”
裴炎脸色一沉,显然不满他对阿芙的称呼,“口无遮拦,当心你这顶乌纱帽。”
“裴大人,里头那位......不是嫂子?”
“张拓张大侠的遗孤。”
贺小川面上一骇,原本的戏谑已荡然无存,“想不到她竟......”
他转头望向灯火隐隐的房间,似想透过遮挡瞧一瞧阿芙的面容,末了,有些惋惜道:“真是苦命的孩子。”
“行了,别伤春悲秋,塑乡应当能找到蛛丝马迹,”裴炎掰过他的脖子,冷声接着道,“她说死了一个人,你让慎行格外留意那些逃走的贩子。”
“好,”贺小川应下,“红姑那边没有异常,近几日那徐茂荣也未再贩新的小娘子进城,麓州一切太平。”
裴炎沉声,“这样的太平,我看不是什么好事。”
贺小川一惊,心中霎时明了,只默默点头,不再多言。
“综合这些日子的线索看,属下已能肯定徐茂荣与掳走姑娘的那伙人并不相识,且看样子,他并不知晓自己卖入绿柳斋的人已出了城。”
“想来也是如此。”裴炎颔首,“徐茂荣如何也是国舅公府的公子哥,犯不着对阿芙下此狠手。”
贺小川又道:“那红姑牵涉甚广,一时之间仍无法抓到把柄。”
“我如今担心的是掳走阿芙的那些人,会不会......”他顿了顿,低声轻叹,目光落在幽深的走廊,“与我们一直调查的事情有所关联。”
贺小川面露惊骇,倒吸一口冷气,踌躇道,“可姑娘与此事似乎毫无瓜葛,掳走她又有何用?”
“如果那人知晓阿芙身后是我呢?”裴炎侧首看他,眸子里的锋芒一闪而过。
贺小川霍然一震,一时竟不敢开口接话。
“想要用阿芙来试探我的底线,以期能牵制锦衣骑的动作,这个推断看起来荒谬,可如此推测下来,很多疑点却能得到解释。”他语声低沉,似也略有担忧。
“那人若与红玉勾结,就必然知道大人当日去见了姑娘——姑娘身份清白,稍加留意便能联想到小池坞......”贺小川面色一沉,显然已融贯了裴炎的逻辑,“按照大人的说法,这样便解释通了!”
“这件事,暂时不要告诉任何人。”裴炎淡淡道。
“那慎行......”
“慎行到塑乡只为查当日花灯会的疑点,若告诉他这些未证实的推测,我怕他先入为主,调查方向有失偏颇。”裴炎解释着。
“是,大人。”贺小川当即顿悟,低声答应。
顿了顿,他又迟疑道:“那姑娘醒来后打算去哪儿?”
裴炎不语,独自思忖片刻,才道:“她要去丰京。”
贺小川一惊,“陛下当初已严令姑娘再不得踏入京师半步,这......”
他低叹,“若我猜得没错,她是听说了那件事。”
瞧见裴炎阴沉的脸,贺小川微愣。
皱眉想了片刻,霍然醒悟,有些无措地望向裴炎,低声道:“想来姑娘始终耿耿于怀,这蒙原世子还真不是个东西!”
“罢了,都是徒增烦恼的旧事,她想去,便由她。”裴炎蹙眉,心中已不知是何思索。
贺小川望了他一眼,嘴角轻撇,心中暗叹还真是一物降一物,他裴炎这冷面阎王也有这般无可奈何的一天!
不多时又想起一件琐事,语态已复了轻松,“对了大人,佛牌已备好,是我按照吩咐从麓州城外的云舒寺求来。”
裴炎先是一顿,转而默默点点头,没有言语。
贺小川一脸揶揄,“大人,你真是艳福不......”
最后那个字还未说出口,贺小川的小腹就被结实地挨了一肘子,裴炎那一撞全无收力之势,这功夫足让他浑身冒了冷汗。
贺小川瞪大了眼,捂着肚子却又不敢大声叫唤,面上扭曲扶着门框,好久还没缓过来。
“明日启程回京。”裴炎冷冷地丢下这句话,转身准备回房。
贺小川忙道:“大人,我这边还有些安排没布置下去,忽然回京......你总得给我一天半天准备吧?”
裴炎拂他一眼,“离明日午时还有五个时辰,你说闲话时间倒够,安排人手却不够?”
言罢,门已被他轻轻关上,贺小川有苦也说不出,差些气结。
风萧萧,夜凄凄,此刻若是慎行在,他必定要向好兄弟大吐苦水,控诉这些日子以来,裴炎对他惨无人道的折磨。
如今却能如何?
只得就这样就着长夜,孤零零回住处罢了。
旦日一早,阿芙在朦胧中醒来。
尚睁眼,自然而然地拧头寻找裴炎的身影,这样下意识的举措,迅速到连她也未察觉自己已如此依赖他的存在。
他依旧端坐案前,似几个时辰以来都未动过。
阿芙才坐起身,他已听到动静,“替换的衣物我放在一边,你起来梳洗妥当,我到楼下买些吃食。”
裴炎一直未转身,阿芙知晓他是怕冒犯了自己。
目光随他的话落在了榻边的衣物上,像是套男装,看着与裴炎现在的衣着材质相仿。
还未来得及多问,眼前人已闭门离去。
而那把从不离身的绣春刀却被他留在了案上,想来是怕阿芙有何意外,可用来防身。
心中微暖,阿芙落地穿鞋,此时右肩的疼痛已消了大半,裴炎的药果真有奇效。
简单洗漱,换上青衫,长发被她松散地挽在肩头,若只瞧她的背影,还当真雌雄莫辩。
裴炎推门进来的时候,阿芙正握着绣春刀,一手提着刀柄,仔细观察着那锐利的刃。
察觉来人,她蓦然转身,神色傲然地望着裴炎。
他微怔,转而轻笑:“玩心不泯。”
手里提着两袋热气腾腾的黄糖糕,轻轻放在案上。
另一手则已将出鞘的刀推回,抬手一托,绣春刀被他轻而易举夺了去,顺势便摆在了一边。
“趁热吃。”他已拆开一袋,两指夹出一块糕点,塞进嘴里。
阿芙怏怏坐下,有些不服气,“若是当初将阿娘的雀翎刀带出来就好了。”
她嘴里咬着糕点,语气含糊,觉得黄糖糕美味,便又拿了一块,像有谁会跟她争似得。
裴炎看在眼里,嘴角牵起,“张夫人那套刀法你练得如何?”
阿芙一愣,有些心虚,“自然已融会贯通。”
他笑意更浓,“我倒想找机会跟你切磋一番。”
阿芙惊得手指一颤,黄糖糕竟掉落案上,“你、你胜之不武!”
裴炎朗笑道:“阿芙,你我尚未比试,你怎么就认定我必然会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