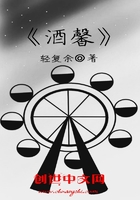这虽然是一句极为正常的话,可惊吓了红星。红星由此想起了早上发生的事:难道早上的事让父亲晓得了?小时候他看到,父亲每次上庙敬神,都要洗手净脸,以便对神灵保持圣洁。他在学校念书,也从回民同学那里晓得了他们的宗教习惯,他们在进清真寺礼主麻,或者做圣祭,给亡人念索儿、散乜贴的时候,都要做阿不待斯和乌苏里(小净、大净),以表示对真主和亡人的圣洁之心,自己早上干的那事,身子分明受到污染,还能上庙给神烧香?他斜着眼看了一下父亲,父亲脸上并没有异样的表情,还是慈眉善眼的样子。他就端了水壶到房门台子上浇水洗脸净手。他趁父亲不注意,端着水壶走进茅厕,掏出那个软绵绵的物儿,用水浇着清洗了一遍,直到把壶里的水浇完,他才系上裤带出了茅厕。
在庙的废墟上,已经有人在那里点香烧表,远远望去,一团一团的火焰在黑暗中发光。红星带着复杂的心情向庙的方向走去。他尽量躲着人,不让人们认出是他。因为他是支书的儿子,又是受过教育的学生,会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影响,要是田组长知道,肯定要批评父亲。他按照父亲的吩咐,在一个僻静的角落,跪下点燃了一撮香和一叠表,烧化后爬下磕了几个头,就快步离开了。
红星回到家里,见父亲又在收拾东西,他把一叠一叠的冥票纸钱放进竹篮子里,又拿了一盒香,一盒表装进篮子。他见儿子进屋了,就说:“丑旦,咱俩去烧个纸,一年了,得给亡人送些盘缠,你拿上几个鞭炮。”
大年三十上庙叫马,给亡人送纸,前几年也是这样子,今年工作组抓得紧,该不会有啥麻达吧?但红星只是心里这么想,也没有说出口。他见父亲收拾好了,就提了篮子随父亲出门了。父子二人绕过了涝坝沿,沿城墙根向西走去。他们来到一处城墙拐角处停下,摆开了篮子里的祭品。红富贵把祭物分成三等份,放在两处,一处是一份,另一处是两份。他对儿子说;“这一份是你父亲老刘的,这两份是你姑夫姑妈的。你如今长大了,这些纸钱应该由你来烧点。”红富贵掏出洋火匣子交给儿子。
红星跪在地上虔诚地擦着洋火,但擦了几根都没有擦着。红富贵说:“不要慌,慢慢擦。”
两堆祭物先后点着了。火苗忽忽地燃烧起来,红富贵折了一根树枝拨着祭物,口中喃喃地念叨:“姐夫姐姐,又是一年了,我领丑旦儿给你烧纸钱哩,你们就收下。过去家里穷,你们省吃俭用,把我拉扯大,又拉扯了丑旦,是我们连累了你们,你们把命都搭贴上了,你们的情,我们这一辈子当牛做马也补不上。如今解放了,穷人自由了,可你们却享不上这些福,我们只能给你们逢年过节烧些纸,给你们报个信儿……”
他又拨了拨属于丑旦生父刘继业的祭物,也说了几句安慰亡灵的话。
纸钱在火焰中燃烧,纸灰带着尚未燃尽的火星随着拨火棍飘到空中,红星仿佛从这火光和纸灰中看到了三张模糊的面孔。
生父刘继业他没有见过。但他曾经听他现在的父亲红富贵说过他。他是一位长相魁伟的架子花脸。母亲齐翠花也说过他:你越长越像你亲老子。那么,自己的亲老子究竟是个啥样子呢?戏台上的花脸他也见过,那些花脸好像个个脾气暴躁,嗓门特大,动不动就扯着嗓子骂人,或者拿着兵器、笏板打人。自己的生父难道就是那个样子?自己到底哪达像父亲呢?自己的脾气一点儿也不暴躁,不要说打人,就连骂人也很少有过。学校带体育的老师甚至说自己腼腆得像个女娃子。有时他也掏出一小圆镜儿照一照自己的相貌,那脸面说不上漂亮,但也并不难看,顺子姐还说自己长得好哩……
姑父陈润年和姑妈陈红氏他倒有些印象。姑父是一个高个子人,微胖,他长着密匝匝的灰白头发,红里透黑的大方脸。他最怕他嘴上的胡茬,那胡茬扎起人来,可真难受。姑妈是一个颠着一双小脚的老太太,她的红肚兜里总有掏不完的核桃、枣儿、花生或者洋糖。人说三岁记老,可自己两岁的时间就记住了经历的许多事情。他最忘不了的是他跟姑妈一起在县城大堡子里的情形。
那个堡子墙很高很高,比红城子的大堡子还要高。城墙上站着拿枪的人,枪上面的刀子明晃晃的。他一看见那刀子就吓得叫唤,把头往姑妈怀里埋。最让他害怕的是姑妈挨打的场面。那些个挎枪挎刀的人,强行把自己从姑妈怀里抢夺过来,一阵一阵的鞭子就抽打在姑妈的脸上和身上,姑妈就痛苦地叫唤,他也吓得大声叫唤。那些个脸上看起来很凶的人有的坐在桌子前,有的站着;有的人大声呵斥她,让她从实招供,让她说出她兄弟和弟媳的去向。后来他才知道,是他的父母亲跟着田大勇叔叔在县城监狱里劫持走了百旺叔叔和兰香婶子,放走了所有犯人,大伙儿一同投奔了延安共产党,让留在家里的姑父姑妈和幼小的自己当了替罪羊。他是如何被抓进县城监狱的,似乎记不清了。可那骇人的审讯场面他是至死也忘不了。那一回姑妈第一次遭受毒打以后,浑身伤痛的她回到号子里,搂着他整整哭了一夜。她叫着自己的名字:“丑旦儿,我命苦的丑旦儿,姑妈怕是活不成了。丢下我苦命的娃谁照看哩?”记得她还狠狠地叫骂父亲红富贵和母亲齐翠花:“富贵呀,你们两口子贼天杀的,把祸给我们闯下了。你这贼天杀的……”
自从那一次提审姑妈挨打以后,只要听见牢门响,他就吓得紧缩进她的怀里。第二次提审姑妈的时候,他见到了姑父。姑父的脸上也青一块紫一块的。他的手上和脚上都戴着铁链子,他一动弹,那链子就嚓啦嚓啦响。当姑父抱过他又用胡茬扎他的时候,他摸了一下那铁链子,好冰好冰的。当时姑父姑妈说了些啥话,他记不清了,只是看见姑妈一个劲儿地哭。自从那一回见面后,就再也没有见到姑妈姑父,后来长大了,才晓得姑父被那些人拷打死了。姑妈也是被那些人打死了。但具体怎样打死的,他没有看见。只记得有一天夜里牢房门开了,有两个拿枪的人喊着陈红氏的名字,当姑妈要抱着自己出牢门的时候,那两个人喝喊着不让带小孩,姑妈就把自己交给了同牢房中的另一位大婶。记得自己当时伸着双手要姑妈抱着走,可那个枪上有刀子的人喝了一声“不要哭,哭了就割耳朵”之后,自己就再也没有敢哭叫。自那以后,也就再也没有见到姑妈,自己被转来转去,最后转到了红城子,又转到了延安……
大年除夕,人们仍然遵循着家人团聚守夜的习惯,食堂里的管理员、炊事员收拾完灶具都回家过年去了,只留下梁老头儿一个人看守门户。齐翠花吃罢晚饭,等人们散尽之后,就一个人在堡墙女墙四周转了一圈儿,听了一阵四邻八村的鞭炮声,就带着满腹的惆怅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小房。
红星顺墙根走进了大门,径直向他母亲住的二层高房上走去。高房里亮着灯,他就用手拍了拍门板,轻轻叫了一声“妈”。门开了,齐翠花见是儿子丑旦,脸上露出了惊喜。她说:“你来了?”
红星说:“我给你拜个年。”说着把衣袋里的核桃枣儿洋糖和花生掏出来往炕上放。
齐翠花说:“不要掏,留着你自己吃。”
红星说;“我不吃,是我专门给你拿的。妈你吃。”他说着剥了一块洋糖,递到她的手中。
齐翠花接了那块精美的糖果,眼泪齐刷刷地流了下来。
红星见母亲这样,显得有些无奈,他搓了搓手,轻声说:“妈,你不要伤心。大过年的,你不要哭……”
齐翠花深知儿子的秉性,她生怕儿子走掉,就连忙擦干了眼泪,拉着儿子坐在了炕沿上,无话找话地问这问那。她问:“是自己要来的,还是你大叫你来的?”红星说;“我想来。”她说:“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末了,她向儿子提出了一个要求:“丑旦儿,今晚是大年除夕,人都回家过年了,这么大的堡子,就我和梁老汉两个人,你能不能陪妈住一宿?”
红星说:“我临来的时间没有给我大说,他怕是不同意哩。我还是回去的好。”
齐翠花说:“儿子陪母亲坐除夕夜,你大他是能理解的。躲过今晚夕,可就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丑旦,咱娘俩见一次面也不容易呀!”
正在这时候,梁老汉在院子里喊叫起来:“丑旦,丑旦,你回去吗?我等着闩门哩!”
也许是齐翠花想儿子的心太切了,就出了房门对梁老汉说:“老伯伯,你就再辛苦一阵,让丑旦再坐一阵子。”
梁老汉说:“辛苦倒是不辛苦,夜深了我怕他一个娃娃家不敢回家哩。要不然这么办,我看丑旦儿就不回去了。大年三十晚夕,你娘们子说一阵话,我去给支书说一声,就说丑旦陪他妈说话,坐夜,今晚夕不回来了。叫他不要等了。丑旦,你个崽娃子听见了没有?”
梁老汉帮了齐翠花的大忙,红星不太情愿地答应了。
齐翠花找东西砸烂了核桃,剥了花生皮,娘儿两个边吃糖果边聊天,从儿子的出生到受苦受难,从坐监牢到去延安,再从学校生活到家庭生活,做母亲的都絮絮叨叨地谈论着,红星只是被动地应承着。夜深了,红星一下接一下地打着哈欠,他瞌睡了,也乏了。是呀,一个身体尚未发育成熟的少年,从早到晚,又写对子又贴对子。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漏了身体内的宝气,他能不乏吗?再者,他从小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时断时续,心灵上不是那么贴近,也还没有从内心深处体会到母亲的苦衷,所以也就不习惯听母亲絮絮叨叨地诉说。
齐翠花见儿子瞌睡了,感到十分心疼,就说:“你瞌睡了,你先睡。。”她拉过枕头,把自己的褥子铺在热炕上。红星也顾不上客气,倒头就睡了。
齐翠花扶着儿子睡下,就给他解开鞋带脱掉鞋子。当她把他破了洞的袜子从脚上退下来的时候,一股脚臭扑鼻而来。儿子长了这么大,她还没有嗅过他的臭脚味,这会儿,这种特有的味道,不但不觉得臭,反而觉得有些香。她在他的臭脚片子上用手轻轻地抚摸了一阵,觉得应该给他洗一洗。就下了炕,端过脸盆,用缸子在木桶里舀了两缸子水,然后取开暖壶的瓶塞,往脸盆里倒进了一些热水,用手指头试了试水温,觉得还有些凉,就又兑了些热水,把毛巾泡在脸盆里摆湿,又拧掉了一部分水,轻轻地给儿子擦拭起臭脚片子来了。在她的心目中,儿子还没有长大,但脚片子却像大人的一样厚实。这一双肉乎乎的脚片子,多像他老子刘继业的。刘继业喝醉了酒以后,她也这么为他擦洗过脚片子。灯光下,儿子的脸上泛着黑黝黝的光,宽宽的额头,浓浓的眉毛,长长的睫毛,高高的鼻梁,厚厚的嘴巴,活活地显露出一个当年的刘铜锤来,刚生下来那奇丑无比的相貌和三岁以前病黄拉几的样子,如今在他身上荡然无存。她自然想起当年诊脉和算卦先生以及那些阴阳对他的预测:他有贵人之相。后来在边区时经过一番马列主义无神论的洗礼,她也对这种说法产生了怀疑。但在她处于逆境,生活丧失信心的时候,她却自觉不自觉地把儿子的前途当作精神支柱。在延安与丈夫红富贵离婚的时候,还一度为儿子的归属争执过一段时间。最后还是在张百旺、王兰香夫妇以及田大勇的极力劝说下,她才作了让步。她清楚地记得红富贵当时的话:翠花,你今后还可以再生养,可我是这么个样子,哪里还能再有孩子?丑旦虽然是你的孩子,可他从小是我惯大的,我离不开他呀?翠花,你就放这一马吧……一个刚强的男人,当时流下了泪水。张百旺夫妇和田大勇都帮他说话,既然咱们把话都说到那个份儿上——离不离都像一家人一样,丑旦儿就留给富贵哥吧?
望着儿子憨憨的神态,听到他带有男子汉厚重的鼾声,她心中涌上一股幸福的暖流。
这孩子长了这么大,也太不容易了。怀他的时候,差一点儿让我这个狠心的娘打掉,一岁以前,一直病得不出脱;两岁的时候,又莫名其妙地坐了几个月大牢;一家人刚刚团圆。父母亲又离了婚……这孩子也就太苦了。由儿子她又想起了另一孩子——田园。她今年也该七岁了。她跟上她老子田大勇去了内蒙。她如今在做什么呢?园园,妈也想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