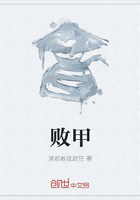萧乾坤道:“据说一个魂魄到阎罗殿去报到时,若是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就会多受些苦难。”
井秋云道:“所以你不忍心我做一个糊涂鬼。”
萧乾坤道:“对极了。”
李柔倩跳了起来,愤怒极了,“你简直不是个人,简直是个混账东西。”虽然愤怒,但她也有她自己的目的。
萧乾坤道:“我若不是一个人而一个东西那该多好啊!是人就免不了七情六欲、爱恨别离,我若是一个东西就可以为所欲为,不必为种种约束、种种道德伦理去控制无穷无尽的欲望。”
李柔倩冷笑。
忽然藏雪雅儿冷漠地道:“真是恬不知耻。”
萧乾坤道:“我只为欲望而活,无所谓耻与不耻。
藏雪雅儿又道:“不可救药。”
萧乾坤道:“满足欲望,达成欲望,生又何欢?死有何惧?”
井秋云道:“我真的很景仰你。世上的每一个恶人在作恶事之前总会找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自己开脱罪名,而你则不然。”
萧乾坤洒然一笑,“每一个成大业、立大事者的身上都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诚实。只有待人以诚,别人才会信任你、依赖你,何况真小人远比伪君子更可爱些,你说是吗?”
井秋云抚掌大笑,声震林木,“不错,对极了。”井秋云的神情陡然间变得很真诚也很诚挚,“千金易得,知己难求。若是你我早相遇一年就可以做一年的知己,若早相识一天就可以做一天的知己,若早相识一个时辰就可以做一个时辰的知己。只可惜上天偏偏不给我们这个机会,当我们一见面时,我就会出手杀你,我一出手,你必当反击。”他漆黑色的眸子里露出淡淡的孤寂。井秋云却还是大笑,没有说话,谁都可以自他的笑声中领略到他那种身在高处不胜寒的孤独、寂寞以及对知音的无限期盼。
李柔倩当然不懂,扬起脸狐疑地看着眼前这两个亦敌亦友的人——既是敌,又怎会成友?既是友,又怎会是敌?她满腹疑团地看着这两个奇怪的人,她忽然想起父皇曾对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对你有深刻了解的人往往并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你的敌人,一心一意想要打败你、甚至想要置你于死地的敌人。敌人对你有深刻的了解是为了战胜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朋友对你的了解仅仅停留在极其肤浅的表面。
李柔倩向后连连后退,无形的杀意使她立不稳脚根,唯有后退,退出杀意袭击的范围,她这一退,便退出了三丈有余。甫一站定,耳畔只听得井秋云还在大笑,只是这种笑声显得非常高亢、极具震撼力,仿佛自九天之上重重地砸在地面,又似乎从地狱里升起,在大地上爆裂开来。在这声音里竟有一种奇异的莫名的力量,这种力量是磅礴的、大气的、虎虎生威的、无惧无畏无人无我的。李柔倩猛一抬头就看见井秋云的身躯正一分分、一寸寸往下沉,一双脚已沉入石子地面中直至脚踝。她不由得大惊失色,这个萧乾坤究用的究竟是什么武功,居然可以迫使对手沉入地面?井秋云这样天下江湖有数的高手竟然也遇到如此的窘境?
她再看萧乾坤时,只见他面色深沉如水——水,可以静止也可以流动,池塘里是水是静止的,江河湖海里的水则是无时无刻不在流动着的。当井秋云纵声大笑时,萧乾坤深沉的面色就如流动不息的水,面部的每一根神经都在轻微的波动,每一块肌肉都在抖动和颤动。“动”着的面部犹如被春风吹皱的湖面,粼粼而动、蠕蠕而动,一纹又一纹,显然是受到井秋云笑声的牵引。而当井秋云的由于换气而笑声止住的一霎那间,萧乾坤那深沉的面色就如静止的死水一般无波亦无浪,极力地压制着井秋云笑声的发出,不但是井秋云的笑声发不出来,而且还把井秋云的身子强压得沉入地面——这就是静止的死水,其本身并无生机与活力但却能够孕育“生”的力量。
萧乾坤这个人仿佛已与空气融为一体,这个人若有若无、若隐若现,形如鬼魅幽灵。井秋云紧咬着牙关任由着双脚不由自主地往地下沉,一种无穷无尽的气势把他罩住——他的神智犹自清醒,他可以真实的感受得到这股无形气势的力量是如此地可怕和强大,他发不出声音来,就连全身上下所有的明的、暗的、正的、斜的劲力都无法挥发出来,而敌人身上的那种力量却仿佛来自天地间的每一个黑暗的角落——光芒是一种力量,鼓舞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活下去,坚持到最终的胜利。黑暗也同样是一种力量,引诱人沉沦其间而不能自拔。
铁见月则是静静地注视着场中的变化,他忽然间听到一点笑声,那点笑声之后就是一个如晴天炸响的惊雷,“出门大笑仰天去。”七个字如七级台阶,井秋云在一级一级地走上地面,同时又如七道利箭射向萧乾坤。萧乾坤在井秋云双脚踏上地面时,后退了半步,一尺二分长。井秋云只是身子晃了几晃,却没有跌倒,额头上只有豆大的汗珠滚落。
这一番拼斗二人都未曾动过手足,但激战和恶斗却在无形中展开——李柔倩从未想象得到世间竟然还有如此奇妙的交战。
井秋云惨然一笑道:“‘维摩不染,天女散花’果然名不虚传,今夜总算是长了见识。”
萧乾坤的脸色苍白得吓人,“彼此彼此。这只是一个开端,你应该是知道的。”他的语气和神色一样都显得诚恳和真挚。
井秋云仰天大笑,“我知道,那就让真正的交战早些开始吧。”
萧乾坤却没有说话。
井秋云的话好像越说越多,“尔来四万八千岁,始与秦塞通人烟。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方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猴猿欲度愁攀岩……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冰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他口中所吟的正是李太白的千古绝唱《蜀道难》,当吟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一句时,他脚下路面上的石子全都飞了起来,席卷、激射向萧乾坤。
萧乾坤不但没有说话,而且一动不动,仿佛老僧入定。当密集如雨隐隐挟着风雷之声的石子来到他近前时如撞倒墙壁一般纷纷失去力道坠落在地,只见他皱了皱长长的白眉,一记手印缓缓地推出。西藏密宗大印手!佛门至刚至阳至纯至猛至正的上乘武学。一记“大印手”其本身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变化,世间所有的武功或多或少都有变化,即使不是精微奇妙的变化,至少也是掌指间尺寸的变化,然而,一记“大印手”却没有任何的变化,这一点,萧乾坤还是很自信的。
没有变化的武功才真正可怕!可怕的并不是武功本身的变化,而来自于人心的变化。前一刻还笑脸相向、低头哈腰,后一刻便盛气凌人、拔刀动枪;前一刻还你侬我侬、相依相偎,后一刻便拳脚相加,劳燕分飞——只有人心的变化才真正的可怕。当你沉醉在没有变化的局中时,真正的变化如暗流般悄然而至,将你无情地吞噬。井秋云现在所看到的只是一记没有变化的“大印手”,仅仅是看到,他不知道萧乾坤的这记“大印手”将会在何时发生变化,唯一可以预见的是这记“大印手”一起变化就绝对可以致命。变化将在何时起?抑或是这一局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变化?井秋云唯有等,以不变应万变,抑或以不变应对不变。
龙门承侠拉着李柔倩的手被迫退得更远了些。没有人能够在西藏密宗大印手的攻击下安然地全身而退。
就连风雨不动安如山的藏雪雅儿也在同一时间内陡然变色。
唯见她忽然间转过身来全神贯注地紧盯着战局——她用一根手指轻轻地拨开遮在左眼前的长发,一只明澈如水的眼睛仿佛可以将世人心中的尘埃和污垢涤荡干净——
忽有大风吹起,将她本已凌乱的长发吹得更加的凌乱不堪。
这阵大风来得快,去得也快。
井秋云的暴喝声在大风中骤响。
龙门承侠、李柔倩、羊伯老、铁见月、水月光、宗氏兄弟这些在一旁观战、掠阵的人同时发出惊呼声,无不目瞪口呆——“大印手”开始变招。
萧乾坤已动,随着“大印手”的招式而动——没有人能够形容得出萧乾坤“大印手”变化的速度,每一招每一式都变化出令人想象不到的招式,仿佛他整个人都化作了这一记惊世骇俗的“大印手”。每一招每一式都显得如高山似流水般,洋洋洒洒、肆意而来、随意而行、意止而未尽,竟然完全不受身体、生理的限制而有所制,如江海般不改初衷、不畏岩石险滩所阻,一意东奔而流,也同样没有人能够形容得出萧乾坤的动作和反应之快的速度,人间的飞箭、天外的流星也不堪与萧乾坤此时相比,他的动作是自然而动,师法“自然”,道法亦“自然”,如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的身形甫地一动便在顷刻间幻化出千万之“动”。“动”如排山倒海、怒浪滔天,绵绵不绝,一发动而全身动,动得优美而洒脱,如精于丹青的妙手,或寥寥数笔、可轻可重、可浓可淡的片刻间便成一幅丹青佳作,手中的一根三尺狼毫如有神助。
没有声音,只有“变”和“动”——井秋云的“变”和萧乾坤的“动”,不变则死,不动则亡。为了生,只有变,只有动,除此,别无选择。
武功在他们身上已成了一种艺术,优雅而美丽的杀人的艺术——杀人也是种艺术。
武功的出现就是为了杀人。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为救人而杀人、为杀人而杀人、为名利而杀人、为自己而杀人、为活下去而杀人、为吃一口饭而杀人、为争一口气而杀人,杀人的目的虽不同但都同样是杀人。杀人的人可怕、可恨、可恶但同时也可怜、可悲、可叹——这世上没有人愿意杀人,但自人类出现的那一天时起直到人类的末日,每一天都会有人被杀,每一天都有人出于某种目的而杀人。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