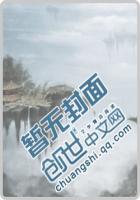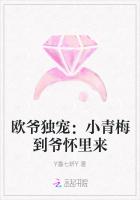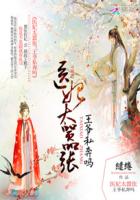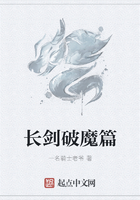“妈妈——个小女孩指着识字课本问,“天怎么是蓝的呢?”妈妈肯定地回答:“天,当然是蓝的啦。”小女孩又指着窗外天空不解地追问:“妈妈,外面的天真是蓝的吗?”妈妈打开窗,看到的是一片灰色的天空。“那湛蓝的天空跑到哪儿去了呢?”小女孩瞪大了疑问的眼睛。妈妈有些惶恐,怎么对孩子描述呢?只好抱愧地对孩子说:“等春天来了,妈妈指给你看。”
春天来了,没有一个真正的蓝天,小女孩问起妈妈,妈妈说等夏天来了再说,就这样夏天又过去了,妈妈说,等秋天来了吧,秋天里蓝天最多,这时雨水没了,云朵散了,雪要下了,应该没什么遮挡了,到了秋天,蓝天仍然没有,也就是说,妈妈记忆里那样蓝的天是没有的了。但妈妈的心里却装下了儿时的蓝天,妈妈是幸运的。那时的春天花红柳绿,溪流潺潺,天像蓝宝石,这宝石上偶尔还有一朵朵轻盈的白云点缀其间,那么飘逸/那么诗意盎然;秋天的天空像一匹蓝缎子,整个天幕找不到一丝云彩,那蓝的色彩既深邃又神秘,既空阔又醉人。
妈妈曾一个人独自穿行在秋风里,秋风拂弄着她的衣裙,也吹拂着她的长发,吹得她少女的心一漾一漾的,有种飘逸与迷醉,吹得她心旷神怡,心底泛起一阵阵牧歌;妈妈也曾躺在夏天的山坡上,闻到的都是草汁浓浓的芬芳。眼前,是飞奔过天空的一朵朵积雨云,阳光直刺云翳,彩虹过后,天空上奔跑过一批批羊群,大地上迅速闪逝过一片片暗影,稻田里,坡地上,那些秧苗、麦子、荞麦花,迅速地在一明一暗中闪亮起伏着,跃起身子。
这些大地的宠儿没变,但妈妈现在确实见不到她青春年少时见过的蓝天了。这些年她在忙碌中度过,现在打开窗,妈妈愣神了,真的像孩子所说的,不见了蓝天,天壁上像覆着层薄膜,那并不远处的青山出没在终日的雾爾中,妈妈明白这雾霭并非是水气,而是那轻轻飞起的沙尘,就是它们挡住了孩子的视线,见不到蓝天了。妈妈说:“孩子,如果想看,就去看电视,或在电脑上去看。”女孩说:“那里面的怎么看都觉得是假的呢?”妈妈说:“想看真正的蓝天,只有到云南、西藏、青海去,电脑、电视里的蓝天,是模拟出来的,那只是假想的蓝天罢了。”女孩更不明白了:“为什么不能留下真的而要做个假的?”妈妈就笑了,笑里有种尴尬和无奈,半晌对孩子说:“孩子,别问了,大人们也想留住蓝天,可又留不住。你看那行道树,灰土土的§那流水沟,冒着刺鼻的气味,郊外的地里,不知谁在焚烧化工下脚料,有许多人喝了不干净的水,呼吸了不洁的空气,吃了有害的食物得了病,甚至丢了性命。”妈妈说:“我们还算幸运的呢,仅仅是看不到蓝天了。”
小女孩想了一会,点点头。她听人说,有些小鸟绝迹了,有的植物也不见了,在她来到这世界之前,还有好多物种就永远消失了,所以她不知道那些动物植物活着时是什么样子。但她相信,只要人们都来关心大自然,都来珍爱每一寸土地,每一滴水,每一棵草,每一种小动物,一切都会好起来。也就真能看到什么是真正的蓝天了,因为蓝天是不会消失的,它仅是暂时躲了起来,只要躲了起来,就能找出来。
想到这,小女孩心里立即涌过一股热流:我要当个植物学家,不,要做个环保专家,不,要做个有力量的人,就像童话里的国王,要把蓝天找回来,让所有的人都有蓝天、草地、阳光和清风,心情舒畅地快乐生活,保护好我们的地球,珍爱自己的家园。她要把这些心里话通通告诉妈妈。
小女孩看一眼妈妈,妈妈的脸上有一颗泪,她顺着泪的爬痕见到了一双明亮的眸子:那里有一片蓝天,小女孩猛地抱紧妈妈的头,把她搂在怀里,她的精神刹那间长高了。
茧,是蚕的一张床。
这张床是自制的,因为自制睡得就尤为踏实,但这也就令人心生感喟:忙碌一生,只与一张床有关系。有些人忙碌一生,只与一幢房子有关系,直到老死乡里。这个人呕心沥血了一生,最后像一只蚕回到茧里,其实,茧最终也不是蚕的,蚕把桑叶吃下,吃够了,又将丝吐出,吐尽了,给自己找一个归宿,把内心吐光,又让内心成为掩体的工具包裹自己,谁说这是与世隔绝的呢?自作自受呢?一个人难得有一个独立的绝对的属于自己的空间,蚕有了。
有人或者以为蚕把自己装进了一只保险箱,像一个高深的隐士,永远就可以这么隐匿下去。隐匿是一种智慧,或者是生命的最终结果。
茧,也给了发明家以提示。人,把它模拟为真实的睡袋。在严寒的野外从事战争、勘探。茧形的睡袋是他生命的另一半。另一半往往就不是来自自己了,而被外力操控着的,要想成为一个完整的“我是何其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另一半那儿,连自己都不能准确对接,这就是人。在野地,一只蚕发现一只孤独的睡袋,会觉得多么奇特!这是一种有年限的知识产权的使用么?当人与人为了传播和限制传播一些信息的时候,蚕,没有想到世间竟为人之间准备了所谓讨回公道的法庭——这莫非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
但是,我看到了房子,各式各样的房子。包括舅爷爷的草房子、土坯房,还有城市里冰冷的水泥高楼,房子的内部,有床,供人休憩和睡眠——滋生自由,也膨胀着享乐与贪欲。
为了更安全,床、睡袋、房子、茧,又有各自的独立空间和存在的理由。
蚕有了茧子,蚕这一生就完全了。这犹如村庄里的人最终羡慕某某有了一口棺椁一样。人把自己的尸体藏起来时,蛋已于先活着时就把fi己藏了,而且不用同类操心。在一段时日之后,你再也找不到蚕本身。至多会发现涂着彩粉的蛾子,像那些在脂粉里洗过的芳华,知事的人便清楚那是蚕的转世,或者叫它还魂,人信不信呢?蛾子信不信呢?这就是人与蚕的大异之处。人有时弄出事来,自己收拾不了要依靠别人,可是有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小动物,它们不,它们把自己料理得精细,自己管好自己的事,让你不得不钦佩。
人们剪开茧子,这时的蚕可能做了产妇。产妇不再永久地占着这张婚床,她们像退位的女皇,消隐在古刹的晨钟暮鼓中。而民间,烟火缭绕,香火正盛,蚕妇们忙着上架,采桑,她们从早上起床后,就为肥胖的小蚕忙活。一口口细碎的轻响,正如夜里的梦事,人,恍惚又迷醉,她们明白,一张床,对于人、蚕、种子,有属于天性的必然选择。
蚕的声响,原来是一种十分原始的母语的呼唤。辽阔、旷远,甚至有些深邃。蚕妇们立即意识到自己何时是一只蚕,在产床上幸福乖巧地替一个叫“母亲”的名词,做了一只茧。这只茧里注定了一个女人抽不尽的丝丝缕缕:缠绵、哀怨、亢奋、荒诞、满足、缺憾。
一盏白炽灯下,我某日再次亲近白胖胖的蚕身子,它缓慢地在桑叶上行走,酣眠,因饥饿而吞食,因疲倦而卧眠,远离阳光、风雨,但大自然还是向它逼近,桑叶把这一切收录了。桑叶——大自然,融为一体,这可以从每一根丝绸上检验。每一根真丝上都有蚕和大自然融合为一的原料,蚕和大自然只不过把这一切合成了一根根具体的丝,再呈现给大自然,也丰富了大自然。有一天,它回到婚床上,是枕套,是垫单,是床罩。制造着人间的喜乐,掩盖悲恸。由此,我们不仅发现万物是相通的,更重要的是采集到了茧——睡袋一一床一脉相承的证据。
春蚕、秋蚕,都是记录光阴流逝的方法,不只是指生命的起止时间。蚕在睡眠中吞噬光阴,它短暂的生长发育期里充满安宁,安宁是它天性的需求,在宁静裹挟的躁动中,蚕一边把养育抽成丝,作为身后之物传之于世人,一边把自己变成美的幻影,从粉蛾中脱身。你应该为那些桑叶而骄傲,一枚桑叶是老死枝头好呢,还是在青青时节进入蚕的内部更有意义呢?桑叶是不知道的,采桑的手却明白无误了。那娴熟而准确的动作,永远迎合着内心,曙色,桑树一阵阵地作痛——生长痛,叶子被反复采摘,同一季节的不同叶子来自桑树。桑树的身体在战栗中获得尊敬,树是盛产桑叶的一张床,每一粒芽苞,每一片嫩叶,层出不穷,兴奋与疼总是与新生与成长伴生着。一个人在压抑、忧郁甚至偶尔产生一种渴望宣泄的愤懑情绪,就是这种样子,在成长中被兴奋与疼痛推搡着,使成长获得了最终的意义——次次地觉醒。
看见蚕越来越透明的身体,会感慨世事变迁的力量,绿汁和叶面的筋络无法去改变另一种生命的质,生命仍然按照各自的生存惯性把自己打开,像打开天窗和谜底,像一根藤蔓和故事中的情节,推到最高阶段,然后消亡。任何一张床都只是一个助产士的身份,它是不可或缺的,但生命是由不得它去决定的,可确确实实生命诞生于床上,哪怕这张“床”是准备给种子的一小块贫瘠的土壤。
床,一个原始又温情脉脉的概念,犹如雪域高原上一条小溪构成——条大河的源头。
河床与胚胎,赐予人类万劫不衰的活力,谁能肯定,它们就不是火山?火山只发生在地貌的某一点上?作为一只蚕,它的每一根丝,就是火山之后对那种冲动的凝固,它是有韧性的,也是有限度的,处于某个定数上,在那奔涌的东西平息下来后,本会感叹一只蚕不会死,它其实是活在每一根丝里。正如一些人永远也不会死,一直活在人人皆知的文字里。
文字里的思想,是人扮作蚕时吐出的丝。人在它的笔画语气里隐身,人又在这样的空间里独守各自命定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