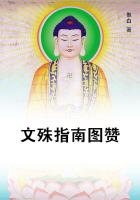我始终有些忐忑。本想讨好老板,谁知热脸焐了个冷屁股,反把他得罪了。挨骂我不在乎,我早不把自己的脸当回事了,不扣钱就行。扣钱没道理。可道理是什么?它长在老板嘴上。
赵燕子去公司门口守着去了。她不可能等见老板,这种小儿科的手段老板还能料不到?我没提醒她,想离她远点儿。卷进老板的私事,那就惨了。自己的事就够头疼了。说来也简单,就是一个钱字。先是宁宁进了皮城的私立中学,一入学就交两万块钱赞助费。我想让宁宁回乡下,只要学习好,在哪儿都一样。肖荣不同意,臭也要臭在城里。肖荣说,人活着为啥,还不是为了孩子?宁宁可是不掺假的,绝对是你周水的种。我拗不过肖荣,什么事都拗不过她。接着肖荣的弟弟开三轮撞了人,对方提出两万块钱的赔偿。那几天,肖荣爹蹲在地上长吁短叹,你就这么一个弟弟,咋也不能看着他蹲监狱吧。我看出来,不拿钱他就住下不走了。再说,也确实不能袖手旁观。我和肖荣的积蓄几乎被掏空,买房的事自然泡汤。钱像一扇大磨,压得我和肖荣喘不过气,我哪有心思和胆量操心别人的事?
可不知怎么回事,我无法把赵燕子从脑里抠出去,尤其是她跪在地上,手忙脚乱往怀里搂杏核的样子,时不时闪出来,撞击着我。
晚上,肖荣一进门就问赵燕子的事。她还是担心赵燕子脸上的伤痕惹出麻烦。我说没有,老板根本没问。肖荣问,老板谢你没?我指了指桌上的广告单说,谢了,派了好多活儿呢。肖荣松了口气,总算过去了,你们老板挺有良心的,你可得好好干。我说,我没糊弄谁。肖荣哎呀一声,我忙问怎么了。肖荣说扭腰了,抱怨我们广告写的太高,登上小板凳才能够着。我说,以后我写低点儿。肖荣说,算了,别让老板找出毛病。我找出一贴膏药给肖荣贴上。我做饭,肖荣躺在床上,但嘴并不闲着,说着白天的见闻。石柳街上的烧饼铺,连着几天没开门,今天公安把门砸开,发现两具尸体,是老板娘和小伙计,已经臭了;一个青皮大白天就讹,把脚伸到自行车下,硬讹了一百块钱;政府门口又有上访告状的,据说三千万的厂子五百万就卖掉了,工人搬着凳子把一条街堵满了。
我耳里灌着肖荣的话,心里却想着赵燕子。这么晚了,不知她吃东西没?难道她整夜守在公司门口?老板干吗要躲她?
肖荣突然问,你发什么呆啊?
我有些结巴,没……没有啊……
肖荣冷笑,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在想那个赵燕子。一回来我就发现你魂不守舍,人家可是老板的姐姐,你就别动那个心思了。
我不高兴地说,你别疑神疑鬼的,她早走了,和我有啥关系?
肖荣挖苦道,没吃上腥,坑的呗。一涉及这个话题,肖荣就变得异常刻薄。
我回敬,真神经。
肖荣毫不示弱,我神经,还是你神经?
我再接茬,肖荣就会上纲上线。她握着我的把柄,总是理直气壮。我扒拉了几口饭,出来。
我的工作其实很简单,抹一层浆糊,往墙上一拍。除了刷写办证广告,并不需要避人。不管是灯光通明的闹市,还是黑灯瞎火的小巷,谁有闲心管你呢?老板说的没错,只要别贴人脸上就行。在居民区,我也照贴。那些保安只是个摆设,只要十点以前进去,他们绝对不闻不问。楼道内的墙壁上到处有我和黑眼儿、小毛子留下的杰作。
我从光明路、师专路,一直贴到黑石路。从黑石路的巷子穿进去,就能走到公司。午夜已过,赵燕子还在那儿吗?我不想掺合她的事,可什么东西拽着我似的,我鬼使神差地游过去。我不知为什么惦记赵燕子,难道真如肖荣所言,因为我有那个毛病?不错,赵燕子是个能引起男人注意的女人,虽然她肤色很黑。但我绝不是为了讨她的便宜。
楼下黑魆魆的。我徘徊了一会儿,还是逃离了。天亮之前,我必须把手里的广告贴完。
一对男女在大街上扭打着。我走过去,他们忽然亲吻起来,声音大得像狗啃骨头。男的四十几岁,女的也就二十出头。我视若无睹。一个个夜晚,我遇到过数不清的奇事、怪事、险事。一次,我走在秀水街上,突然被一个麻袋罩住,接着被扔到车上。我又是挣扎又是叫喊,脑袋被踢了一下,一个声音恶狠狠地说,再叫,把你扔到沟里喂狼。我老老实实地蜷着,不敢再扑腾。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要绑架我,我没得罪过什么人——一个靠辛苦挣钱的哪有胆量得罪人?从我身上也榨不出什么油水。也许他们想割我的肾?皮城有这样的传言,一个男人头天还好好的,第二天肾就被割走了。这一惊,顿时一身冷汗。我被拖到一间房内,取掉麻袋,刺眼的灯光晃得我睁不开眼。他们让我交代藏货的地方。我愣愣的,怎么也反应不过来。后来方知他们抓错了人,还好,又把我装进麻袋送回来。就是挨了几脚,没啥损失。还有一次,一个男人在街上走着,忽然冲上几个人,捅了他几刀。我看得清清楚楚,男人倒下去的时候还向我伸了伸手。我想报警,深更半夜的,没地方打电话。拦车,没一辆肯停下来。我想背他,又没胆量,怕和我扯上关系。后来,我跑到一家洗浴中心,跟保安讲了,保安打电话的时候,我溜了。我不知那个男人捡回命没有。
我从不向别人讲这些经历,谁相信呢?更不敢和肖荣说,怕吓着她。与夜晚的故事相比,肖荣的见闻根本引不起我任何兴趣。
清早,我竟然与黑眼儿和小毛子碰面了。两人的架式明显是找我的。我问是不是有什么事,小毛子说老板转话给我。黑眼儿碰他一下,兄弟,你出一次血,请我俩吃个早点,我在老板面前可没少替你说话。说到这份上,我不能再逃,故作爽快地说,不就是吃个早点嘛,走!终是不放心,问他俩,老板说什么了?黑眼儿说,没诓你,肚子饿了,说不出话。
黑眼儿和小毛子每人要了碗羊杂,我要了碗稀粥,每人两个油饼。对于我们这些干夜话的人,早餐就是正餐。黑眼儿瞅着我说,吃碗羊杂吧,你一个人能省下?我说吃不惯。黑眼儿嘿嘿笑起来。我低头喝粥,听得黑眼儿还要两碗羊杂,用余光扫了扫,黑眼儿很硬气地说,一碗吃不饱,请一次你就大方点儿。我没说话,一顿早餐,黑眼儿和小毛子每人吃了四碗羊杂。这两小子,把一天的饭都吃进去了。不心疼是假的,肖荣一个月都舍不得吃一碗羊杂。
小毛子把一张纸条给我,说上面是公司新地址和老板的新手机号。我失声问,手机号也换了?黑眼儿说,这可是你闯下的祸啊。我苦苦一笑,我也不是故意的。小毛子说,老板说了,再让那个女人找见这个地方,你就得滚蛋。我说,我能拴住她?腿在她身上长着。黑眼儿拍拍我,她要不跟在你屁股后头,绝对找不见,这可是为你好,捧了这么多年的饭碗,别砸了。
老板这么快就把地址和手机号换了,可见他实在不想见赵燕子。老板不会从皮城消失,可对于赵燕子来讲,老板和蒸发没有任何区别。她在公司门口守,能守出什么结果?
一个躲,一个找,我不明白他们是怎样的夫妻,只知自己扮演了一个滑稽的角色。我想得出老板恼火到什么程度。万幸的是,老板没有彻底翻脸,没有踹掉我的饭碗。没活儿干比流汗的滋味可难受多了。老板的担心是多余的,我再笨,也只犯这一次错误。
我狠狠地睡了一天。
肖荣在我屁股上狠拍一掌,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以为肖荣还在为昨天的事生气,撒谎自己不舒服。肖荣马上问,吃药没?不要紧吧?我说不要紧。肖荣神秘兮兮地问,你猜我看见谁了?我呆看着她,知道她会说出来。肖荣常年在烈日下工作,脸上起了不少黄斑,她每天用劣质化妆品厚厚覆盖一层,黄斑倒盖住了,可脸又粗又涩。肖荣催我,猜呀。我懒洋洋地说,猜不出。肖荣说,我看见赵燕子了。
我一惊,差点咬了舌头。
肖荣审视着我,怎么一提赵燕子,你就来精神?
我问,在哪儿看见她的?
肖荣说,就在门口转悠呢,看见我,马上躲了。
我下意识地抓了抓,什么也没抓住。老板预料得没错,赵燕子果然缠上我了。一夜之间,赵燕子回过神了,她守在那儿并没多大希望,跟着我,迟早能见到老板。她想盯我的梢呢。
肖荣话中有话地说,这个赵燕子真是怪,鬼头鬼脑的,肯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我知不能再瞒下去了。越瞒误会越深。
轮到肖荣瞪眼了,你不是编的吧?
我说,我哪有这个闲心。
肖荣愤愤不平,这个女人真讨厌,为啥说是老板的姐姐?这不是往火坑推你吗?你也真是猪脑子,她说啥你信啥。这下好了,她缠着你找老板,你咋办?
我也很恼火,她让我干啥我就干?
肖荣哼了一声,死跟你,跟死你,你还能把自个儿变没了?
我安慰她,我又不笨,不会让她坏我的事,放心!
肖荣说,人倒霉,喝凉水也塞牙……突然顿住,我见她一脸惊愕,猛地回过头。
赵燕子抱着那个花布提包站在门口,如一只惶惶不安的老母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