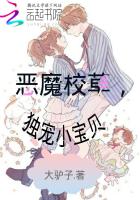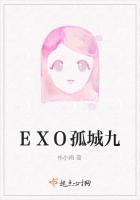综上所述,诏令作为档案文献的性质,即它是未经人改写的过往史事的真实记录,因此具有数据的原始性和内容的多样性之特征,从而决定了它在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中的独特的多方面的价值。具体到宋代文化研究的实际状况来说,我们粗略考察了迄今为止宋代诏令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它在宋代学术研究中的使用情况,应该说,宋代的诏令文献,仍有较大发掘及研究、利用的空间。我们分析了学者们对宋代文化研究中使用诏令文献的现状,相对来说,利用北宋的诏令文献显然比南宋更加充分,这主要缘于北宋有宋人所编之《宋大诏令集》可资利用,搜检比较方便。而南宋的诏令文献主要分散在史籍、文集、方志及笔记小说中,因此极大地限制了学者们对诏令文献的使用,由此对学术研究的不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就宋代总的情况来看,即使有《宋大诏令集》这样一部收文较多的诏令文集,以及上世纪80年代开始编纂、本世纪初出版的《全宋文》等大型文集问世,但从现存宋代诏令文献数量的庞大和内容的丰富性、诏令文献本身应具备的史料价值以及研究者按类查阅文献的便捷性而论,上述诸书皆各有其不足。
《宋大诏令集》汇编了北宋太祖至徽宗时期的诏令,内容涉及这一时期的重大史事。如前所述,该书对于保存宋代文献及对于宋代学术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本书亦有诸多的不足之处,概括言之,主要有:第一,收文不全。根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在有宋一朝的诏文中,南宋约占五分之三多,而北宋所占不足五分之二。而本书所收诏文仅及北宋八朝。且即使以北宋八朝而论,本书所收诏文也仅占这一时期今存诏文的约三分之一。同时,今存《宋大诏令集》在流传过程中,卷七一至卷九三、卷一〇六至卷一一五、卷一六七至卷一七七的诏文已佚。因此,本书只能称为残缺的北宋诏令的选集。第二,收文内容严重失衡。由于编者的尊君观念,故所收诏文偏重于宋代皇室,如许多生下数月乃至数天即卒的皇子的封赠诰文均悉数编录,而对宋代政治进程产生了重大作用及影响的中央政府和地方行政官员的除拜、罢免的诏文,除宰执及部分武臣所录较详外,它如台谏官,转运使、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以及大量的州、府、军、监及县级地方官员,几乎未有涉及。第三,分类不尽合理。本书所分14类中,《典礼》和《政事》所收诏文最多,分量最重,但仅分两类来收此类诏文,或许失之粗略。第四,文字错讹较多。由于本书在流传过程中主要以钞本的形式出现,故文字的脱、讹、衍、倒较为严重。如中华书局本仅据铁琴铜剑楼本和读经庐本互校,就已经校出了相当多的错误。详中华书局本《宋大诏令集》卷后校勘记。而我们又根据《宋史》《长编》《宋会要》《宋宰辅编年录》等史籍,又校正其系年错误达245条,王智勇:《中华本〈宋大诏令集〉系年辨误》,载《宋代文化研究》第二辑。其中尚有遗漏。因此,对于存在长达三百余年、使中华文化达到“造极”之盛的赵宋王朝来说,《宋大诏令集》所收诏文远远不能反应宋代史实的实际状况。
由曾枣荘、刘琳先生主编之《全宋文》,在收录诏令的“全”上弥补了《宋大诏令集》的不足,但诏文的收集尚有不少的遗漏,如我们根据《宋会要辑稿》、宋元人所撰宋人年谱及宋元方志如《咸淳临安志》等典籍,普查到《全宋文》漏收的诏文约50余万字。此外,最近20年来所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其中亦多有《全宋文》未普查之典籍;更重要的是,《全宋文》所收诏文均置于诏令草拟者或皇帝名下,未按内容分类,研究者不能按其所需地查寻相关数据,使其功能受到很大的限制;同时,此类诏文特别是宋人文集中之诏文,絶大多数皆未系年,由此大大降低了诏文的“征史”之价值。此外,该书诏文的校勘和标点也多有值得商榷之处。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认为,将有宋三百年间的诏文悉数收录,重新编撰一部新的《宋代诏令全集》是极有必要的。本编的编纂过程及学术特色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普查。本编的主要特点,就是在收集诏文上尽可能全,在具体编纂过程中,主要针对《全宋文》漏收之诏文,一方面反查《全宋文》曾经普查但因诸多原因而漏收较多诏文的宋元典籍,如《宋会要辑稿》《咸淳临安志》等;另一方面,补查了近20年来陆续出版的有关古籍,如宋、元人所编撰之年谱等。通过这个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全宋文》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导致的漏收诏文之憾。全书计在《全宋文》基础上,增补了3000多篇、约50余万字的诏文内容。
二、校勘。在基本完成普查工作后,我们对所有诏文重新进行标点校勘。其所校诏文主要分两个方面,首先是从史籍、方志、笔记小说等典籍中所辑得的单篇诏文,此类诏文往往在多部典籍中皆有记载,而我们采用的每一篇诏文的底本,大致按照史籍时间早、诏文全的原则收录,其校勘的材料则主要参校现存宋元史籍。其次是宋人文集中之诏文的校勘,主要通过考查该文集的版本系统、源流,确定其工作底本,并通校二至三个版本及其他宋元典籍,如《宋会要》《宋宰辅编年录》《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力求使本编在标点校勘上达到较高水平。
三、系年。众所周知,系年是史学最重要的要素之一,若无系年,则诏令文献就失去了征史之价值,徒文章类也。因此,本编所收每篇诏文皆尽可能系年。由于现存宋人文集中之诏文多未系年,因此,考定诏文系年占了我们较长的工作时间。通过考定现存宋代史籍所载史事,如《长编》《宋史》《要录》《中兴馆阁录》及《续录》等史籍,以及宋元方志、碑传墓志等,准确考定出了现存宋人文集所载很大部分诏文的确切年代;其余无法确定准确年代的诏文,则根据草诏者任职两制的时间,并结合诏文所述史事所藴含的信息来暗分年代。通过这一工作,大大增强了本编的史学价值,其所收诏文,皆具“征史”之用。
四、分类。分类是我们编纂本书过程中感到最困难、亦是费时最多的工作,因为分类既要符合现代学术研究的特点,又要考虑到宋代史实及宋代诏令文献的实际状况,这就对编者学识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且需具全局之观。首先,类目的设置除要做到科学合理外,还须符合现存宋代诏文的实际状况,如:现代之主流学科,未必是宋代学术之重点,故此类诏文反而不多;而官吏三代封赠、宗室除拜等内容,却占了宋代诏文中相当大的比例。凡此,皆需根据宋代诏文的实际情况来设置类目。因此在分类过程中,类目的调整增删时有发生,这就需要对已进行的分类作出相应的调整,有时甚至是牵一髪而动全身的调整。此外,每篇诏文归入何类,皆须编者准确理解其文意,并始终贯彻统一之标准,方能做到以类类文,同一性质的诏文不致分入多处。本编的分类,主要参考了《宋大诏令集》《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以及龚延明先生《宋代官制辞典》等,全书共分“帝系”、“政事”、“典制”三大类,每类下又分若干小类,小类下又分若干小目,如:“典制”类下的“军事”门,又分“兵制、兵器、马政、兵事”四小门;并有部分四级类目,如“典制”类下的“典礼”门,又分“总论”、“郊祀”等目,“郊祀”目下又分“南郊”、“北郊”、“册文”、“祝文”、“青词”、“其他”六小目。同时,诏文的著录采用互着方法,即一篇诏文如涉及两个以上的内容,除在主要门类中著录此诏文外,又在所涉及的其他门类中著录其篇名,并注明“文见某某类”,使研究者达到以类查阅资料的目的。此外,我们又在书后编制了人名索引,尽可能多角度地为研究者提供查阅数据的途径。
本书的编纂计划实际酝酿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全宋文》编纂之际,当时《全宋文》主编曾枣荘、刘琳老师指定由我负责《全宋文》中皇帝文(主要是无法考定出作者而归入皇帝名下的诏文)的整理。其间,曾枣荘老师曾多次叮嘱,要我在《全宋文》的基础上,重新编纂一部内容更丰富、收文更全、包括南北宋在内的《宋代诏令全集》。因此,在编纂《全宋文》的过程中,我随时注意收集有关资料,做了较长时间的学术思考和前期的准备工作,并相继发表了《〈宋大诏令集〉的价值与整理》《宋人文集误收诏令考》《〈宋大诏令集〉佚文考》等论文。但因本书篇帙巨大,出版不易,加之《全宋文》编纂完成后,又相继参加了多个较大的集体项目,亦无充足的时间进行这项工作。四年多前,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庄剑先生闻知此事,和我就此课题进行了反复的论证后,获准立项出版。于是我请曾枣荘、刘琳老师担任本书的学术顾问,两位先生为扶持后学,欣然应允;又请本所王蓉贵先生共与此役,亦获响应。在本书的编纂过程中,常向曾枣荘老师、刘琳老师及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胡昭曦老师三位学术前辈请教,获益良多;书稿接近完成的时候,又幸遇社科院历史所王曾瑜老师莅临川大历史文化学院讲学,使我能在课间就编纂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向王老师求教,王老师答疑释惑,使我对这些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此外,武汉大学杨果教授对宋代官制及宋代诏令等有很深的研究,我在编纂过程中遇到许多难题时,亦常在电话中向她讨教;本所刁忠民教授正在进行《宋会要辑稿》的整理,他也常将在整理过程中有关诏令的考证成果相示。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庄剑先生审读了全稿,不仅校正了原稿中不少错误,并为本书的改进,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可以说,《宋代诏令全集》能够完成并付梓出版,和上述师友们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在此谨致谢忱。但由于我们的学术水平有限,书中肯定存在不少错误,恳切地希望专家学者们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