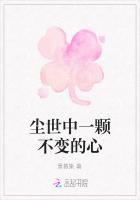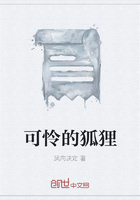赵匡胤生前殚精竭虑,为大宋帝国略定了根本性格局。他省略了革命性的激进与激荡,在邦国治理方向上,开辟了许多后人不及的德政、仁政。他恪守“天下目标”,保持光明心态,以“简、俭、慈”的胸怀与操守推演天下文明,及殁,有《太祖誓碑》传世,为中华政治文明开创了亘古未有的“文明时势”,立德、立功、立言,足可不朽。
春季不得“采捕”
赵匡胤,史称“太祖”,这是他的庙号。史上对他还有一个称号“艺祖”。但为何又称“艺祖”?考据大家顾炎武《日知录》专章说到“艺祖”时,已经认为“不详其义”。但顾炎武也说明:“艺祖”,历代多有此类称谓,不独赵匡胤一人,大略意思应该是“大祖之通称”。我认为“艺”有“开辟”“草创”“树立”“文明”之义,当与“始祖”意思相近。《尚书正义·舜典》谓尧帝祖先为“艺祖”,后人解释“艺祖”之“艺”有“文”的意思。“艺祖”,就是“文祖”,“文祖”就是“最初的祖先”。故称谓赵匡胤为“艺祖”,等于说老赵是大宋始祖、开国之君。
他所开创的大宋帝国,在省略了革命性的激进激荡之后,在邦国治理方向上,开辟了许多后人不及的德政、仁政。在传统中国的帝王“圣君”谱系中,他受到的赞誉和价值影响力,可能确如船山先生所论,仅次于汉光武帝刘秀。
与光武帝刘秀一样,如前所述,赵匡胤也是一个恪守“天下目标”而不是“政权目标”“部落目标”“寡头目标”或“个人目标”的人物。
老赵的“天下目标”甚至涉及生态思想。
《宋会要辑稿·刑法》有一条“禁采捕”,说太祖建隆二年二月十五日,曾经下诏,要求春季不得“采捕”,诏书说:“鸟兽虫鱼,宜各安于物性;置罘罗网,当不出于国门。庶无胎卵之伤,用助阴阳之气。其禁民无得采捕虫鱼,弹射飞鸟,仍为定式。”
这里说的“国门”就是古人说的“九门”。传统儒学经典中就有关于“时禁”的政策规定。《礼记·月令》就说过季春之月,捕猎的用具之类,“毋出九门”。九门,不仅包括都城的大门,也包括“近郊门”“远郊门”以及各类关隘之门。相当于国家各个重要的通行卡子口。“置罘罗网”,都是捕猎工具。在季春时节,这些东西不能在以上卡子口通过。这就是“时禁”。
为何要有“时禁”?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一般人都看到了“生态保护”的生态伦理意义,但更深一层的意思其实是“民生”方向的。因为有“时禁”,所以可以不必竭泽而渔,这样,黎庶所需就总有“余食”。因此,“时禁”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为了黎庶俗世利益而设计的“民生”政策。
但还有比这层意思更深邃的思考,那是伦理哲学方向的设计。在传统儒学理念中,有一种“敬畏生命”的思想,这是直接源自于《周易》中关于“生生不息”理念的思想。在这类思想的照临下,儒学认为“仁”,可普及万物。仁是天地之生气。万物各有其存在之理由,且各有不同之“物性”,或者胎生,或者卵生,等等,在这种差异性存在中,天地间“阴阳之气”各得其所。因此儒学主张“各正性命”,“无相夺伦”。
帝制时代,文明时期往往要在春季下诏,颁布“时禁”。赵匡胤显然继承了这一儒学传统。这类“时禁”对于养成祥和天下,是有功能意义的。
赵匡胤时代,民间已经有火葬。但老赵认为火葬不佳。为此也下一份诏书道:“王者设棺帜之品,建封树之制,所以厚人伦而一风化也。近代以来,率多火葬,甚愆典礼,自今宜禁之。”
古来王道制度设计棺椁和墓葬标识等物品,建立封丘坟垄制度,是为了醇厚人伦统一风化。近代以来,很多火葬,对古礼很多违背。自今以后应该禁止。
老赵不同意火葬。火葬看上去节约土地,其实一样占地,而尸体火化并不比土葬更“低碳”。当然老赵所谓古制,在今天已经有所更化。但老赵当初在葬式问题上的意见是出于“厚人伦而一风化”的,这种圣贤发心,值得今日回味。
老赵的光明心态
大宋对宗亲的抑制,可能是历朝罕见的。太祖太宗之时,宗室近亲受官,亲王之外,一般都到殿直、侍禁、供奉官这类散官为止,出了五服的宗亲,更是有所裁损。这类制度一直延续到大宋末年,所以终大宋一世,没有戚党之患。
皇族中有人犯法,除了少数例外,一般也不姑息。乾德二年,有一宗正少卿赵砺,因为犯了赃罪,就给予了决杖若干、除籍为民两个惩罚。
老赵对自己的光明心态很自信。他憎恶种种卑鄙行径。
汴梁皇宫最初是后梁太祖根据自己的府第修建的,名为建昌宫。到后晋时改名为太宁宫,周世宗居此做了修缮,但与长安洛阳等地的皇宫比较,还是“未尽如王者之制”。于是老赵要求改建,仿照洛阳宫殿的规模。宫殿严格按照中轴线布局。殿成后,老赵坐在正殿,令人打开面前所有的门,可以一直看到宫外。
然后,他对左右说:“这些门也像我的心,哪怕有一点点邪曲之念,人们都能看到。”
因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老赵这种心态的光明与他近于多元价值观的现代意识相关。他知道物之不齐乃是常态,不会为了求得表面的“统一”而削斫物之本性。
宋朱弁《曲洧旧闻》记录一个故实,说大宋建国初,有个管理竹木场务的监官,看到堆积的竹木长短不一,上章要求将场中的竹木一律截削整齐,如此摆放起来岂不更是好看!老赵是又好气又好笑,在他的章奏后批示道:“汝手足指宁无长短乎?胡不截之使齐?长者任其自长,短者任其自短。”你手脚上的指头脚趾难道没有长短吗?何不截了它们让它们一般齐?长的就任它长,短的就任它短!
据记录者朱弁说,老赵这份“御批”,到北宋末年宣和年间,他还在亲戚家看到过。
老赵知道身居九五之尊,纵情快意无人可以制衡;但他更知道,在无理性的恣意之后,很可能正在犯一个错误。世界很大,不是为我赵匡胤一个人的存在而存在。故老赵有了儒学所倡导的“三省”(多次反省)精神,总是在快意之后,自我反省。
有一天罢朝,老赵坐在便殿,很长时间快乐不起来。左右看到他情绪低落,就来问是何缘故。老赵说:“你们以为做了‘天子’是个容易事啊?刚才就为了图一时快意,指挥一事,但现在想来是个失误。所以乐不起来啊!”
还有一次,他去打猎,忽然从马上坠落,大怒,拔出佩刀来将马刺死。但是很快就后悔了,叹息道:“我耽于逸乐,打猎找快活,干的都是危险的活儿。是我自己跌落马下,马有什么罪?”
从此以后不再打猎。他甚至还因为喝酒过量可能的失态而自省,他对左右说:“朕每因宴会,乘欢至醉,经宿,未尝不自悔也!”这样,他对臣下可能不同于他的价值观,也有了宽容。
“生长”出来的风景
老赵喜欢便宴,常常很随意地宴请宗亲大臣、读书人或外国使节。有一次宴请很多读书人,翰林学士王著乘着酒醉喧哗不已。老赵认为他是柴荣时代的大臣,对他很客气,见他已醉,就让人把他扶出去。但王著不肯走,反而靠近屏风,掩袂痛哭。左右等于把他拽了出去。第二天有人来上奏,说王著逼近宫门大恸,是思念周世宗。
老赵说:“这家伙是个酒徒。在世宗幕府时,我就知道他。没关系。一个书生哭哭世宗,又能做些什么呢?没关系。”
宋人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记录了老赵很多这类故实。书中说,“太祖豁达”,得到天下后,有些在老赵“微时”待老赵不很友善的人物,也在朝中做官,赵普就多次说到这些人,准备暗中加害他们,老赵看出赵普的意思,就说:“不可!若在红尘中,人们就能识别谁是未来的天子、宰相,人人都去找天子找宰相去了!世上哪有这类事!”
赵普因此看出了自己的卑污,从此以后不再说这类事。老赵的宽容,不仅在“爱育黎首”(爱护百姓)方向,还在“臣服戎羌”
(以德服人,招徕远方之人)方向。陕西为古秦州,那里有个夕阳镇,生产大型木材,有森林绵亘,看不到边。但这些木材只对当地的“戎羌”部落有利。大宋建国后,有很多营造(建筑)的工程,需要大量木材。尚书高防知秦州,辟地数百里,在当地建筑堡垒要塞,招募兵卒千余人为“采造务”,同时对当地的“戎羌”部落约定:“渭水之北,归戎羌所有;渭水之南,归秦州所有。”这样一来,果然就获得了上好木材数万本,制作了连排木筏从渭水运往京师。后来“戎羌”部落率领帐下部族,从渭水中拦截木筏,杀掉运输的兵卒。高防与“戎羌”大战,史称“剪戮甚众”,还活捉了几十人,捆缚到狱中,上报给朝廷。
但太祖闻讯,并不高兴,反而非常同情秦州的“戎羌”部落。他说:“夺其地之货产,能没有争战吗?这样只会增加边州的困扰!不如罢之。”于是下诏,慰抚当地的酋长,厚厚赏赐他们,抓起来的“戎羌”,都赐给袍带,遣还原来的部落。此举感动了当地“戎羌”好几个部落,都哭着表示感谢。后来更上表,愿意献出当地盛产美材的林场五十里。
大宋王朝的历代君王都从老赵这里继承了天然的宽容精神,就宽容而言,赵宋王朝超过了历代王朝,有资格获“宽容”主题的“集体荣誉奖”。我说“天然的宽容精神”,是说,“宽容”,在老赵这里不是沽名钓誉“做作”出来的风景,而是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风景。
理解老赵的“宽容”,可以看看船山先生的评价。船山在《宋论》中评价老赵,用了“简、俭、慈”三个字。简,就是简洁,不生事。俭,就是俭朴,不奢华。慈,就是仁慈,不酷虐。这之中,首要在“简”。按政治哲学考察,这个“简”字实在是攸关保守主义精神的一个绝大命题。
船山先生的意见是,“求之己者,其道恒简;求之人者,其道恒烦”。由于“烦”,军政反而紊乱,刑罚反而复杂。后世儒者经常“挟此以为治术”,认为要有建树,要建不世之功,要推动历史进步……但正是这类堂皇情绪,反而背离了儒学正见。老赵不如此,行政简、军政简,一切从简,有所不足,自我反省。他不去外求,不去要求他人如何如何,订立什么责人之章程,而是自我做起。要天下俭而不奢,自我先做到俭而不奢;要天下做到仁慈隐恻,自我先做到仁慈隐恻;要天下行事由简,自我先做到行事由简。
太祖做事一向就是崇尚简易。五代时公文处理有“文牍主义”特点,很烦琐。按朱熹的话说就是“须要三省下吏部,吏部下太常,太常拟差申部,部申省,动是月十日不能得了”。赵匡胤办理公文与此不同。
《朱子语类》记录一段故事。说当时蜀中一州军变,这应该是极重要的大事。有人来报要求差人管摄军马。当时朝廷负责军事的枢密院差使使臣公干,拟文上报太祖,内一人姓樊,注云:“此人清廉可使。”太祖就此人姓上点一点,就下批四字云:“只教他去。”公文后面又有附录说明:“杂随四人,某甲某乙。”太祖又批其下云“:只带两人去。”又有附录说明“:某童某童,大紫骝马一疋,并鞍辔;小紫骝马一疋,并鞍辔。”太祖又批其下云:“不须带紫骝马,只骑骝马去。”带个普通马去就可以了。然后即刻通知有关部门作速差遣该州知州,后面有铨曹(主管选拔官员的部门,相当于今日之组织部门)拟写的任命书。大约只隔一二日,到任的文书就到了。枢密院派来的兵马监押才到,那位知州也到了。赵匡胤行文派遣就是如此简洁利落。
老赵要拣选一批京官监督管理在京的各类仓库。这类工作偏重事务性,比较缠人,一般比较爱端着点的官员或小文人不屑于去做,称之为“浊务”。但帝国要运转,就少不了这类事务性工作。事实上,孔夫子早年也曾有过“浊务”工作经历,大宋帝国,有出息的大臣,也往往不惮于做这类工作,因为,他们知道,帝国秩序与结构,有此分工。有一位工部侍郎本来也在拣选名单中,但他认为自己有“清望”,有美好的令名,不愿意沾这类“浊务”,就推辞不干。对这类官员,老赵的方法很简单,回答他说:“惟致仕乃可免耳。”只有退休才可以不去做。如果不退休,就要服从朝廷安排,去做。这个处理方法,省略了很多麻烦,也不必过多解释理应如何。这位工部侍郎为了维持“清望”,选择了退休。
大宋的“天下目标”不是“发展”而是“太平”。一般来说,由官方主导的“发展”程序会出现种种政策倾斜。即使制定政策者皆为圣贤都难免出错,官方的圣贤与民间的圣贤一样,都是理性有限的物种,在“发展”的政策倾斜中,如果杂入“寻租”活动(一般来说,是一定会杂入的),“发展”就成为官方的牟利借口。按自发秩序原理,发展与否,是民间根据“看不见的手”自我推演的程序。官方无须倡导。因为官方不一定知道哪些该发展哪些不该发展,老赵也不例外。他即使身为“圣君”也不能保证国家的发展可以按照他的意图愿景渐次展开。传统儒学基本上不讨论“发展”问题,道理在此。
善言《易》者莫如昭素
老赵不致力于“发展”,将天下目标简洁地锁定为“太平”,一切皆由民间自发地去推演。
乾德二年(964)春正月丁未,老赵下了一道诏书,规定:
县令、县簿、县尉,非公事不得到村落。
这是传统“皇权不下县”的“旧贯”。民间如何“发展”,由民间自行演绎。这种源于保守主义精神、源于儒学“仍旧贯”的智慧,成就了大宋的繁荣。
大宋经由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代百年,基本上奉行一个“简”字,君王们看到天下有不足,自省中反求诸己,故天下安定。到了仁宗朝庆历年间“议论始兴”,延续到神宗熙宁年间,“法制始密,舍己以求人”,从这以后,太祖赵匡胤以“简”为核心的“德意”渐渐泯灭。
船山称:“得失之枢,治乱之纽,斯民生死之机,风俗淳浇之原,至简也。知其简,可以为天下王。”军政得失的枢机、国家治乱的枢纽、万民生死的钥匙、风俗好坏的本源,其道,都是至为简洁的。知道这种简洁,可以使天下达致王道。而那些不懂“简”,总试图有所兴作,并打着儒者的旗帜,其实是泛滥于申不害、韩非子之间的法家做法,距离儒学远甚。
“反求诸己”也是儒学的智慧。
《论语》孔子有言:“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孟子》更反复陈说此义:“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后一个比喻很精彩。说“反求诸己”就像几个人竞赛射箭一样。射箭者要“正己而后发”,如果射箭不中,没有理由埋怨竞赛对手,应该反过来想想自己哪些地方出了问题。因为自己射箭不中,要求他人射中,是没有意义的。之所以能够“反求诸己”,是因为心下先存一份戒惧,知道人的理性有限,不可能在暴戾恣睢中达成正当愿望。故君子有所不为,而鄙夫则无所不为。元佚名《宋史全文》说一事。有个高人名叫王昭素,说此人少年时就读圣贤书,有志行。据说他有一次装修房屋,房间里堆了些木料,有个小偷穿墙而来,因为有木料靠墙,他进不来。王昭素察觉后,就将室内所有的东西扔到房外,对小偷说:“你快拿着东西跑吧,再不跑会有人来抓你啦!”小偷很惭愧,丢弃了东西不拿,逃了。王昭素还著有《易论》三十三篇,很多人跟着他学《周易》。
开宝三年三月,老赵听到了他的大名,就在便殿召见他。当时王昭素已经七十多岁了。老赵问他:“你为何不出仕啊?以至于我这么晚才见到你。”王昭素愧谢说不会做官。老赵知道他对《周易》有研究,就让他讲《周易·乾卦》。
讲到《乾卦》中的爻辞,说到“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时,王昭素敛容道:“此爻正当陛下今日之事!”
于是引援证据,话语中对老赵多有劝谏性质的“微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