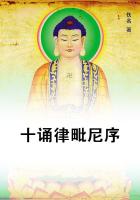临近年下,府上照着以往准备过年诸事。原本倒也没甚复杂,府上统共两位主子,事项都列的清楚。云低看着都是井井有条的,心里却莫名有点燥乱,总觉得要出什么乱子。
云迟已经开蒙,白日里多是在自己院子里听讲或者做功课。除了头一日云低去同先生见礼,后来也不曾再去打扰。今日心乱的走来,不由自主竟走到了云迟的院子。
北地严寒,云低自小长在江南,虽然到了长安三余载,仍是不太能适应这儿的冬天。一到冬日,必定早早裹得厚厚实实。肥厚的冬衣外面再裹一件狐裘,就像是一个圆团子,让人老远就能一眼看出是她。
书房里烧着几个碳炉子,云迟觉得热得晕沉就开了点窗透气。老远从窗户看见母亲过来,就同先生说了一声走出屋来迎。
云迟站在门口等了半天,就见母亲恍恍惚惚的走到半道,忽然顿足抬头看了一眼,像是走错路了一般就要扭头回去。
云迟就喊了一声:“娘。”
云低听到喊声,回头看见儿子站在书房门口处,穿得单薄,连忙急走几步过来挽了云迟的手往屋里带。边走边责怪道:“寒冬腊月的天,怎么穿这么点就站在风口里。”
云迟咕哝道:“屋子里闷热的厉害,出来透透风正好。”
进了屋瞧见教书先生在,云低有些不好意思地笑说:“打扰先生授课了……”
先生是王猛请来的,为人正直、知识渊博,只是对于刚启蒙的孩子颇有些严厉了。平日里对云迟教导少有温和颜色的时候。今日倒是和颜悦色地对云低说话,“夫人不必介意,今日的授课原本也快结束了。小公子聪慧,启蒙课业对他而言很是轻松。”
云低执礼谢道:“小儿顽劣,劳先生费心了。”
先生忙回礼说:“夫人客气,小公子天资出众,加以磨砺日后定成大器,是时吾身为启蒙亦与有荣焉。”
两人又客气几句,先生就起身告辞了。
云迟瞧着先生走远,撇撇嘴说,“平日从未见先生这般好相与过。”
云低好笑道:“先生不好相与,可是因为你太顽劣了?”
云迟心虚道:“我哪里顽劣了……先生教的我都学会了。”
云低摸摸儿子的发顶,“课业学会了固然好,但是娘更希望阿迟能学好做人。先生对你严厉是希望你能成才,玉不琢不成器,先生是为你好。阿迟明白吗?”
云迟低声回,“知道了。”
云低听着儿子闷闷的声音,蹲下身细瞧着云迟有些郁闷的小脸,问道,“阿迟可是因为课业繁重不开心吗?若是太辛苦,将就跟先生说说讲得慢些。”
“才不是呢。”云迟傲然,“那点东西我根本不需费力就学会了……”迟疑一下,云迟又说,“娘觉得魏先生很好吗?”
“魏先生人品持重,学识也渊博。是王丞相亲自看过的,人自然不会差。阿迟何故有此问?”
云迟有点扭捏,“魏先生虽然好,可年纪大了些,人又迂腐……”
云迟一愣,猛然醒悟云迟在扭捏什么。不由好笑,“傻阿迟在想些什么,娘只是敬重魏先生,对魏先生并无男女之意。”
“真的吗?”云迟脸上阴霾一扫,“娘娘不中意魏先生?……我就说嘛,魏先生看着比丞相先生都老了些……”
云低敲了敲云迟的额,“不许这样妄议先生。”
云迟撇撇嘴,“我又没乱说,怎么能算妄议……哼,魏先生对母亲格外亲切,定是仰慕母亲。既然母亲不中意他,以后就务要多与他谈笑。”
云低忍不住想要扶额,这孩子究竟从哪里学来的这些个想法。“阿迟啊,母亲与魏先生只是正常的寒暄,是与人交往的礼节而已……你这些仰慕中意之类的话,都是谁教与你的?”
云迟不在意的挥挥手,“就是听卢四儿他们讲的。”
卢四儿是厨房下面一个打杂的。小伙子正是娶妻的年纪,约莫私下爱与人谈论这些话,不想却被云迟学了去。云低皱眉道,“阿迟年纪还小,还不懂这些,以后莫要再说这些话了,知道吗?”
“阿迟不小了。这些话阿迟都懂得。“云迟辨驳道,“娘以前不是说过,来过我们家的王叔父是娘以前喜爱过的人吗?喜爱就是中意,就是仰慕。对吧?”
完全没料到云迟会突然提起子敬,云低怔了半刻,有些不知该怎么开口。该怎么说呢?当时告诉阿迟,只觉得他年纪小还不懂。现在听自己儿子突然问及,让云低又羞又无奈……以后真的不能再把儿子当小孩子对待了。“那个……阿迟,阿迟说得没有错……”
云迟凝视了母亲一会儿,“那么,母亲也喜爱过父亲吗?”
云低一滞。
云迟有些伤心道,“母亲没有喜爱过父亲吗?所以母亲才会嫌了父亲,与他分开吗?”
云低下意识就回道:“不是的……”
不是的。不是因此才与他分开。实在是因为他们之间有太多误会和隔阂。可是,喜爱过他吗?
若说完全没有,似乎也不是。
当初在豫州,秦军围城他回城寻她时,城门之上共赴生死时……某些瞬间,她似乎已经心动了……若不是后来出现的那幅画,让她不顾一切的回了建康,或许他们早已在豫州完婚。
如果当时她没有看见那幅画,没有离开豫州,好好的同桓伊完成了婚礼。最后还会是这般吗?
也许会完全不同吧……
毕竟是那样一个人,若他有意有多少女子能不心动……
“母亲原本就要喜爱上你的父亲了,可是后来阴差阳错,发生许多事。我们之间都做了让彼此伤心的事……所以我们才会分开……”云低认真地说。
见母亲有些戚然,云迟有些愧疚。母亲说过,提起父亲会令她伤心的。可是因为他愈来愈想要知道关于父亲的事,忍不住就开口了。母亲是不是伤心了?会不会怪自己?……
“娘娘……”一双小手迟疑地拽上她的衣袖,声音有些委屈又有讨好,“娘娘不要伤心,阿迟以后不再提父亲了……”
云低拍了拍云迟的小手,安抚他,“娘不是因为阿迟提起父亲伤心,娘是因为想起了一些过去的事情有些感伤罢了……”顿了一下,云低又说,“阿迟以后若想知道你父亲的事,就问母亲。你长大了,母亲不该断绝你对父亲的渴望。每个人都有父母,让阿迟与父亲分开,是母亲的过错,也是情非得已。但是母亲以后不会再让阿迟断绝对父亲的念想。阿迟以后想问什么,就来问母亲。”
“真的可以吗?“云迟有些不敢置信,“阿迟若问,不会令娘伤心了吗?”
“伤心是有一些,”云低笑笑,“但是过往已经是过往,何必太在意。且况娘有我的阿迟,亦没什么好伤心的了。”
云迟开心地摇了摇云低的衣袖。这样稚气的动作,平时云迟是极少做的,可见是真的开心。
云低不由也心情愉悦起来。
是啊,过往已矣。阿迟都这么懂事了,她还有什么好纠结的呢?
如今她只愿岁岁如今朝。有阿迟相伴,平平淡淡就是幸福了。
窗外簌簌又飘起小雪,衬得墙角处一株盛开的腊梅格外娇艳。隔墙隐隐传来炮竹炸开和小孩嬉笑地声音。正是一幅盛世长安的美景……
而云府正门口,一队风尘仆仆的人马刚刚停住。
为首的男子一袭天青色斗篷将面容遮得严严实实,“就是这里吗?”
一贯高山流水般净澈的声音带了丝暗哑。让一旁侯着的侍从不由坐直身子答道,“就是这里了,郎君。”
男子凝视了府门上的匾额半晌,才转身策马而去。匾额上“云府”两个字由行草书就,笔意潇洒中又添秀气,应是由女子书就。
北风吹过,很快掩盖了一行人马来过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