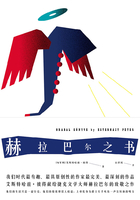补玉心想,这回冯瘫子的小女伴儿怎么是一张真脸?上面没涂着红红蓝蓝的颜色。她跟在车后进了巷子,又跟到了停车场。不知哪来的一辆中巴,也不知它什么时候溜进来的,跨着好几辆车的位置。补玉叫喊着指挥“奔驰”进、退、往左打、往右打……女孩子从车里又露出脸,对补玉说:“靠边点儿!不用指挥!”
“奔驰”舞蹈似的几乎原地转了个圈,然后又是几个果断、短促的动作,从一辆“赛欧”和中巴之间穿过去,一点没商量地停在了场边上。
女孩子跳下车,把补玉吓一跳:一张娃娃脸下面是一个彪形女力士,运动短衫短裤裹着一串串棱角不含糊的腱子肉。至少有一米七二?不,一米七五。女孩子雄赳赳地走到车后,从后备厢取出冯焕的折叠轮椅。轮椅在她手里轻得像纸扎的。她把轮椅放稳,拉开后车门,腰一佝,上身进了车内,双手再一抄,冯瘫子成了个大婴儿被抱起,再被搁置到轮椅上。这套活路女孩子不是在干,是在玩。
“走啰!”她以心情很好的语调对冯焕说道。
“补玉,不握握手?”冯焕说道,脸费劲地向补玉扭过来。
补玉一扭肩膀:“谁跟你握手啊?来了也不上俺们的门儿!”
“这不上门儿了?”冯焕还是以那副欠缺丹田气的声音,那副缺乏真诚的爽气,哈哈哈乐起来。
不过倒不再是欠缺真实的快乐。这瘫子上哪儿找着了真快乐?补玉嘴里全是寒暄,怨冯焕来之前也不打个电话,不然她把最豪华的那间房留给他俩。她看一眼彪形女孩。女孩没在听他们说话,瞪着两只单眼皮眼睛东张西望,望了便提问,柿树一棵能结多少斤?屋檐下的马蜂窝是个空窝不是?给“补玉山居”题字的是谁?……
冯焕照例要了三间房。补玉把女儿叫来,让燕儿打开房门透气,同时扫扫抹抹。瘫子绝不是上这儿来消闲:他没闲可消。肯定是来跟补玉拉扯关系,想把补玉从小曾家赁的宅基地赁过去。
“咱闺女长这么高了?”冯焕看着燕儿说道,“漂亮闺女,一看就聪明!”他可劲挥霍好话。
四个客人坐在葡萄架下打麻将。其中一个女客人说她困了,要去打个盹,另一个女人问补玉肯不肯顶替她打两圈。补玉问彪形女孩,要不要试试手气。冯焕马上替她回答,她才不玩那玩意儿。瘫子冯哥怎么了?很是以女孩“不玩那玩意儿”自豪?
女孩又粗又长的胳膊腿竟异常灵活,帮着燕儿打扫整理,不一会儿,把家具都掉换了位置,更便于轮椅进出、瘫子起卧。所有物什在她手里都没了分量和体积,在她手到之处起落,连声响都没有。补玉再次感叹,女孩哪儿像在干活儿?就是在“玩活儿”。然后女孩拿了双柔软的黑布鞋出来,蹲在冯焕面前,一下、两下,冯焕脚上的皮鞋变成布鞋了。虽然皮鞋布鞋对冯瘫子来说都没有区别,仅仅是打扮那双废脚的,但布鞋毕竟舒服得多。冯焕瘫了的脚在女孩摆弄下十分乖,眼神也十分的乖。冯瘫子可从来没对任何人乖过。
补玉从厨房出来,端着刚沏好的茶。女孩迎着她说不必忙,冯大哥刚才在村口新开的那家茶馆喝了不少茶,喝多茶他不爱睡。女孩给了补玉一个大正面:短短的脸,圆鼻子单眼皮。冯焕长进太大了,找的这位小姐一点不美艳,就是让你看着舒服,像渴了的人看见水、冻着的人看见棉花一样舒服。这年头好看的人不难找,看着舒服的人,绝迹了似的。
得知女孩叫孙彩彩,小名叫“不点儿”,因为她在家排行老小,生下来只有四斤,十岁前都是班级里最矮小的学生。这是晚上八点多钟,冯焕在上网办公,彩彩到厨房来找开水泡草药。那是冯焕擦身用的草药,功效是活血散淤。瘫了的人最怕血脉淤结。
她注意到彩彩挪家具时,把三人沙发搬到大床边,又把另一间屋床上的卧具铺在沙发上。这个彪形女孩跟前面的小姐们不同,不与冯哥同床异梦。趁彩彩在炉前调药汤,补玉问彩彩是不是山东人。是啊,这么大个儿还能是哪儿人?彩彩一口牙白极了,又整齐,一笑嘴巴从东咧到西,肚里的念头都看见了。
吃饭的时候,补玉做了几个应季的菜,凉拌南瓜嫩须,鲜黄花炒木耳,半岁童母鸡炒嫩核桃仁,山溪小虾炒尖椒。瘫子一看葡萄架下的一小桌菜,嘴里的话都在口水里跑:“彩彩给我把相机拿来,我要剽窃版权!”他指鲜绿明黄殷红的一桌。
彩彩真的跑回房间去了。补玉走过来,把蚊香搁在小桌下,又用手里的竹扇轻轻拍了一下冯焕的头,下巴一指屋内:“看你有福气的!”
冯焕当然知道她指什么,笑的时候脸颊竟然红了。五十多岁的瘫子,一向变本加厉地风花雪月,竟还是头一次在补玉面前害臊。
到了第三天,补玉一直等着的话等来了。这是星期一,客人们都走了。彩彩推着冯焕在工地上待了大半天,下午回到“补玉山居”。九月初突然回暑,热得像三伏,一夜间苍蝇四世同堂。冯焕的裤子上不知怎么溅了泥污,被挽了上去,露出一截无动于衷的小腿。当他被推进大门时,那小腿上落了十多个绿莹莹的胖苍蝇。人活着,死去的肢体也会招苍蝇,补玉胃里一阵拧巴。他叫补玉到他屋里去一下,有话谈。
要谈的话补玉全知道,所以她沏了一壶好茶,拿了两个杯子,步子闲闲地穿过院子。葡萄枝蔓耷拉下来,搔了一下她的额头。她还啐它一下:“讨厌!”稳操胜券,她忙什么?
冯焕请补玉坐。他腿上那一大群苍蝇跑了一多半,还剩三四只,在他膝盖上爬爬停停,爬得补玉心直痒。她看出彩彩也受不了那几只苍蝇,手提蝇拍,但始终不朝它们下手。在那死去的腿上拍苍蝇不合适。这是个好心的姑娘,补玉对此已经有数了。
话从询问谢成梁、补玉的公婆开始,绕到全村若干家开客栈开店铺。有了服务经验的农民将来对他那个豪华度假庄园大有用处,他可以付四星级酒店的工钱雇用他们。至于他们现在那种小农经济的旅店,在不久的将来,不打自垮。一旦这里成了旅游胜地,城里人还是城里人,走到哪里他们都要找城里的生活方式。他可怜城里人,也可怜山里人似的,哼哼地笑了笑:“他们对农居的新鲜劲已经过去了,村里还在玩命给他们垒土炕、做土布棉被!”
所以,他冯焕将要开的五星级度假庄园是正规军来了,来收编所有“土八路”。冯焕说着话,一面接受彩彩给他的按摩服务,所以他说到某个字眼,拖长了音,或虚掉一个字眼的尾巴,脸还抽一下拧一下,得劲极了。彩彩按摩很认真,根本没听见他们俩在谈什么。
补玉说那是,那是,谁都知道冯总腰缠亿万。
冯焕正在让彩彩捏后脖梗,捏得头探出去老远,下巴颏松下来。他得劲得口齿也不清了,问补玉想要多少钱,才肯把那块宅基地出手。补玉问哪块宅基地?冯焕马上斜她一眼,说这样不好,别抵赖嘛,抢先赁了那块地,不就想在他的庄园里做绊脚石吗?
补玉笑嘻嘻的,心却跳得她微微恶心。补玉够惨的,花三十万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做块绊脚石。昂贵的绊脚石。挪开它可更加昂贵,她狠狠地想。
“你要多少钱?没事,只管说,你有要价的自由,我呢,有还价的自由。”
补玉看出,冯焕已开始紧张,能走动的话,就是坐立不安、满屋打转。她在心里笑死了:腰缠亿万他也怕补玉这块绊脚石呢!万一这是一块要他破费一百万、两百万才搬得开的绊脚石,对于生意场上常胜的冯焕来说,是多失败的纪录?就是亿万身价,一百万也不能看成小数。
“那我还得跟成梁商量商量。放心冯哥,您又不是外人,外人成梁没准真给他来个狮子大开口!”
“现在就把成梁叫来吧。”冯焕说道。正因为他瘫,所以他往往叫谁谁就得到。
“谁知道他上哪家串门子去了。”补玉存心急急他。
“一共三十四户人家,一户一户跑也找来了。你去找找他!”他对补玉说。
正因为他瘫,他发号施令才这么理所当然,这么威风。正因为他是瘫子,人们才心甘情愿被他支唤。不过他今晚支唤不了补玉。
“急什么呀冯哥,我和成梁今晚商量完了,明儿准给你回话。”
“你是拿谢成梁挡我吧?小谢什么时候那么当家呀?”冯瘫虽然还在摆风度,已经有很大的脾气在话音里了。“我上这儿来,你以为我真是休闲的?”
“那您干吗来了?”补玉的脸在说:可怜见的您什么都有就是没“闲”。同时她又想笑:要是他不瘫,他也不会这么忙。
“我就是想住下来,好好跟你谈宅基地的事儿啊!”冯焕气不打一处来。怎么会被误认为是闲得长毛,住到她的山居安享中年来了?一个大忙人,被错看成闲汉,这可让他想不开,因为这等于是抵消了“忙”中的重要性。
“那冯哥您早该说一声!怎么住了三天才张口?我这就去找成梁商量,明天一早一定给您个答复。”
冯焕张张嘴,又没说什么。补玉走出门时,正瞥见那彪形姑娘在给冯焕吹茶水。她的手又厚又大,端茶杯全身小心,就怕不小心把茶杯捏碎了。她给冯焕按摩恐怕花一多半力气在下手轻柔上,用很大劲儿提着劲儿,不然冯焕也会碎在她一双大厚手里。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补玉到豆腐坊去买刚出来的豆腐。回来见河对岸一个金鸡独立的身影,一脚立地,一脚蹬天,两腿拉成一条线。彪形女孩在干吗?一眨眼,她又换了条腿,碗口粗的腿被她轮番玩,补玉看得让箩筐里的豆腐滴湿了鞋。上午她跟冯瘫子说,没想到他这回找了个女大侠,冯焕朝正在院里跟燕儿捉迷藏的彩彩投了一眼。多少温柔在那一眼里!
“还什么事不懂呢——一个孩子!”冯焕炫耀着。
“从哪儿来的?”补玉轻声问。
“从报纸上来的。”冯焕轻声答。
“吃过苦的孩子。”
“可不。”他突然一愣,“你看出来了?”
补玉笑着摇头:“看不出来。来我这儿住店的人,个个的我都看不出来——趁不趁钱呀、是不是夫妻呀、有没有偷我一条浴巾要不就一个烟缸啊,我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她笑起来。是那种能在男人那里办成很多事的笑。
冯焕一点也不笑,要她明白,她笑得多么妖在他这儿也甭想办成任何事。“我可是能看出你来。你在想啊,这瘫子钱包不知有多深,得好好地挖挖。”
补玉的脸不好看了。肯定很不好看。冯焕却哈哈大笑,笑得后脑勺向后一个劲儿仰去,这就是他动作的极限,等于一个正常人笑得四仰八叉。
“说——想在我钱包里挖多深?跟小谢商量好了?五十万?六十万?说嘛。”冯焕的大笑把彩彩惊着了,从藏猫猫的玫瑰花丛后面走出来,朝屋里打探。冯焕朝她摆摆手,意思是“玩去吧”。
“我们成梁说了,赁出那块地,这个店就关门。我们老老小小省着点,够吃到孩子们考学校了。”她看到自己的话在冯瘫子脸上收效,她慢条斯理,他五内俱焚。
“你要多少能吃到孩子们考学校?”他紧张地盯着她。
“怎么也得一百万吧。”
“曾补玉……”冯焕急得舌头也要瘫了,“你存心毁我哪?!”
“谁毁得了您呀,冯哥?”补玉现在是一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那种女子模样。
“你们祖祖辈辈的淳朴民风,就是让你这么干的?!”
补玉笑而不答。她的笑其实是说:“可不。”
“我们这样怎么谈?”
补玉感到侧后方一股热烘烘的气流。彪形女孩听见冯焕拔高调的话,赶紧来看看,看她那海碗粗的腿、茶杯粗的胳膊能帮她冯大哥什么忙。她热烘烘地一身就绪,冯焕对她摆手她也不走开接着“玩去”。
“那您还价呀。”补玉说着,朝彩彩扭了一下头。彩彩在场,她莫名地不自在起来。
“没事吧,冯大哥?”彩彩问的是冯焕,瞪的却是补玉。她自己那两条又粗又长的腿,她玩得那么好,补玉到她这儿,她两下就能把补玉玩趴下。
冯焕说:“你出的这个价就让我生气!”
补玉说:“那您还个价,让我也生气呀!”
冯瘫子又对彩彩摆摆手。这次手不是大哥的手,而是主子的手:让你走你就走,没什么商量。
彩彩退了出去,却不再玩耍,站在葡萄架下接着观望这屋的冯焕和补玉。
“您自己说的,开价还价,买卖自由!”补玉说道。
“假如你不是跟我做交易,就是存心捣乱,我干吗陪你玩?还价还有意义吗?”
“冯总,您在我店里住过好几次,我是存心跟人为难的人吗?问问街坊四邻,曾补玉什么时候存心跟人捣乱过?这是我的村子,我在我自个儿地盘上开店,挣一口不干不稠的饭吃,不图别的,只图孩子们长大能考大学,一辈子也有一口不干不稠的饭吃。您在这儿开五星级、六星级庄园,我们再想吃饭要靠您赏,是您在毁我们,还是我们在毁您啊?”
“好,这话说透了,说穿了——你是觉着我要毁你,所以你干脆先毁了我。曾补玉,我不是什么厚道人,你知不知道?”他被自己的话呛住了。
补玉看着他,一点表情也没有,但意思却告诉了他:我从来没小看过您把您看成善茬儿。
彪形女孩彩彩再次走进来。她这次顾不上用眼睛来顶撞补玉的眼睛,赶紧替她主子摩挲着胸口。
“有话好好说,别起急,啊?”她轻声对冯焕说。
这种女人!一份体贴、一张笑脸、一记抚摸都不免费,都记在冯瘫子的账单上。冯瘫子欠得多了,最后终归会被这样的账给陷住,给埋了。于是,彪形女孩就将得到一个亿万的账户和一个什么雄性事物也干不了的冯瘫子。就那么回事。没想到她五大三粗,没心没肺,反而比那些浓妆艳抹、水蛇腰流水肩的妖冶小姐们更算计。彩彩嘻哈地说过自己体重是一百六十斤,原来是一百六十斤的一个大钓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