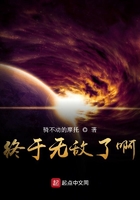“古人诚不欺我。”金小银一声长叹。
秋喜拔高音调,手掌摸了额上的汗,甩了甩,“都什么时候了,姐姐还作诗。到底怎么办啊?”
“还能怎么办,逃命呗。”她将腰上的银袋解下来,塞给秋喜,交代道,“那空菜筐放在菜场占摊位了,以为明天还要去的,你得空了去把筐弄回来。”
“姐姐,你这是……”秋喜眨眨眼,迷惑不解。
金小银吧钱袋塞到秋喜手里,拍拍他的肩,叹口气,“我的家当银杏知道放在哪里,这钱袋里有一百多两银子,加上我那些积蓄,够你们三个赎身出来,别问我哪儿来的钱,总之是干净的银子,你们好好用。”
秋喜听出这话不对劲,急忙把钱袋往她手里塞,她一摆手,推了回去,“傻秋喜,我可不能再跟你们一起了,替我照顾好银杏和连翘,等这事儿过去了,我一定想办法联系你们。”
金小银没把握自己还能不能回得来,说这话不止是安慰秋喜,也是为了安慰自己。看着秋喜那双满是不舍和失落的眼,心里酸酸的,喉间一梗,眼泪涌了上来,烫得眼眶疼。
“钱袋收好,我走了。”
秋喜拉住金小银的袖子,哭了。金小银从没见秋喜哭过,他刚进柳府来时,个子又瘦又小,面黄肌瘦,总是让别的小厮欺负,有一次他们拔了秋喜的衣服,把他倒吊起来拿蛇去咬他,让金小银发现了,立马请了夫人来替秋喜做主。那一次他身上被咬得皮开肉绽,几乎就要死掉,也没见他掉过一滴泪。
之后刘妈也常使坏,折磨他们,但也从没见秋喜难过。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好了好了,都快十四的人了,是男子汉了,哭什么。”金小银一边说,自己先哭得两眼红肿,抬袖子擦了泪,握住秋喜的手,“我会回来找你们的。”
“说话算话。”秋喜红着眼,定定的看着她。
金小银笃定的点头,他才略略安心了些,放开攥在手里的衣袖,将钱袋推给金小银,“姐姐收着这钱袋,要是以后有难处,记得回来找我们。”
“这钱本来就是给咱们赎身用的,你不拿,我就去自首。”
秋喜还要推,金小银立马抽身往相国府正门去,秋喜一惊,拦下她,当着面将钱袋装好,眼眶又红了一次,从袖子里掏出一锭银子,握进她的手心,“姐姐保重,别忘了答应过秋喜,要平安回来。”
“放心。”
离别是最伤感的,金小银不喜欢离别的场面,也不愿意多留,朝高墙之上看了一眼,墙里面就是她穿越来后,生活了三年的地方,一时间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就要离开,还有些不舍得。
低下眸子,抓了秋喜的肩,将他转身去,“回去吧,别回头。”
秋喜点点头,她也转过身,擦了泪,大步向前,没有回头。转过街角,向皇城南门的方向去。
脚下步子很快,但心里却是一片萧索,说得文艺些,从此她就是个亡命天涯的人了。说得俗一点,以后她就是个通缉犯,不能明目张胆的过日子,得学老鼠住在谁都不会发现的洞穴里。
金小银站在皇城门口,应着城门外吹来的西风,一把鼻涕一把泪,哭得双眼肿成一对桃子。就那么哭了半个时辰,眼泪也流干了,委屈也都流出去了,深吸一口气,揉了揉红肿的眼,摊开手掌,低头看里面躺着的一锭银子——这个加上鞋底的七个铜板,就是她所有的家当了。上一次这样一无所有在大街上吹风哭鼻子,还是外婆去世的第二日。那是深冬,很冷,她只穿了一件外婆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旧棉袄,冻得浑身发抖,兜里揣了一张五十,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连外婆都没有了。
深吸了口气,脱了鞋子把里面的铜板扒拉出来,和那银子一起放进衣袋里,从今天开始这些钱就要有计划的用了,不然在找到安身之处和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之前,她就得先饿死。
出城去么?抬眼望了望城门外一排等客的马车,十个铜板的车价,最远可以走到离皇城三十里外的白桥镇,那是个平和安宁的小镇,去那儿生活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她不舍得离开皇城,因为这里有对她来说最重要的三个人。
是谁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不如去相国府谋个差事,对了……相国府不是招尿桶搬运工么,工资比她在柳府厨房里还高出两倍的说。听说那工作的人,大家都忌讳,见了面也要避让三尺,也就不怕有人认出她来了。
就这么定了!
金小银掉了头,往相国府去,路上顺道去夏老伯的摊子上买了两个芙蕖糕垫垫肚子,跟夏老伯闲聊了一阵,又香又软又热的芙蕖糕下肚,郁闷的心情都不见了。夏老伯倒了一碗煮好的浓茶给她喝,苦味散开之后,嘴里回着淡淡的清香,顿觉神清气爽。
早市已经消停下来,没什么客人来往,她在夏老伯摊子这里歇到将尽正午,才别了夏老伯,拐进了小巷子,往相国府去。
话说到了相国府那道小门前,那张招工的广告竟然不见了!金小银心里顿时一空,左顾右盼,围着院墙来来回回的找,也找不到那张告示。正碰上路边过来一个丫头打扮的人,这行头应该是相国府的丫头,她上前拦下那人,指了指那边的小门,“请问,贵府还招吉童么?”
那姑娘一听这人是来应聘尿桶搬运工的,当即推开三步,斜了眼将她上下打量了一遍,这小伙子虽然脏了点,模样还算长得清秀,手脚也还健全。姑娘眨眨眼,细声细气的问,“我看你好好的,干嘛要来做这个?”
“说来话长。”金小银也很无奈的说,看看眼前这位姑娘,穿着小粉裙子,戴着碧玉簪子,脸上扑了香粉,嘴上还擦了红红的胭脂,一定是伺候身份高的主子。再看看自己,穿着男人的宽大衣服,灰头土脸,没一点女孩子的样子,不免又一阵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