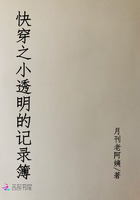乞丐也看透了方先生的尴尬,急忙说:“天底下没书的人很多。只是,我没想到这家房屋的主人也会没有。不好意思,打扰您了。”说罢,抬腿欲走。那溢于言表的鄙薄与不屑令在场的人都很难堪。
一直在一旁不动声色的申小姐急忙走上去,将随身携带的一本文摘读物递给乞丐,和颜悦色地说:“也许,你会喜欢这本书,不妨读读吧。”
乞丐接过,连声道谢,然后席地而坐,旁若无人地读了起来。
这天送走申小姐后,方先生满腹心事。看来,他想博得申小姐的满意尚有一定的障碍。
不久的一天,方先生突然作出决定:“阿伟,送我去书店。”
在书店经理室,方先生将一张二万元的支票拍在办公桌上,对接待他的小姐说:“愿意与我做成一笔大生意吗?”
小姐说:“当然愿意。不过,我们这儿无什么大生意可言,只有书,您任意选吧。”
方先生将支票推置小姐案前,说:“我懒得选,拜托你了。下午两点,我来取货。”
小姐惊奇地盯着眼前这个财大气粗的人,不知如何应付。当方先生准备调头而去时,她才醒过神来追问道:“您想要一些什么书呢?”
“只要是书,只要有名气。”方先生头也不回地说。
下午两点,我们驱车来到书店。那位小姐将支票还给方先生,并说:“很抱歉,我们经理不想接受这笔生意。”
方先生再一次愣住了。他咆哮道:“你们的经理呢?让他出来见我。”
“不必了。”小姐笑笑,“我们经理看过支票,就知道您是谁了。他要我一定转告您:本书店没一本可以束之高阁的废书。每一本书都是有灵魂的生命,都有情有独钟的恋人,最终总会归其所爱。”
元城赌王
赵明宇
安大山出了桃花坊的门槛,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正是阳春三月,远远望去,元城的上空已是飞红流翠了。他的心里却飘过一片凄凉。
桃花坊是元城很有名的窑子,安大山来这儿是为了一个名叫唐三娘的窑姐。怎奈那唐三娘千娇百媚,端的是娇艳的小美人。在温柔乡里走一回,安大山的骨头都要化了,酥了,生出一腔豪情来,发誓要赎回唐三娘,独占花魁。
可是,钱从哪里来?只有去赌一把了。
安大山是在赌场里泡大的。他手里整天提着一把长嘴大铜壶,跟在吴老爷身后端茶倒水。吴老爷毕竟是有身份而且赌技很高的人,他目不斜视地坐镇赌场,内心风起云涌却不露声色,常常气定神闲处乱不惊地转败为胜,被誉为元城赌王。元城临卫河,往来客商繁多,赌场生意自然红红火火。闲暇,安大山便抱着大铜壶看得眼神儿直勾勾的。时间长了,安大山对于吴老爷的赌技看出了门道,每一招每一式都熟记于心。
有时候,吴老爷示意安大山也来碰碰运气,安大山就连连摇头。无论别人如何怂恿,他都置若罔闻,微微一笑说还要尽心侍候客人。吴老爷赢了,便会赏给他几个小钱,他就把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狗一样作一个揖,连连说几句感激的话。
安大山一日不见唐三娘,便会觉着缺精少神,像是一颗血疙瘩心被人偷走了。
坐在赌场上,安大山盯着骰子,脑子里还萦绕着自己和唐三娘缠绵的事。一口气赌下来似有神助,竟然出神入化,掏空了一个又一个往来客商的腰包。有几个公子哥儿不服气,专程找安大山来赌,安大山一连几个杠上开花,盛气凌人,打得公子哥儿落花流水。
终于,吴老爷坐在了安大山面前。
几局下来,吴老爷的脸色阴了。安大山的眼睛像血一样红,下注白银一千两。
三个六点让吴老爷的胡子一抖一抖的,眼神像斗鸡眼一样,好半天没有回过神来。吴老爷把一千两的银票推给安大山时,吐了一口血,再也没有站起来。
安大山被奉为元城赌王。
安大山在元城牛市街买了一套房子,兴高采烈地来到桃花坊,把三锭银子甩给老鸨,牵着唐三娘的手回家了。
男儿当风流,安大山好不快活。
在元城,赌徒们听得安大山的大名,纷纷告退。安大山并不着急,骑一匹快马,三五天到顺德府或者到济南府去一次,天亮收场。到日头将午,便回到家来,把马匹拴好了,唤一声“娘子”,顺手丢下一个沉甸甸的包裹来。安大山到偏房沐浴,然后抱着唐三娘你死我活地一番折腾,蒙头睡去。
唐三娘说,官人不如置买田地,好好地打发日子,莫再去赌了。
安大山说,已是欲罢不能。
一日,有一个头戴貂皮帽的汉子从内蒙古贩卖马匹途经元城,听说还有安大山这等奇人,便慕名寻来了。当时大雪纷飞,掩埋了路径,旷野天寒,朔风如嘶。一阵砸门声把安大山惊醒了。开了门,陌生的客商含笑作揖说,慕先生大名,特来讨教。
安大山眼睛眯了,打量客商,知道来者不善,抱拳说,不敢不敢。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客商说,不必,就在这里吧。
安大山请唐三娘取银子出来。客商说今天不赌银子,赌人。
赌人?安大山心里咯噔一下。客商说,我以一千匹马与你赌唐三娘,马匹就在门外。
安大山顺着客商的手指方向望去,果然看到一群马站在远处的雪地里。
安大山说,赌人就赌人。说白了,赌场如战场,赌的就是胆量。安大山笑笑,遂回房中取一把利刃藏于腰间,心说,赢了便罢,倘若输了,岂能与你善罢甘休?
安大山手持三颗骰子,顺手撒去,排出三个六点,乃是赌场上被称为豹子的最大点数。
客商微微一笑,从囊中掏出来一把黄豆,抛开了,落在地上,竟像一个方阵,左看右看都是豹子,竟是罕见的双豹。
安大山头上的汗水下来了。
只听得门环响动,唐三娘一袭红衣款款走出来。安大山唤一声“娘子”,羞得低下了头。
唐三娘把十八颗黄豆含到嘴里,香唇轻启,黄豆喷出,三三成行,乃是赌界传闻的豹中豹。
客商和安大山都看呆了。安大山惊奇的一声“娘子”打破了沉寂。
客商说,三娘,我来赎你了。
唐三娘说,我已经不欠你的了,你走吧。
唐三娘又向安大山说,奴家在官人眼里就值那一千匹马?
安大山取出明晃晃的利刃,寒光闪过,四根手指齐刷刷地落下。
雪地上像是盛开了一片梅花。
纸枷锁
远山
西太后过生日,男旦艺人花木春去赴堂会,一路上脸色有些沉重。
木春不是第一次这样奉旨而来了,引路的太监已经熟悉,就劝了木春几句,倒不是因为木春的脸色不好——到了太后面前想必木春的脸色会好的,而是木春并没有穿红衣服,这可是最忌讳的。
木春家人刚刚去世,太后招呼哪敢不来,可衣服实在是来不及换了。木春这样对太监敷衍了几句。
堂会在东厢的小会堂开始,满布红色,处处笑脸。婉曲曼歌,韵味绕梁。花木春的脸上自然是笑意盈盈了。但他那衣服早被太后看见了,太后并不言语,只是让花木春靠后了再上台。
中间休憩时,太后赐予花木春两样东西。先是鞭子,当然都是下人传的话:知道为什么赐你这个东西吗?木春一脸的惊诧,如实说:不知道。下人说:我们也不知道。你预备好谢恩就是了。
趴下一顿抽。花木春硬是没敢吱声,默默忍了,站起来。开始第二个赏赐了:今儿个,你甭唱别的了,唱一出《戴枷行》。木春一惊,这可是老佛爷的生日堂会呀?不敢出声,只愣怔瞧着太后。
太后说话了,天高海阔地说了两句,大意是:支撑这么大一个家累着呢,内务外交像戴了枷锁一样子劳神费心。什么生日不生日的,就来一段《戴枷行》好了。
下半段的堂会开始了,花木春正在后台准备着呢。太后跟前的人手里拎了个东西过来传话,说:咱今儿个,为了让你演得逼真,特让你戴上这个上台。
接过来一瞧,木春当时便心惊肉跳。你当是什么?原来是一副纸糊的枷锁。
那差人瞧见了花木春脸色不太舒服,就说:一个纸糊的东西而已嘛,重也不重,硬也不硬,想必是一撕便破了的。
此时,木春的心才稍微定了一点,他昂起头,想说出来难以从命的话,还没出口,那差人就搬出了太后的意思——没别的辙儿。
压轴戏,临到花木春上场了。乍一露身,举座皆惊。
唯西太后气定神闲,微露笑意。
听那台上,悠扬唱腔,婀娜身姿,溢满了楚楚动人的病态男旦之艳美绝伦。一曲终了,谁敢出声啊。太后给了个满意的手势,下面的人才放下了一颗心。
不用说,又要赏赐了。各位名角一一领赏而去。
太后留下花木春不放,眼神恍惚起来。下人纷纷退去。才一会儿,太后厉声唤回太监。
太监低眉见了太后的脸色,禁不住一抖。而花木春呢,满脸奇怪的神色,低头不语。
赏——太后的声音是打了弯的,仿佛在空中划了一个弧线落了下来。太后要太监取来花木春演戏用的纸糊的枷锁,对花木春说:这个就赏给你了。
看得太监们一头雾水,太后要愣在那儿的花木春过来,戴上它走一圈。太后指指花木春的脖子要问什么,没出声。太监看花木春局促的样子,恐怕再惹了太后,悄悄上来告诉花木春,太后是问你脖子感觉如何。
也不等花木春应答,太后就笑了几声走开了。
不安地回到了家,花木春轻轻放下西太后赏赐的东西。
连着多少天,花木春总感觉脖子上有问题,特别是戴了纸枷锁的部位,奇痒无比。找人给看,人家都说看不出来什么呀。找了多少人看都是一样,可脖子那部位就是难受。
晚上做梦遇上了太监,太监说都怪你自己……怪自己什么?人家不说明白。
花木春烧了好几炷香,嘴里念念有词,仍不管用。那天烧香以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那纸枷锁烧了。
纸枷锁烧了,烟灰在空中袅袅着……看过去,似乎和一般的纸没什么不同,用纸灰抹自己脖子难受的地方,痒是不痒了,可是为什么却越来越痛呢?直到痛得昏过去了。
不久,花木春死了。到底是自杀他杀,还是被吓死的,人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脖子上有道深深的痕迹。至于如何形成的,始终令人费解。
德富老汉的最后结局
胡炎
德富老汉给牛喂足草料后,便开始拉上牛去地里做活。在这样一个晴好的秋日下午,干瘦硬朗的农民德富老汉有着很好的心情,他和他多年相伴的老牛悠然地踩着村路往自留地里去。所有的乡野风光看上去都熟悉而亲切,就像他身上的一块皮肤,沙河依旧在潺潺流淌,细密的波纹永无疲倦地揉搓着那轮干净浑圆的日头,麦场上一座座麦秸垛依旧散发着新鲜的麦香。有几条狗在玩着游戏,有一条正值青春的母狗显然已经懂得恋爱了……德富老汉就这样和他相依为命的牛走过了他稔熟的田园风光的一部分,口里喷着辛辣厚重的旱烟,不时很有资格地咳嗽一声……现在,他和老牛已经进入了那片待耙的自留地,走入了他生命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地方,当然,也是这篇小说的重要场景。
这会儿年逾六旬德富老汉打量着遍布麦茬的田野,温煦的阳光在田野上跳荡,这是个让德富老汉愉快而情意缱绻的地方。德富老汉每当在这片土地上耕种和收割的时候,总能闻到先辈们的汗腥味和臭脚板子的浓郁味道,德富老汉便会陷入一种痴迷,觉得自己正走进一个恒远的梦中。而每每最后提醒他的,还是几声沉实绵长的牛哞,德富老汉觉得牛哞是这世间最美好的语言。
德富老汉喷出最后一口烟雾,把长长的烟杆子在地上磕了磕,而后深情地打量着他的老牛。这是一头温顺无比的动物,对于鳏居多年的农民德富老汉来说,它简直是一个宠物,是与他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一部分。在漫长的岁月中,老牛以它的温顺、沉默和勤劳给德富老汉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德富老汉很难想象假如有朝一日失去了老牛他会是什么样子。
这会儿,天上的那轮暖阳正在缓缓西移,为德富老汉的人生烘托着一个结局前的氛围。这是一种难以言状的祥和,博大而宽厚,具有无比的包容性。当然,德富老汉对此浑然不知。他审视着他的老牛,他发现老牛的眼睛比平常更亮一些,一束犀利的光穿透了他。德富老汉并没有往别处想,他只是感到老牛是越活越精神了。老牛冲着德富老汉点了点头,德富老汉非常满意地笑了。这是他亲自调教出的牛,德富老汉还记得当初买下它时的样子,那时的牛是个烈性子,很难驯服的,德富老汉用鞭子蘸上水好一顿抽,牛哆嗦了一阵,便再不敢耍泼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德富老汉细心地照料着日渐衰老的牛,夏扑虻蝇,冬裹棉褥,虽然还时不时要抽它一鞭子,牛也是毫无怨言的,只是更加肯卖力气。德富老汉想这牛是通人性的,它晓得打是亲骂是爱呢。
德富老汉向他的牛走去,开始为它套上耙犁。德富老汉右手攥住了鞭杆子,说:
“伙计,该干活了。”
秋日的下午一片静寂,德富老汉看到阳光在田地里流溢,金灿灿的很合他的意。在田野的东北方约十五米处,就是德富老汉先辈们的坟茔,草木丛密十分气派,德富老汉想这会儿先辈们也许正看他耙地呢,他是他们的后辈。是铁打的庄稼汉,不会丢他们的人。德富老汉向往着在这片田野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而后到先辈们的中间去聆听他们对他这个后世子孙的评价。那评价一定是不赖的。德富老汉想。德富老汉曾为自己设计过几种结局,一种是寿终正寝;一种是正在田里做活便蓦地倒下,永远融入泥土,和先辈们一块扎根在这里,看世代沧海桑田,看自己的后辈们犁地;还有一种最美满的结局是和他的老牛一块静静地老去,相拥辞世,永不分离,为那边的列祖列宗们牵去一头有情有义的牛该是多美的事!这三种结局都让德富老汉坦然,这是一个温馨的境界。
德富老汉吆喝了一声。德富老汉的吆喝今天显得格外尖锐,划破长空,阳光也在震荡中轰鸣。阔大的田野渗进了德富老汉的声音,使德富老汉显得十分突兀而伟大。但是牛站着纹丝不动,好像根本没有听见德富老汉的吆喝。德富老汉感到了某种蹊跷,他又吆喝了声。整个秋天的下午被他的吆喝声撕开了一条口子,但是牛仍然无动于衷。德富老汉觉得忍无可忍了,他为老牛今日的反常举动大为不满。“畜生!”德富老汉骂了一声,气急败坏地奔到牛头前,劈头盖脸地抽下了鞭子……
这个秋日的下午在这里开始定格,德富老汉走进了他最后的结局。就在德富老汉的鞭子抽在老牛脸上的时候,老牛猛地往前一冲,将德富老汉顶在了地上,然后,老牛前腿跪在德富老汉的腹部,用尖硬的犄角挑开了德富老汉的喉咙……
几乎无人可以接受这个结局。德富老汉血肉模糊的身体被送进了先辈们中间,只是那头老牛被亲戚们打死后并未送去陪伴德富老汉,而是被剁成块分给村人吃掉了。
秋日一派祥和。
台球张
萧磊
我叫他张老板。其实,他比我这个穷学生,多不了几个钱。
他在骆家塘的街头,守着几张台球桌维持生计而已。的确,只是维持生计而已。
按年纪,他其实也可以做我的“伯伯”了。
大学快毕业的那个学期,陆陆续续有用人单位来我们学校招人了。招聘单位,除了看看相貌以外,更多的就是看看简历和分数。说起来很惭愧,这四年大学,我把很多时间都奉献给了我那温柔的被窝,或者是金华的大街小巷,还有就是那么一大堆文学书和我自己藏在抽屉里的破小说。所以,我的简历上空空荡荡,我的成绩单上,也没有像父亲拾掇农田那样挂满黄灿灿的稻穗,只剩下“补考”、“重修”的屈辱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