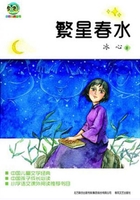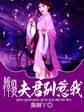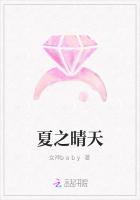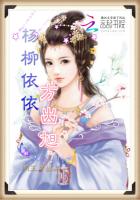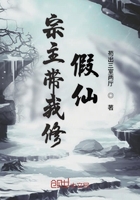一
1921年,对于徐志摩来说注定是一生中最有意味的一年——这一年里他不远万里地将妻子张幼仪从国内接来英国,但几乎与此同时,一位名叫林徽因的江南才女又走进了他的生活。
林徽因后来成了一位著名的建筑设计师,一生中设计了许多堪称经典的建筑,也参与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国旗,但是,事实上她毕生最精彩的设计则是诗人徐志摩一生的命运。
在中国现代文人中,徐志摩可谓是最独特者之一:作为一个人,他生性单纯而生活又极其复杂;作为一个诗人,他艺术人生可谓精彩纷呈而最终命运又极其不幸和悲哀。然而,如果说他人生中所有的精彩和复杂像一出大戏,那么在这一年里似乎都作了彩排;如果说他一生最终的不幸和悲哀如一部小说的结局,那么伏笔也似乎在这一年里已经打下。这样说初听起来有点玄,因为人一生的命运如同一条在大地上自由流动的河,看起来是那样的散漫而毫无规则可寻。然而尽管如此,只要我们稍加考察,会发现事实上总有一些关键的瞬间和特殊的部位不但决定着其现实状态,也决定着其未来的流向甚至结局。佛家相信因果报应,即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然而我们许多时候并不相信所谓“命中注定”,那是因为“因”与“果”之间常常不但隔着时间的千山万水,更大小不成比例。谁能相信北美大陆上的一场飓风,最初仅仅是因为亚马逊雨林里一只蝴蝶翅膀的轻轻扇动呢?的确,我们很难从眼前那些转瞬即逝的细枝末节上发现它们与未来的联系。然而,再小的一块石子坠入水中,也会在水面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我们可以不相信石子,但怎能对波纹视而不见呢?
众所周知,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但24岁的他在异国他乡第一次遇到林徽因时,还只是一个普普通通一事无成的“海漂”青年而已——甚至连普通的“海漂”青年还不如,因为那时他虽已在海外漂泊三年,但对于自己将来究竟要干什么,究竟能干什么等问题,似乎还昏头昏脑:他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经济,但似乎对此并无多少兴趣,最后虽然获得了个硕士学位,但毕业论文的题目则是《论中国妇女之地位》;此时他空前高涨的是对政治的热情,主要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上;正当他被一些中国同学称为“鲍雪微克”,即布尔什么维克时,他又突然要做哲学家,突发奇想要跟“二十世纪的伏尔泰”——罗素学哲学,并且真的为追随罗素放弃了哥伦比亚大学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从美国来到英国;来到英国后,他交往最密切的人物却是作家狄更生;在狄更生的推荐下他可以随便选修科目,这让他“有机会接近真正的康桥生活……慢慢地‘发现’康桥,和不曾知道过的更大的愉快”,而这“更大的愉快”则又不是政治或哲学了,而是文学。但此时作为一个文学青年的他,已“创作”出的最成功“作品”便是一个3岁的儿子,离写出成名诗作的那一天还早着哩——谁知道他能不能写得出来呵?因此他平时生活中那些有些异常的举止,在许多人的眼里并非是一种诗情的冲动,而实在只是一种疯疯癫癫,他的同学温源宁就曾将一件与他有关的事情当作笑话说给自己的妻妹听:
有一天,正下着大雨,浑身湿淋淋的徐志摩突然从雨中冲进宿舍,拉着正在看书的同学温源宁就要往外跑,说:“我们快到桥上去等着!”温源宁一时没头没脑,问:“这么大的雨,等什么呵?”徐志摩眼睛瞪得大大地说:“等雨后彩虹呵!”温源宁表示,这么大的雨他不愿去,并劝他将湿衣裳换下,穿上雨衣再去。可没等他将话说完,徐志摩已一溜烟地又冲进了雨帘中。(丁昭言《在现代与传统中挣扎的女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8月版)
温源宁的妻妹听过后果然笑得很开心,并且还追问道:“那下文呢?他真的等到了彩虹了吗?”
“我哪能知道呵?这要问他哩!”
“是的,有机会一定要问问他!还要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
温源宁的妻妹不是别人,正是林徽因。不要以为林徽因在见到徐志摩前对他就有这样的好奇便以为她就是徐志摩的同类或知己,其实那时他们的情趣恰恰相反,我们不妨看看林徽因给朋友信中的一段话:
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是英国的不断的雨。我爸爸到瑞士国联开会去,我能在楼下厨房里炸牛腰子同洋咸肉,到晚上又是在顶大的饭厅里(点着一盏顶暗的灯)独自坐着(垂着两条不着地的腿同刚刚垂肩的发辫),一个人吃饭一面咬着手指头哭——闷到实在不能哭!理想的我老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的发生,或是有人叩下门走进来坐在我的对面同我谈话,或是同我坐在楼上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的还是有个人要来爱我。我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而实际上却是天天落雨又落雨,我从不认识一个男朋友,从没有一个浪漫而聪明的人走来同我玩——实际生活上所认识的人从来没有一个像我想象的浪漫人物,欲还加上一大堆人事上的纷纠。(张洁宇《你是人间四月天——林徽因爱与被爱的故事》,见2000年4月《历史》)
明明是一样的雨,在徐志摩那儿是点燃激情的催化剂,而在她那里是只会带来孤独与寂寞的无尽愁绪。
林徽因出生在杭州,在江南长大,骨子里透出的不但是让人无法忽略的才情,还有一种让人无法抵抗的美丽,而且这种美丽又带着一种让人心碎的忧伤。此时,她漂泊异乡,青春的生命正经受着一场孤独的洗礼。如果说此时的徐志摩是一团火,那么此时的林徽因似乎是一块冰,冰火本是很难相融的。但是同时我们又不难看出,林徽因冰冷的外表下其实掩藏着一颗火热的心,这颗心充满着对爱的渴望——这一点与徐志摩是相同的——有了这一点相同,便注定了火有一天将会把冰融化,而由冰融成的水,也注定将会把火浇灭。
二
林徽因渴望爱情,徐志摩也渴望爱情!
但问题是,你徐志摩不是早已是一个有妇之夫了吗?你不是正写信要妻子不远万里地从国内来英国吗?你还有渴望爱情的资格吗?
是的,自从四年前徐志摩接受了父亲为他安排的婚姻后,他便失去了爱的资格,对此他比谁都明白。他初到林家,“一见钟情”的并不是林徽因,而是林长民,且他们的“一见钟情”只是一场游戏。1925年12月24日,林长民在郭松龄军中为流弹所击而阵亡,为了纪念他,徐志摩在自己编辑的1926年2月6日的《晨报》副刊上刊出了林长民的《一封情书》,并加编者按说:
分明是写给情人的,怎么会给我呢?我的答话是我就是他的情人。听我说这段逸话。四年前我在康桥时,宗孟在伦敦,有一次我们说着玩,商量我们彼此装假通情书,我们设想一个情节,我算是女的,一个有夫之妇,他装男的,也是有妇之夫,在这双方不自由的境遇下彼此虚设的通信讲恋爱。
此时的徐志摩只能在一种虚拟的游戏中享受着爱与被爱。
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两个大男人实在有点无聊甚至变态。然而细想一想,徐志摩既然将它作为对亡友的纪念而公诸报端,在他看来一定是能感动许许多多的读者的吧,因为那时在“不自由的境遇下”挣扎的人何止他们二人呵?因此,与其说他们的这种行为是一种“无聊”和“变态”,还不如说是一种挣扎和自慰,一种因渴望而做出的无奈挣扎和绝望自慰。
那位与徐志摩互写“情书”的林长民不是别人,正是林徽因的父亲。正因为林徽因有着这样一位父亲,所以徐志摩后来出入林家时才敢于越来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而林长民呢,也似乎一直能容忍,甚至有时还推波助澜。渐渐的,林徽因也从最初时的“差一点把志摩叫了叔叔”,到后来把他当作了那个“浪漫聪明”、肯同她谈话并愿意爱她的人,而最终二人终于携手走进了康河美丽的夜色中:他们踩着美丽的月色,听着远处教堂里传来的悠长钟声,默默地走着。忽然林徽因扑哧一声笑出了声,因为她想起了姐夫说过的那个有关徐志摩的笑话。
徐志摩问她笑什么,林徽因没有回答,而是反问道:“你看到彩虹了吗?”
徐志摩说:“当然看到了呵!”
如此没头没脑的答问,一切全凭心有灵犀。
“那么你等了多久才看到呵?”
“记不清了,反正是等了好久,不过很值!那真是太美了……”
林徽因打断他对彩虹美丽的描述,更加好奇地问:“你凭什么就知道准会有彩虹呢?”
徐志摩得意地笑着说:“全凭诗意的信仰呵!”
……
也正是凭着这种“诗意的信仰”,徐志摩与林徽因越走越近,他们相依着出入舞厅、剧场,相偎着谈论艺术、人生……而这一切被林长民看在眼里,他不仅对徐志摩没有丝毫的责备,反而还在林徽因表现得有些犹豫和不安时主动写信给志摩加以解释:“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嘲笑,足下误解了。”信末附言:“徽徽问候”。
一段时间里,徐林之恋似乎天时、地利、人和全得了,但实际上其中正酝酿着一种危机,因为无论是徐志摩还是林徽因,他们事实上是互相做了“第三者”:徐志摩自不必说,就说林徽因,她在来英国之前,父亲林长民已口头上与梁启超有过婚姻之约,将她许配给了梁家大公子梁思成,实际上林徽因此时也早已是“罗敷自有夫”了。因此,康河上的那一个个夜晚虽然美丽,但注定了脱不掉忧伤的底子,这从十年后林徽因那首题为《那一夜》的追忆性诗作中不难读出:
那一晚我的船推进了河心,
澄蓝的天上托着密密的星。
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
迷惘的星夜封锁起重愁。
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
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
到如今我的船仍然在海面飘,
细弱的桅杆常在风涛里摇。
到如今太阳只在我背后徘徊,
层层阴影留守在我周围。
到如今我还记着那一晚的天,
星光、眼泪、白茫茫的江边!
到如今我还想念你岸上的耕种:
红花儿黄花儿朵朵的生动。
那天我希望要走到了顶层,
蜜一般酿出那记忆的滋润。
那一天我要跨上带羽翼的箭,
望着你花园里射一个满弦。
那一天你要听到鸟般的歌唱,
那便是我静候着你的赞赏。
那一天你要看到零乱的花影,
那便是我私闯入当年的边境!
而对于徐志摩来说,康河边只有美丽没有忧伤,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觉察这份美丽忧伤的时间与心力,此时他心头越来越急切的痛苦是,从国内载着妻子张幼仪的船正越来越近地驶来,他不能脚踩两只船!
三
张幼仪的船终于在法国的马赛靠岸了,徐志摩急匆匆地从英国伦敦乘飞机赶过去接她——他不去接谁去接呵?这既是他的义务也是他的责任!总不能让一个第一次出远门又不懂法语的女人在异国他乡自己折腾买票、转机等事情吧?
马赛港的码头上挤满了来接亲朋好友的人,一个个脸上挂着期待和兴奋。徐志摩也挤在人群中,只是与众不同的是,徐志摩的脸上可没有一点期待与兴奋的表情,他身穿一件黑色的长大衣,脖子上搭了条白色的围巾,这将他本来就不白的脸衬得几乎与他的大衣一般的黑。
终于看到四年没见的妻子走上岸来,徐志摩不紧不慢地迎了过去,四眼相对时,他嘴里只吐出冷冷的两个字:“来啦!”见此情景,本是满脸欢喜的张幼仪突然间也似乎更加冷淡,只从鼻子里“嗯”了一声。就这样,他们的见面仪式便算结束了。
张幼仪乘坐的船在海上航行了近一个月,在这近一个月无所事事的日子里,她曾设想过无数种与丈夫见面时的情景,但就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从法国去英国要乘飞机,张幼仪是第一次坐飞机,心里本来就有点害怕,再加上那种飞机又很小,飞行中只要一遇到一点点气流就会颠簸得厉害,这让她在途中出了洋相:起飞不久,飞机便剧烈的颠簸起来,张幼仪不禁朝窗外看了一眼,没想到不看还好,这一看,可把她给吓坏了!她看到舷窗外朵朵白云,再从云缝间向下看,只见一片茫茫大海,此时她心里真怕飞机会颠散了从天上掉下去——也许是过于紧张吧,此时她的胃里一阵痉挛,随即便哇的一声吐了起来。
看到张幼仪呕吐,徐志摩非但既不帮她处理秽物,也没有半句安慰的言词,反而将头扭向一边,还轻轻说了一句:“你真是个乡下土包子!”
其实这话徐志摩已不是第一次说了。早在结婚之前,当徐志摩第一次看见张幼仪的照片时,他就曾把嘴往下一撇,用一种充满鄙夷的口吻说道:“乡下土包子!”婚后一起生活的那段日子里,他更是动不动就将这句话甩给张幼仪。
其实徐志摩说这样的话实在没有道理:张家在上海松江县城,你徐家在浙江海宁硖石镇,如果说县城是“乡下”,那你徐志摩不也是“乡下人”吗?再说两家门第,张幼仪的爷爷做过多年县令,父亲是一方名医,尤其是两位兄长可都是人物,二哥张君劢是民国政坛的风云人物,大哥张嘉敖曾留学日本,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担任过《国民公报》的编辑、《交通官报》的总编辑、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等,同时还是“国民协进会”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他为妹妹选夫婿时身份是浙江都督府秘书,他之所以选中徐志摩,是因为徐志摩的才学——他那次去杭州府中视察,徐志摩的作文本上的文章和书法深深打动了他,他便决定将这个名叫徐志摩的学生选作自己的妹夫,至于他的出身、家境等根本就没作考虑;而相比之下,徐家充其量只是个土财主,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只是当地商会的会长,他之所以看中张家这门亲事,是因为他更看中张家的官场背景可以为自己在生意场上赢得更大的成功。因此,要说张幼仪是一个“土包子”,那你徐志摩不更是“土包子”一个吗?聪明的张幼仪一定在心里这样比较过。因此,当徐志摩在法国飞往英国的飞机上又这样无礼而又无理地说她时,她终于反击了——老天似乎也有意要帮她的忙——徐志摩说张幼仪“乡下土包子”的话音刚落,自己竟也突然间呕吐了起来,见此,张幼仪回敬道:“我看你也是个乡下土包子!”
或许是贤妻良母式的张幼仪很少这样“出言不逊”,也或许是徐志摩压根儿就没想到张幼仪会这样回敬自己,这让他感到十分狼狈。许多年后,他还与自己的学生一再说起这一次飞行中的狼狈。而对于张幼仪来说,许多年后我们再来品味她的这句话,分明能从中品味出她自尊、自爱和自强的个性,而对于后来她与徐志摩离婚时表现出的那份坦然,以及离婚后独自一人在事业上创造的一个又一个辉煌,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张幼仪来英国只半年多,徐志摩便与她一起登报宣布正式离婚了——此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宗西式离婚案——这让人很是怀疑徐志摩当初写信要家里将她送来英国的全部目的似乎就是为了要与她离婚。
而就在徐志摩与张幼仪的离婚办得紧锣密鼓时,林徽因、林长民却与徐志摩不辞而别,于1921年8月突然从伦敦回国了。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