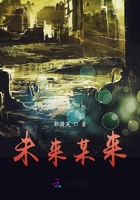北北从林中拣来树枝。安迪点燃了篝火,又从背包里拿出真空包装的宫保牛肉拌白米饭,倒进锅里煮了。香味立即散开,给小岛增添了人间气息。陆滨还烧了一锅水,给每人冲了一杯中国绿茶。三人坐在篝火旁吃晚饭。安迪说,在加拿大的野外吃中国餐别有风味,比三维治好吃多了。
日落时,湖上波涛慢慢涌动。晚霞的橙红渐渐淡成乳黄,随后转为黑蓝,湖面就完全平静了下来。北北钻进帐篷,很快发出了鼾声。陆滨叹口气,说:“北北要是总能像今天这么开心,就好了。”安迪沉吟片刻,缓慢地说:“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我儿子,唯一的儿子,华德·欧文,二十几年前因为忧郁症自杀了……那年他刚满18岁……”
陆滨分明看到安迪眼中的泪光。
“他自杀后,我才知道他得了忧郁症。”安迪哽咽起来。
安迪曾像一个旅人,在高速公路上悠然开车,突然从路旁的悬崖上跌落下一块巨石,砸毁了他的汽车,挡住了他的去路。他攒聚起全身的力气,从汽车中爬出,艰难地在巨石和悬崖之间寻找出路。
那块巨石,是华德的自杀。
那天他正在安大略湖边长跑,接到警察的电话。警察说他发现一具年轻人的尸体,从年轻人的钱夹里找到了驾照,还有一张安迪的名片。年轻人名叫华德·欧文。安迪因奔跑而激烈跳动的心停顿了一刻。那一刻有多长?五秒,十秒,还是一分钟?他无法计算,那一刻改变了他的后半生,他的心再无法恢复原来的频率……
在安葬了华德之后,安迪又开始了长跑,风雨不误。长跑对于他,是一种治疗。在激烈的运动中,他能获得些许平静;而在静止时,他无法控制内心的风暴!他用同一个问题折磨过自己成百上千次:“华德为什么自杀?”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他就像一个敏感多疑的侦探,力图从儿子的遗物中,从儿子朋友的介绍中,多方搜寻蛛丝马迹,从具体中寻找抽象,又从虚无中寻找实在,来回答这个沉重无比的为什么。答案一天比一天明朗:忧郁症。可惜太迟了,他宣告自己是一个失败的父亲……再没有机会挽救……
他无法继续待在家里。每一件物品都令他想起儿子。伤心事,像插在心头的玻璃碎块,每时每刻都尖锐地立着……他加入了一个支援非洲的社会组织,到埃塞俄比亚工作了一年。他以为远离,能让他忘记失去儿子的悲伤,但等他回到多伦多时,他陷入更深的悲伤:他的妻子莉塔成了陌路人,他的养子保罗离家出走。在他和妻子离婚之后,他的生活变得愈发简单。他开始有意识地搜寻有关精神健康的资料。世界上的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可能在其一生中承受精神病的煎熬。这个数据让他震惊。精神病是导致自杀的主要原因,而在三十五岁以下离世的人中,第二大致命原因是自杀。加拿大人每年住院治疗,其中有四分之一是因为精神疾病。
他决定投身精神健康领域。人到中年,进入一个新的领域,自然是挑战。他在接受了一年的培训后,进入安河精神健康中心工作,成了一名社会工作者,同时晚间在多伦多大学修心理学课。两年后,他获得硕士学位,又开始在一家心理诊所兼任心理治疗师。当他第一次见到北北时,就联想到了儿子华德。尽管北北和华德的眼睛的颜色不同,但眼神竟惊人地相似:一样的模糊、忧郁,还有一样的困惑。他这些年一直关注北北,不希望儿子的悲剧发生在他的身上。
陆滨说:“我觉得自己在打一场持久战,永远和儿子的高扬和低落搏斗……这种搏斗这么复杂,经常要变换方式,很多时候我想放弃……”
安迪开导:“别把它看成是一场战役,把它看成是生活的一部分。”
陆滨和安迪谈到了夜深。陆滨的英语突然超乎寻常地流利起来,他竟体验到了畅谈的快乐。直到篝火熄灭,两人才走进各自的帐篷。陆滨躺在帐篷里,品味着安迪说过的话。他人的经历永远都是一面镜子,他终于学会了从这面镜子观察自己。他想起了美国女歌手CharleneDuncan创作演唱的一首歌,“I’vebeentoparadise,butI’veneverbeentome”(我到过伊甸园,但从未到过自己的内心)。抵达内心,是人生中最曲折最漫长的旅途。周围安静极了。偶尔有一只潜鸟哀叫着飞过。因为白日消耗了许多体力,身边的北北发出均匀的呼吸声,他也陷入了沉沉的睡眠。
不知过了多久,他醒过来,起身,走出了帐篷。四周的树枝纹丝不动,鸟儿都歇息了,湖水静如甜睡的少女。城市里霓虹耀眼,天空却是灰色的,而在这里天空漆黑如墨,星星便格外地明亮。夜这么厚重,这么纯粹。在大自然中万物在夜里休憩,期待白日的清明,而在城市中人们在夜里辗转反侧,在白日里浮躁混沌。
他回到帐篷,很快又入睡了,睡得像个婴儿。早晨醒来,他的每个毛孔都被灌满清新的空气。他看了看身边,惊讶地发现北北不见了,他立即套上短裤,跑出了帐篷,叫着北北的名字,心被恐惧的纤绳吊在了半空。他在小岛上一边喊,一边跑,终于在岛的另一边看到了北北纤瘦的身影。他气喘吁吁地跑过去,跌坐到北北身边,说:“我以为你被熊吃了。”北北微微一笑:“你想甩掉我,哪儿那么容易?”他正在写生。陆滨探过头细看,他画的是莲花湖。
三人启程,当天抵达了独木舟湖。他们登陆湖心小岛,拜谒了加拿大画家汤姆·唐穆森的圆锥形石冢,据说他生前最喜欢在这里宿营。北北说,大约一百年前,汤姆·唐穆森辞去了在多伦多一家商业美术设计公司的职务,来到阿岗昆公园,当兼职钓鱼导游和森林防火员,就是为了作画。是否为艺术放弃舒适的生活,大概是艺术家和俗人的最大区别。如果他没有在三年中每年在这里生活八个月,他也许不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画家。他的足迹遍布阿岗昆公园,被青山秀水养育。他热爱每一棵树,画过落叶松、白桦、短叶松,还有松树……可惜他不到40岁就突然离开人世,他的尸体是在独木舟湖的中心被找到的,死因至今还是个谜。他的朋友们掩埋了他,并堆了朴拙的石冢,让他能日夜眺望迷人的湖光山色。
陆滨听说过汤姆·唐穆森这个人,但并不知道他的生平细节,更不知道他竟然是北北的偶像。他人,陆滨突然想到这个词,他人是多么神秘、多么陌生,连他的亲生骨肉,都时时让他吃惊。
陆滨在旅行结束时,突然有些不舍,意识到他和北北在走出阿岗昆公园时,已经不再是走进公园时的那两个人了。
北北进入了一家农场工作,做些简单的农活,比如摘樱桃和苹果之类。农场是由一个不营利的组织办的,主要宗旨是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一个相对轻松、健康的环境。邱霜在电话里一再阻拦,但陆滨说服了她:“让孩子去寻找他自己的路吧。”
邱霜自从到西部教中文起,感觉生活中缺少了点什么。平日忙忙碌碌,日子还过得去,但到了周末,心里就出现一个莫名其妙的黑洞。有一次同事办生日派对,把地点定在唐斯赛马场的酒吧,邀请她参加。一群同事凑10元钱的份子赌马,结果每人赢了300元。从此邱霜迷上了赌马。痴迷总是从兴趣开始的。当兴趣被发展为痴迷,仿佛从玩枪到走火。她频繁到赛马场下赌,输多赢少,消磨了许多时光。赌马成了她的隐私。她对陆滨只字未提。陆滨对赛马一向不感兴趣,短短几分钟的比赛,用半天时间来酝酿情绪,还要忍受播音员没完没了的聒噪。当比赛开始,马匹迅速冲线,所有的激动又戛然而止……但北美人对赛马着迷。北美每年各地十几万场的赛马,吸引几千万人观看,创造巨额门票收入。赛马被视为牛仔文化的集中体现,一种骨子里的乡愁,一种古典主义的纯粹与美,一种原始的力量与危险。这一切似乎与商业无缘,但商业无孔不入,岂能放过从赛马中赢利的机会?
加拿大一年一度的唐斯赛马会即将开幕。那天邱霜早早地开车上路。离唐斯赛马场还有20英里,高速公路上的指示牌这样说。指示牌是绿色的,青葱得令她联想起赛马场的草地。对于她,想象,永远都是一支不衰的神笔,能随时点铁成金。一丝微笑从她的唇边浮起,牵动起眼角的皱纹,立即被她从后视镜中捕捉到了。她旋即有些无奈地收起了微笑。四十几岁的人了,连微笑都不得不战战兢兢。她早上虔诚地扎上红腰带以求好运,今天,该是她时来运转的日子。她等这一天等得殷切,即使在当年待嫁时,也没这么殷切过。
唐斯赛马场热烈的节日般的气氛,让她立即雀跃了起来。空气中散发出马粪的味道,但这丝毫不影响她的好心情。许多女人戴着插满鲜花的帽子,穿着袒胸露背的裙装。这样的打扮她是不敢尝试的,担心被人看作老妖精。她甚至看到了好莱坞一个专演警察的硬汉,虽然记不清他的名字,但他的出现让她兴奋。人群中的亚裔面孔不多,她的出现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她尽力把腰板挺得直些。被人瞩目永远都不是一件坏事。
几天前,她就已经开了一个叫e-Wallets(电子钱夹)银行账号,把整整两万加元,都押到“草原美人”上!如果她母亲知道她此刻下的赌注是她一年的全部血汗钱,她会在棺材里腾的坐起身来。这一次邱霜单押“草原美人”,而不是押前两名和前三名。如果“草原美人”得了冠军,她就会大赢特赢,最高可能赢到15万加元。有了15万加元,她就可以立即当上老板!就可以在卓悦面前再次骄傲地挺直腰板。也许驱动她的仅是一根虚荣的神经。这一次如果她赢了,所有的人都必须对她刮目相看。她渴望出人头地。她甚至怀疑自己想卓悦这个名字用掉的时间比想陆滨要多。敌人自有敌人的魅力。人在许多时候与其说是被爱人,不如说是被敌人塑造的。卓悦不但塑造了她,简直就是她的人生动力。
她来到观众席,找到一个前排的座位坐下来。邻座是一位蓝眼睛的男人。他年纪不轻了,头发已灰白,但依然颇有魅力,像老年版的克拉克·盖博。她在心里暗自叫他“克拉克·盖博”。克拉克·盖博曾在电影《飘》里扮演男主角,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迷倒了中国一代女观众,包括邱霜自己。她如坠梦中,身心漂浮。
“你押的是谁?”“克拉克·盖博”问。
“草原美人!”邱霜的口气充满骄傲。
“我也押‘草原美人’!”男人兴奋起来,“你很有眼光!”
“草原美人”是所有赛马中的唯一母马,仿佛中国古代军中的花木兰。邱霜的目光追逐“草原美人”,像母亲追逐自己为之无比骄傲的女儿。在唐斯赛马会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正式参赛的母马不过几十匹,而“草原美人”是其中之一。她具备纯种马名贵的睥睨天下的气质,精壮灵活、体态完美,拥有一身乌黑的毛发。邱霜的眼神和“草原美人”对视了,她几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耐力十足、好胜,永远俯视众生,渴望在苍茫天地间奔驰。
离比赛时间越近,邱霜的心跳得越急。命运即将被改变。裁判吹响了哨子,比赛开始了!“草原美人”迅速超过一众公马,开始领先!生命的脆弱与强悍,恰在奔驰的危险与快意之间。邱霜的心,仿佛突然被一只无形的手提到喉咙里,她紧咬双唇,担心稍一放松,就会把心呕出来。公马“雄狮”后发制人,骤然冲刺,超过了“草原美人”。“草原美人”越过了终点,以仅仅3/4个马身的距离落后“雄狮”,屈得亚军,酿成终生遗憾。她没有轰然倒下,没有骤然尖叫,似乎很平淡地跪倒下来,低着头,鼻息变得微弱。训练师立即上前检查,发现她的两条前腿踝关节骨折了,断定她已是一匹残废的马,不可能再参加任何比赛。播音员宣布了这悲哀无比的消息,全场一片欷歔。邱霜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让眼泪肆意横流。“克拉克·盖博”搂住邱霜的肩膀,轻言安慰,但她却毫无回应。
“草原美人”的主人决定给她安乐死。达尔文的冷血理论在这里又一次得到证实:适者生存。如果不在奔驰中赢得生命的璀璨,便在死亡中获得灵魂的安息。当医生开始给“草原美人”注射吗啡,全场上万观众都屏住了呼吸,邱霜不由得闭上了眼睛……针头似乎扎进了她的手臂,痛是些微的,却是致命的……
与此同时,在布鲁斯半岛的狮首镇,陆滨找到了道格拉斯一家的度假屋。苏菲接到邻居的电话,说是度假屋的水管漏水,让她派人修理,免得毁了房屋。不巧琼得了感冒,她不能离开,就求陆滨帮忙。度假屋的房主其实是道格拉斯的父母,但他父母常年在佛罗里达生活,房屋维护的任务就落到了道格拉斯一家的身上。
度假屋是全木结构,建在一座山坡上,因很久无人打理,门前庭院里的花草露出失宠后的憔悴。他用苏菲给他的钥匙,打开了门锁。起居室里有一股霉味儿。推开窗,清新的空气便急切地扑进来,休伦湖的乔治湾映入眼帘。天碧蓝如洗,仅几片白云,像被画家涂上去的,恬淡,安静。度假屋分上下两层,楼下是起居室、厨房,楼上有连着浴室的主卧室,还有两间卧室,外加一个浴室。
他没费多少周折就修好了厨房的水龙头。他有些累了,准备消消汗,休息一下再返回多伦多。他在度假屋里转来转去。道格拉斯的父母和儿女一年能在这幢度假屋里住几天?加拿大冬长夏短,真正需避暑的日子不会超过三个月。这世上总有人面临“拥有太多”的问题,而他面临的是“拥有太少”的挑战。命运就这么不公平,但不管他愿不愿意,他必须接受现实。
他好奇地打量墙上挂的画,和书架上各种艺术品。这里的装饰不像道格拉斯家里的那么讲究,有点拼凑之感。他突然转念想,也许道格拉斯会把安迪家里不用的东西拿到这里来。这个念头使他完全兴奋起来。他走进主卧室,在房间的每一个橱柜、抽屉里寻找,甚至趴到地板上查看床下……似乎无缘由的,他的心跳开始加速,额头上刚消退的汗又冒了出来……终于他在客房的壁橱里,找到了一幅镶在廉价木框里的水墨画。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拿出来,那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桃花潭水》!他的血都涌到了头上,两腿一软,跌坐在床前的地毯上。他用衣袖擦去画上的灰尘,像护士清洗刚出生的婴儿般。他仍不放心,从钱夹里找出罗杰和祖母的合影,对照那幅挂在他们背后的画反复对比,终于确认了。他的心被狂喜填得满满的。周围一片寂静。异国、异乡、陌生人的房屋、价值非凡的名画……所有这一切几乎令他恐惧……他穿过了时间、空间的黑暗隧道,和这幅画相会。
陆滨拿出手机,拨通了邱霜的手机号码。她是他儿子的妈妈,他想在第一时间与她分享喜讯:“你猜我找到了什么?!”他竭力压抑语气中的兴奋。
“总不会是金砖吧?”邱霜一边开车,一边没好气地说。
“比金砖还值钱呢!我找到了《桃花潭水》!”他急促地讲了这幅画的来龙去脉。
“真的吗??”她在电话中兴奋地喊起来,并没有责怪他以前对她的隐瞒,“你在哪儿找到的?”
“在道格拉斯的度假屋里。苏菲求我到这儿来修水管。”
“他家有人吗?”
“没有,好像左邻右舍也没有人。”
“那你还等什么?把《桃花潭水》拿回家吧。”
“那不就是偷吗?我干不出这样的事儿。”
“《桃花潭水》本来就是你家的,现在物归原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