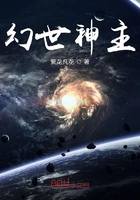浅浅的一道海峡,隔开了大陆和台湾,隔断了乡愁和归路,隔绝了四十年的天涯。
一九八七年,台湾政府开放了“荣军民众”返乡探亲的限制,得到消息的异乡人,顿时把申办证件的公务处围得水泄不通,引发新闻界报导的热潮。
楚尧是最早提出申请的人之一,可获得批准的只有泊菡一人,因为开放的条件之一,必须是三代直系血亲健存大陆,泊菡的父亲章燿健在,符合条件,而楚尧的父母早已离世,不能申请到探亲签证。
楚尧照顾了多年泊菡,不放心她一个人远赴大陆,要求已在美国的楚忆和在台湾无所事事的楚念念兄妹两人陪着母亲返乡探亲。
六十年代中期,泊菡随楚尧调至美国日本东南亚的各基地,写过几本出名的游记。八十年代,台湾电视业发展,泊菡人缘好,外貌佳,电视台请她主持旅游节目,手头的工作不断。楚尧退休后办了间山庄农场,除了照顾泊菡,就是领着张帆、沈崇海、小冉一帮老兄弟,还有出狱的陈醒州和吴茱萸夫妇,在里面自娱自乐,自给自足。
泊菡留好三个月的空档,与念念在香港汇合了从纽约赶到的楚忆,母子三人转机上海,回到暌违近四十年的故乡。几大包回乡的礼物,都是楚尧亲手打理的,一样样贴好姓名标签,交到念念手里。
事先发了电报不让家里来人接机,可走到上海虹桥机场的国际及港澳同胞到达大厅时,念念眼尖,一眼看到有两个头发花白,望眼欲穿的老人,手里拿着大大的一张白纸,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章泊菡”三个字。
泊菡扶了扶金丝眼镜,把这两位清瘦的老人仔细打量,尘封的记忆被一阵风吹过,顿时有了鲜活的生命,她冲到两个老人面前,抱住了其中一个:“二哥!我是小妹呀!”她拿了久违的上海话唤着毓信。
“小妹!”毓信连忙握紧了泊菡的双手,民风的差异,这边更习惯用握手代替拥抱,“刚刚我还和盈秋说,这个美人就是小妹,可盈秋不信你会这样年轻!”他笑着嗔怪一旁的妻子,脸上露出小小的得意,还像当年那样阳光纯真。
盈秋稳健地和泊菡握手,又注意招呼泊菡身后的两个孩子。她刚刚从上海市政府对外办公室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休,看得出她的待人接物要全面周到得多。
“欢迎回到祖国的怀抱!我们安排了轿车,欢迎你们这些远方的游子。不会再让你们像当年离开那样凄凄惨惨,今天,我们要高高兴兴!”盈秋为今日的重逢定下了调子。
坐在轿车里,盈秋和毓信一路为泊菡和孩子们介绍着上海的变化,两个孩子第一次到大陆,第一次见到亲人,听到祖国这样的字眼,血液里的中国情缘澎湃而生。
盈秋安排的路径穿过热闹的静安区,经过繁华的外滩,泊菡看着又熟悉又陌生的街景,感到脑海中那些记忆的碎片在不停地闪光,慢慢地亮成一片,她忍着眼泪,努力不要伤感,努力只让喜悦的心情充盈心胸。
突然,毓信指着一处江堤,转头问泊菡:“小妹,你还记得吗?抗战胜利的那年,你我、二妹和楚尧、家祺伯英,就是在这里看黄浦江夜景的。”
泊菡茫然地摇摇头,又伤感地点点头。现在的黄浦江,里面停驻的都是大型的钢铁船只,有了完整的水泥堤坝,她根本认不出哪里是当年驻足的地方。可她又记得分明所有的细节,她就是在那一天,对年轻冷俊的军官一见钟情,那晚的月色,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
车子穿大街入小巷,停在一片小楼丛林前,毓信下了车,告诉泊菡:“我们家的院子已经被盖成单位宿舍,不过,你从前住的小楼仍在,没有变化。”
楚忆和念念自幼就听到妈妈说起家里的大院子,紫藤长廊,大草坪,外婆种的八仙花,美人蕉……可现在,这里是密密的砖房,热闹的里弄,各种说话和炒菜的声音,看到他们打扮气质不同,每家都有人探出身子,怀着好奇招呼,打探。
毓信笑着与邻居们打招呼,介绍泊菡,左停右停,蓦然一下,久别的小楼竟突兀在眼前,一株苍劲的紫藤遮蔽了半个小楼,正值暮春四月,万花盛开,香气扑鼻,小楼倾泻下淡紫色的藤萝瀑布,好像是为迎接远方游子洒下的欢乐。
“小妹,这棵紫藤,就是拆除长廊时,姆妈移过来的。她说,你从前最喜欢那里,长廊没有了,紫藤树一定要在。”
“忆儿,你快点帮妈妈和紫藤树拍张照片,那是姆妈留给我的思念。”泊菡抹去镜片后的泪水,这么多年,她还会想念姆妈温暖慈爱的怀抱,可惜绣银已经去世十七年了。
楚忆立刻从背囊里拿出一架宝丽莱相机,拍下了妈妈在紫藤花下轻拭泪痕的身影。
小楼的门口出现了一群人,其中手持拐杖,精神矍铄的老者,正是九十高龄的章燿。
“爸爸!”泊菡在门前双膝下跪,流泪唤了一声,楚忆和念念跟着跪下,按照楚尧的交待,给外公叩了三个头。
“起来,小妹!我们新中国,不兴这个啦!”章燿绷着悲喜难辨的皱纹脸,示意身边的儿女快快扶起小女儿一行。
一个套着护袖,身穿布衫的微胖妇人上前挽起泊菡:“小妹,你还认得我吗?”
她满脸风霜,头发花白,泊菡叫了声:“二姐!你是我的二姐!”她再也想不到,从前美丽得不可方物的二姐,现在会老成这样,要不是声音依稀还在,她已认不出泊芙。
毓诚夫妇也来相认,他们和王家祺一起,六十年代初支援大西北建设,在西北高原落地生根,这次听说小妹回来探亲,特地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赶来。
大家坐到客厅里,前两年大姐泊莲回国探亲,带来了当年绣银安排的一笔巨款,章燿重新翻修了破旧的小楼,添置了新家俱。
亲人相见分外高兴,七嘴八舌地问着泊菡别后的情况。
“忆儿在他爸爸手下吃了不少苦,他和我一样,读书凭兴趣。却被他爸逼得考上工程系,他又不喜欢,后来,去美国念硕士,被电视台相中,当了新闻主播,娶了美国太太,如今自己办公司,算是小有成绩。”楚忆是电子公司老板,名成利就,生了三个高大英俊的混血儿子,泊菡夸起他来,总是喜滋滋的。
楚忆就像翻版的楚尧,风度翩翩,不过远比他温和,善解人意。他笑着向身边的外公亲热道:“外公,我听说您耳朵不好,特地从美国给你带了最新款的助听器。”
他替章燿安好助听器,把一个胶片样的东西贴在耳边,顿时恢复了章燿失听多年的世界,章燿满脸慈祥,笑呵呵地拍着他:“这个孙子好,这个孙子懂我的心意!”
大家都哄笑起来,有的叫爸爸,有的叫爷爷,外公,都抢着说:“难道我们不好吗?不懂你的心意?”
章燿却像个老小孩:“他也有不好的,就是长得太像那个坏蛋!”泊菡母子三人听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原来章燿一直把楚尧叫做坏蛋。
盈秋微笑着劝公公:“爸爸,楚尧再有错,也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共|产|党都不翻旧账,不扣帽子好多年,爸爸也要促进两岸统一才对!”
五十年代末期,毓信因为言行激进,被单位打成“右|派”,下放到西南边陲,当时盈秋还在海外工作,听闻后不顾大好前程,主动承揽了责任,也和毓信一起下放,就冲这有情有义的情份,她在章家人心目中地位超然。
章燿听话地:“好,我错了,要向前看。”
毓信关心地问:“小妹,楚尧对你好吧?”当年的事他也是主谋之一,因此比旁人更关心泊菡的幸福。
泊菡尚未开口,就被活泼伶俐的女儿抢去了发言权:“小舅舅,我爸对我妈,好不好搞不清,但不放心才是真的!怕她忘这个忘那个,怕她吃不好睡不香,怕出版社、电视台的才子帅哥太多,我妈会移情别恋……反正我们从小到大,只知道我妈一直被我爸捧在手心里,生怕丢掉了!”
念念这样生动的描述让众人相视而笑,泊菡的幸福化解了当年的怨恨,在这里变成祝福的微笑。
章燿慈爱地望着已经二十九岁的念念,楚念长得一如泊菡当年,他亲热地摸着外孙女的脸,胳膊,手,万分垂怜:“念念啊,你生得好,生得好!是我们章家人的长相,走到哪里,别人一看,就知道是我们静安章家出来的!”
大家又哄笑起来,一个个叫着:“难道我们都不像章家人,出去给爷爷(爸爸)丢脸了?”
重逢、团圆的气氛很快乐,章燿脑筋清楚,突然想起来,又生气地:“我记得应该还有一个孙子,怎么不来看我?”
念念机灵,撒娇地抱着外公:“外公说的是二哥吧?他身份特殊,是现役的民国空军大队长,楚憾楚上校,能来吗?你们欢迎吗?”
盈秋笑道:“我们欢迎一切有利于祖国统一的台湾民众。”
泊菡解释:“台湾不可能让他过来。所以憾儿让我带话给大家,欢迎所有的亲人去台湾,食宿都由他请客!”
大家笑说:“我们这么多人,他请得起吗?”
念念笑道:“二哥有什么请不起的?我爸的钱就是他的钱,他玩跑车玩摩托,都要爸爸贴补!爸爸钱不够了,就向大哥要,妈妈要!”
大家都听出来了,泊菡偏爱楚忆,楚尧喜欢楚憾,楚忆拿出弟弟的照片给大家看,一身军装的楚憾高大俊秀,泊芙笑道:“有些像几年前演《孔雀公主》的唐国强,但比唐国强还要奶油些。”
泊菡他们不知道唐国强是谁,可泊芙说奶油两字,知道是嫌楚憾生得过于漂亮。
念念笑得肚子痛:“姨妈要是见了二哥,千万别当着他的面这么说,二哥一生唯一的遗憾,就是长得太像小白脸了!”
大家哄笑,楚憾人虽漂亮,性格却绝似楚尧,顽强冷硬,他的手下都吃过亏。
泊菡笑向毓信:“憾儿的太太,就是苏愉的长女燕苏,他们自幼青梅竹马,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女儿。”
亲人团圆,有说不尽的话,好在,既然重逢,就不会长别离了。
第二天,泊菡告诉儿女:“今天,我要和你姨妈去见一个人,等我见过他,再领你们去。”
楚忆知道是谁,默不作声。只有念念笑对母亲:“妈妈,昨天我以为你和这么多长辈相见,一定会抱头痛哭,想不到气氛那么快乐。”
泊菡眼睛微红,却淡淡而笑,说:“傻孩子,你没有看出来,我们都在绷着吗?坚持着不哭!就像蓄满水的大坝,一但开了一条口子,一切都会崩溃而出……所以我们只得坚强,把四十年的苦难藏在心中,只说些快乐的东西。”
儿女在震憾沉默中,慢慢体味到了父辈们的艰难心酸。
泊芙领着泊菡,转了几趟公交,去看望楚舜。
泊菡小心翼翼地问:“我这次回来,他知道吗?”
泊芙笑着点头:“收到你来信的那天,我特地过来,告诉他了。”
“他什么反应?”泊菡强忍泪花,喃喃道。
“他哭了。”
“哭了?”在泊菡菲薄的印象中,楚舜被他的姆妈自小训练,是几乎不哭的男人。
“嗯。他的确流泪了。”泊芙望着天空,肯定道,“只是不知道是喜悦的泪水,还是悲伤的泪水。”
泊菡取出纸巾,狠狠地吸着鼻子。
“我嫁给他,做了他这么些年的妻子,你没有意见吧?”泊芙平淡地。一九五三年,有百货公司职工揭发经理蹇伯英贪污公款,以次充好,个性懦弱的伯英在单位跳了楼。泊芙领着一双儿女生计艰难,多亏楚舜的相助,慢慢度过了困苦的日子,一九五九年,两人结为夫妇。
泊菡连连摇头,告诉姐姐:“虽然,得知你嫁给舜,我很吃惊,可又觉得安慰……我好怕他会孤独一人。”
“我们一家陪着爸爸姆妈生活,他很温暖,一直是他们的好女婿,我孩子的好爸爸。”泊芙望着前方静谧幽深的小径,眼里浮出一丝发自内心的笑意。
“你们为什么没再要个孩子?”泊菡疑惑不解。
“舜说,如果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伯英的儿女就会有受抛弃的感觉,被抛弃的滋味,很难言明。”泊芙平静而直接,可泊菡已经泪如雨下了。
“一会见到他,你不要总是哭,如果害他伤心,我会不高兴的。”泊芙嗔怪小妹,看得出,她很照顾第二个丈夫。
“二姐,我会控制不住。这么多年,我不是不想他,在漫长的时间里,我已经忘了所有的不愉快,只记得他的好……我想过无数次和他重逢,想亲口对他说声对不起,亲耳听到他的谅解。”泊菡转着右手无名指上的戒指,那一道窄窄的金色,是楚舜给她的婚戒,她戴了整整四十年。
泊芙拭去爬过皱纹的泪花:“小妹,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谅解你,这么多年来,他从未提起过你的名字,从未说起过一次你。有几次吵架时,我故意气他说,你这样难怪小妹不要你,他都没有一丝表情……只有释怀,才会谅解,他这种态度,我不知道……”
小路的尽头,泊芙指着一袭灰色,对泊菡说:“他就在那儿,要问,你自己去吧。”
望着那袭浅浅的灰色,泊菡好像看见灰衣少年俊美绝伦的身影,他静若秋泓,向阳而立,回首微微一笑,似在唤她:菡。
她扑上前去,抱住了那袭灰色,冰冷的水泥硌痛了她的肌肤,石碑上刻划的文字:先夫楚舜之墓,灼痛了她的眼睛,让她的血,和着她的泪,山洪崩溃那般,汹涌而出。
“舜……”她不知道痛哭了多久,说了多少心痛的话,可是遗憾已经永远地造成,在十年前,楚舜因为长年辛苦,积劳成疾离开了人世。
“整理他遗物的时候,我翻出一枚金戒指,是我亲手放进他的骨灰盒里,那时候还不知道你能回来。只想着万一有一天你们在天堂见面了,凭着这枚戒指,你还能认出他。”泊芙安慰妹妹。
“他真的没有一句话留给我?”泊菡痛楚难过,心碎如尘,感到连呼吸都困难重重。她多希望楚舜能留一句话给她,哪怕是一个恨字,她也可以感受到他的感觉。
不像现在,不知道他心里有过什么,放下过什么,或者没放下什么,仿佛故事只听到一半,没了收梢,一颗心独悬空中,永远落不下来。
她期盼地望着泊芙,可二姐摇摇头:“没有。他临终前,只留下一句奇怪的话:我死了,你们都不要到墓地去看我,我不在那里,我会化成风,过来看你们。”
这个墓地小而整洁,看得出泊芙常常过来祭扫,她并没有听从楚舜的遗言,执意用这样的探望延续夫妻间的情谊。
泊菡深深痛哭,难过,折磨,痛苦,窒息,将伴随终生,至死难灭……
这时,一阵微风拂面而过。
像秋日的阳光一样温暖,像温柔的落雪一样清凉,像夜晚的星辰一样轻盈,像初生的小鸟一样自由,穿过地面上两个落泪的女人,向着远方,飘飘而去。